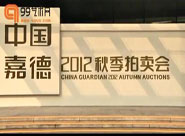美丽和丑陋,饱满与虚无,忧伤和嘲讽,执着与逃避,站在世界的两个端点,当你紧张不安时,便开始分不清,是你在看茹小凡的画,还是他的画在审视你。
艺术家其人茹小凡,1954年生于中国南京,生活工作于法国巴黎和中国南京,1982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艺术系,1986年毕业于巴黎高等艺术学院,1988、1990年获la Casa Velasquez奖学金,深造于西班牙马德里,被收入法国拉鲁兹大辞典当代艺术家部分,作者PASCALE LE THOREL-DAVIOT。
茹小凡的个展“从所”,取自于孔子暮年时的状态:“从心所欲不逾矩”。他自知到不了孔子的境界,所以只敢借来“从所”二字。他把“从所”翻译为不成词句的“De I’”,De I’在法语里,是一个句子的开头,有刚刚开始的意思。
花丛盛开在修道者的身体上部,被供奉于餐盘之上。仔细看那些盛开的花会发现,一些花已经枯萎,大多数仍在透明的塑料管道之间肆意灿烂,对于即将被“吸食”与“消化”,全然不顾。
花面的颓靡之于拥挤的盛开,食色的欲求之于修道者的神圣,茹小凡的“从心所欲”似乎远远越过了世间的“规矩”。就在这个时候,他却小心翼翼地告诉你,De I’。
“呼?吸”之间
2011年,离开中国近三十年的法国华裔艺术家茹小凡,在北京开始了他的“呼?吸”。这是他继与法国“具象后现代主义大师”马克?帝格朗尚在京联展后的第一个个展。
茹小凡在“呼?吸”里刻意给人制造了一种“窒息”感——画面被肥大臃肿的花瓣染得饱满,花汁顺着画布淌下,如果不是屏住呼吸,恐怕画面随时要在面前爆裂。也正是在这些布满画面的肥嫩花朵和塑料消费品里,茹小凡想要表达的“虚空”同时被传达。
“越满越空,满就是空,空也就是满。”茹小凡用中国禅宗思想来解读“呼?吸”中的作品。或许,受到法国超现实主义影响的茹小凡会暗自庆幸,与那些土生土长的法国艺术家相比,游离于中西方的两种文化之间,他的呼吸空间更加宽广。
1983年到法国,茹小凡成为“文革”后中国第一批自费留学生。在这之前,他做过裁缝也当过老师。从南京师范大学艺术系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一所中学教美术,这是茹小凡最大的痛苦,“那时的初中生没有美术基础,除了要教学,还要管理。”
他只是想有所改变,就像他最早开始学画,不光学老师教的,也会画自己想的;上大学时,他特意跟法国留学生学画抽象画,对法语感兴趣。能够在那个氛围紧张的年代去法国,跟他的第一次跨国婚姻有关。
在法国的相当长一段时间中,茹小凡住在一对法国中产阶级夫妇家中。这对慷慨的法国夫妇把一套别墅免费送给茹小凡住。女主人是家庭主妇,但艺术修养很高,对当代艺术有自己的见解。在茹小凡的帮助下,她甚至翻译了中国的佛教经书。闲暇时,茹小凡会教授这对夫妇中文,也会听他们朗读时下最热门的小说或者先锋舞台剧本。
《等待戈多》是茹小凡到法国后让他震撼最大的舞台剧。在国内时,他也曾读过这个剧本的译本,但真正看到话剧演出,茹小凡还是受到了不小的震动。从此,他开始对荒诞剧产生了莫名的兴趣。直到现在,也能在他的作品中看到荒诞的影子。
回国之后,茹小凡发现,他的生活地与他的生长地如此不同,却又奇迹般的相似——当轻飘飘的巴黎遇到秦淮河畔忽明忽暗的灯光时,他带回的那只肥硕的花朵发生了奇异的变化,在“一呼一吸”之间,它们变得如此自然而然,似乎本该如此,本来如此。
“从所”之外
“在自由‘呼?吸’的状态之下,往前推进,到达‘从心所欲’的境界”,其实,在茹小凡此次展览海报的“自画像”中就能看得出来。画面中,他依然穿着具有标识性的白衬衫,双手微微张开。茹小凡说,这个动作在他平时生活中出现的频率最高。这是一个伸懒腰的初期姿势,有一次画画累了,他偶然从镜子里发现了自己的这个动作。或许是巧合,这种刚刚开始却因彻底放松而进入到无拘束的状态,用来为“从所”做代言,显得再适合不过。
从现实主义到超现实主义,茹小凡的转变显得不可思议而又合情合理。对于一个从描摹具象事物中成长起来的艺术家,让“似乎梦中所得的一朵花”,从心所欲地在画布上生长时,人们似乎已经忘记:这朵花看似具象,却并不可以在现实世界中找到对应物。
开始以“花”为主题的创作,跟茹小凡十一岁时的经历有关。1966年,毛泽东最后一次次接见红卫兵,茹小凡就夹在游行的队伍里。那是他第一次来北京,第一次看到天安门,也是第一次见到毛主席,但他却只对天安门前摆放的花团印象深刻。
茹小凡以花为题材的创作开始于2004年,作品《百花》,他选择画一百张各不相同的花,灵感来源于毛泽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思想。他的这批作品在拿到爱尔兰展览时,被爱尔兰最大的连锁酒吧老板和建筑师看中,后来他们建了一个新酒吧,专门放《百花》。
从毛泽东《百花》,到与马克一起,昭示生命力的超现实花朵;从胀满整个画布的“呼?吸”到随心所欲的“从所”,茹小凡习惯保持不断变化的常态。他喜欢那些一直都在变,甚至变得天马行空的艺术大师。“如果一个形式,我自己都看到觉得厌烦,那更不用说看画的人。”
茹小凡在做“从所”的瓷器雕塑“打坐颂”时,中国的几个商人问他,“你这个做出来不像佛像,中国的佛像没有这样做的。”茹小凡在一旁笑而不语地听着他们的讨论,最后谁都不说话了,茹小凡告诉他们,“我做的不是佛像,我做的可能是你,可能是我,也可能是他们。”
悲观主义者的幽默
巴黎的“La Couple”,法国最著名的餐厅之一,这里也是很多美国人慕名而来巴黎的理由。曾经,加缪、萨特、波伏娃、布列松、海明威和数不清的文学家、艺术家、思想家,在这里喝酒、聊天、思考、写作,伴着玻璃杯中摇摇晃晃的红酒,不知老之将至。当然,这里也是俊俏的年轻男子,等待法国贵妇垂青的“猎场”。伴着情人们甜蜜的耳语,也沾了法国文化的光,将近一百岁的La Couple依然流行却并不市侩。
建造于1927年, La Couple的穹顶壁画会邀请每一个时期的有名艺术家绘制,而如今的穹顶壁画就是由茹小凡在2007年为庆祝餐厅的80周年,和来自其他三个国家的艺术家共同绘制的。
肥大俗艳的女人像是一个巨大的气泡,犹如消化系统的透明塑料管道伴着气泡伸张,不知道衣冠楚楚的法国绅士和名媛,在享受鹅肝之余,不经意对屋顶一瞥时作何感想,但餐厅的负责人也负责任地在茹小凡迟疑“是不是要改一改”的时候,告诉他,“我们就要这样。”
La Couple的屋顶壁画流露出了茹小凡的悲观情绪,“现在在法国也是,穷人希望变成富人,富人希望变得更加富有。但人们都不愿意付出努力和劳动,却等待政府的福利。”他不知道,世界这样发展下去会变成什么样子,想到这儿,他就会本能地逃避。
所以,他公然在法国最著名的餐厅嘲讽“一触即碎”的浮华世风,即便如此,慷慨的法国也带着欣喜给出了幽默的答案:我有多骄傲,就有多乐观。
显然这样的幽默在茹小凡身上也开出了奇异的花。他的“从所”中有这样一幅作品:一个身着华服的妙龄女郎,凝视着手中的骷髅。女郎的颈上招摇着绚烂的花丛,但仔细看时,会发现,这些花正是开在盛时即衰的时刻。无论怎样年轻美丽,也无法逃脱衰老临近,就在这样的忧郁时刻,却发觉生命的终点就在手掌之上。当你因此有了悲伤时,却发现,骷髅头上那只调皮的小鸟,一直在看着你窃笑。生命开在幽默之上,显得如此轻松。
茹小凡说,死亡是一个生命的开始,如果没有死,哪来的生。按照这个道理,他对于死的愉悦并不少于出生的快乐。所以,当你看到茹小凡的每一个作品,发现他不断变化,持续“逾越”时,他其实正沉浸在绘画最初的兴奋、欣喜和激动之中,他会笑呵呵地悄悄告诉你,其实每一个完成,都是刚刚开始。
对话茹小凡
我不属于“新波普”
记者:因为2006年法国《世界报》报道了你的“新波普”,因此有评论把你归结到“新波普”艺术家里,你认可这种说法吗?
茹小凡:只是有过展览,把那次展览标在里面。但是我觉得我跟新波普没有特别大的关系。因为我用过消费品,可能跟波普有点关系,我用过百花,毛主席的“百花齐放”可能跟政治有关,所以把我分到波普里面,其实我的画跟波普没有太大关系。我画消费品的时候,其实我画的并不是消费,而是消化,就是人吃饱了以后的那个“消化”。
记者 :现在法国的艺术市场是一个怎样的状况?
茹小凡:现在很不好,全世界都不太好,也不光是法国。但是回来后我发现中国艺术市场,从某一个方面来说,是越来越好的。那就是人们对艺术的认识越来越综合,越来越成熟。但是如果说一个艺术家突然被发掘出来,然后成百倍地往上升的话,这种状况会越来越少。
记者 :对于年青一代艺术家不断出来,你怎么看?
茹小凡:不管国内的艺术品卖得怎么样,从年轻艺术家来看,是欣欣向荣的,比国外感觉要活跃得多。像60后、70后、80后一拨拨的艺术家,在国外没有这样的提法,这几年来,我好像只在国外看到过一个大的展览,在法国的一个当代艺术博物馆,展出的是35岁以下的艺术家作品。
记者 :你说过去德国或者美国的艺术家可能百分之八十都回国了,反而在法国的艺术家发展的情况比较好,你觉得这是为什么呢?
茹小凡:是融入的问题,巴黎的这种传统比一些新兴的城市更包容,或者说是文化的包容性比较强。虽然他们的艺术市场不好,相对保守,投资的勇气小一点,但是文化上很包容。这不光是艺术,戏剧、文学也一样。
【编辑:宋林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