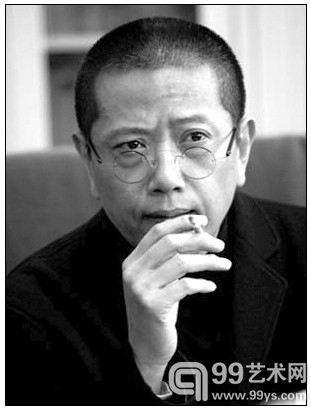
陈丹青
在整理近5年手稿的时候,面对近60万字内容、体例不同的文章,虽明白有些东西无缘最终呈现给读者,但陈丹青自己也不确定哪些话是至关重要得被保留的。
归国十余年,出版著作多部,陈丹青以《退步集》及其续编里对人文、社会话题的冷嘲热讽闻名,为何在新书中却感慨:“人活在这里,也便是这样地一步步学乖?”
陷入人际关系泥沼,最多的文字是应酬
陈丹青缓缓地步入聚光灯下,台下早已响起了掌声,他摘下帽子的右手轻轻地在半空中稍一停留,以此向在冬日下午赶来的读者们致意。当天下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一共安排了3场新书发布活动,陈丹青的这场名为“谈话的泥沼”的对谈被安排在两场中间,提前赶来的读者将走道坐满,其中大多数是背着书包的学生。
与陈丹青对话的是作家蒋方舟,尽管她数次引导陈丹青就书中的内容谈一谈,陈却总是在简短地回应一两句后便迅速地岔开话题。对于三本新书,他评价最多的是“没什么好谈的”。三本新书的书名也承继了陈丹青的一贯自谦甚至自贬风格—《草草集》、《谈话的泥沼》和《无知的游历》,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他之前的《退步集》、《荒废集》等书。
陈丹青一边非常真诚地赞许蒋方舟的写作才华,一边又谦逊地表示自己不是作家,只是一个写了很多文字却谈不上创作的“写家”。就连三本书的内容,他也不否认都是零打碎敲成文。5年前《荒废集》的序言中,陈丹青便说自己已藏身画室,推掉不少稿件约请与琐事,此后他又公开表示要暂停写作,专心绘画,直到现在,他多数的时间“大抵管自画画,减少作文”。
在新书发布会上,陈丹青对读者说,“我最多的文字其实是应酬,说来不足为外人道。就是朋友、同学、长辈、晚辈,帮个忙写篇序,中国是一个人际关系的泥沼,所以我在里面爬不出来,你不写,人家非常受伤害。”同样的感慨,他在10年前初回国后写就的《退步集》便说过:掉进人堆,支应不暇,所言既多,谤议相随,这都不足怪。
媒体习惯了将他塑造为公共话题的批评者,对当下社会议题时有“火气”流露的陈丹青也经常通过媒体表达他的观点。与媒体的打交道增加了他的知名度,但也因经常被无意地误读或是有意地简化曲解,让他不安与愤怒。在整理《谈话的泥沼》的书稿时,陈丹青删除了超过百余处问答,共计五六万字。陈也直言,能给他带来快感的访谈太少。在与读者的互动里,他说,“我这些年接受了这么多访谈,其实是不好的,真的在退步,慢慢沉下去,就是一个同化的过程。”
2002年一次与青年人的座谈会上,就有一张小纸条传递到陈丹青的手中,一位匿名的青年写下了这样的话提醒陈丹青:陈老师,你这样说来说去有什么意思呢?你会退步的。此后,他将“退步”二字作为新书的名字。让他感到有趣的对话是10年前“非典”时困在寓所,应作家王安忆之邀就中国连续剧展开的书面的长篇对话,这篇对话如今收录在《谈话的泥沼》一书中。
没有“存在感”,只有“大时代”
不可否认的是,写作让陈丹青增加了画家之外的另一重身份,因为文字观察敏锐,细节刻画生动,再加上时有妙语,这位早年以《西藏组画》成名的画家,现在常常被认为是一位名作家。而不时冒出的辛辣警世的言论,又让人觉得他是一位批评家或曰公共知识分子。对这些外界加在身上的角色,在《退步集》里他说可见如今成“家”真好办,对于知识分子等称谓陈并不领情,他宁愿做回“老知青”。
在新书发布会上,陈丹青与蒋方舟聊童年与青春,他颇有讲故事的天赋,“上幼儿园时,一位女同学贴着我的耳朵,用上海话说我们长大了结婚。”然后他得意地仰头笑起来,“那感觉舒服死了。”不过,当蒋方舟用“存在感”解读青春时,陈丹青却直言,这是一个他的童年与青春经历中从未有过的词汇。
“我们这一代接受的是意识形态教育,被教育做共产主义接班人,解放全世界,闹革命,种种这些,所以我们没有存在感,我们没有自我意识。”1953年出生的陈丹青,其个人经历有太多的“不由自主”,四五岁时父母便相继被打成“右派”,6岁到8岁左右赶上饥荒年代,童年的记忆里就是饿,吃完了饭还得舔碗边,16岁被下放农村后自学绘画,至今“知青画家”依然是他最早的标签,“我们那代人是最没有存在感的,只有大时代。”
他习惯了当一个旁观者,这些个人的童年经历,陈丹青从未想过要讲述或是写作下来。“我有一个被灌输的概念,这个概念可能是木心给我的,就是你要非常慎重写你自己的经历,因为你要假定为什么别人读你的书。”陈丹青说,另一个原因在于,他和木心这两代人已经不太可能坦然地把自己说出来,“在我的原因可能是那个大时代的教育,我会羞于说出来。在木心是另外一个大时代,战争,还有他自己受的苦。”以木心为例,他有写长篇小说的构想,也把故事和陈丹青说过,是关于他自己的童年和他母亲的回忆、他姐姐的回忆,接起整个过往时代的回忆,“但是他不好意思写出来,他说不忍心。”
在写作《无知的游历》前,陈丹青应《华夏地理》杂志之邀,每年去一个国家,然后写一个题目,但在确定去俄罗斯前,他一直拒绝去这个地方,毕竟“苏联”这个名词曾在他的青少年记忆里打下了深刻的烙印,这个记忆里包含了一个青年时代的想象以及一个国家对一个国家的想象。“最难描述的是俄罗斯,我们这代人是‘毛泽东的孩子’,是‘苏联的孩子’。”
不是教育问题,是权力问题
在三本新书中,陈丹青所谈的议题极其广泛,从艺术到国情再到社会的苦难,但显而易见的是,几年前《退步集》、《退步集续编》等书中对教育对社会问题抨击的“愤青”陈丹青,现在的“火气”少了。
有读者在发布会上问他如何看待一个艺术家跟社会的关系。陈丹青表示,自己现在已经被放在这么一个位置上,“好像你非得对社会有批评或者责任感,这真的是蛮纠结的。因为我们这一代是在另一种语境当中长大的,要求所有艺术家,不光是对社会,还要对革命、对国家、对历史干些什么,你才有资格当艺术家。”
尽管在书写的议题里已经甚少涉及教育,他也不再像《退步集》、《退步集续编》那样将“教育”单列一章,但在很多读者的记忆里,陈丹青依旧是那位当年在清华的辞职信中批评教育体制,痛陈人文艺术招生中毫无必要的英语、政治门槛,直白地说“这一决定(辞职)出于我对体制的不适应及不愿适应”的潇洒模样。
在很多场合,陈丹青免不了经常被问及对教育体制的评价,一些将陈奉为心中导师的年轻大学生,也习惯于向他请教对大学生的建议。此番在新书发布会上,当有一位读者再提这两个问题时,陈丹青没有过多回应。毕竟对后一个问题,陈向来惧于回答,他说:“没有什么建议,就是把它混掉,把学位拿到,四年大学不是你人生的全部,你出了大学才刚开始。我的劝导总是很简单,你得自立,养活自己。”
“混”已经不是陈丹青第一次提及,在《退步集续编》里他说:人在体制,只有一条路,就是“混”。在《荒废集》发布时的受访中,他也说:你只要稍微了解大学的情况,就发现教师的心思不在教学,学生的心思不在求学,大家混,快点混过这几年,拿个学位,弄个职称,对家长对社会有个交代。
而对前一个问题,在他的多本书籍里都有涉及,在《谈话的泥沼》中,他收录一次访谈的实录,再一次点评教育体制:“没有教育问题,只有权力问题。问题是它比赤裸裸的权力还可怕,因为一切是以学术的名义。这可能是有史以来最聪明、最糟糕的办法,就是学术行政化,行政学术化,有人再添一句,经典极了,叫做‘学术行政化,行政江湖化’。所谓‘行政江湖化’,是啊,权力寻租,眼下很多领域都在权力寻租,不是吗?”
在陈丹青看来,权力教育的精髓就是听话,别思考,谁听话、谁识时务,谁就能得好处,最后就是学会“混”,“混”就是“教育”。
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