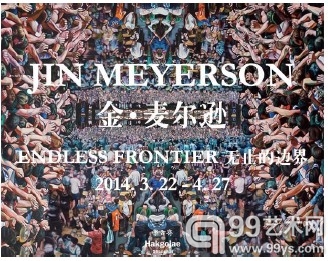
展览海报
麦尔逊是一位美籍韩裔艺术家,1972年出生于韩国仁川,后被一个瑞典犹太家庭收养,在美国明尼苏达的乡村长大。他早年曾在纽约、巴黎和首尔工作生活,现定居于香港。他于1995年获得明尼阿波利斯艺术与设计学院艺术学士学位,1997年获得宾夕法尼亚美术学院艺术硕士学位。麦尔逊在具象绘画的复兴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并应邀参加了一系列重要展览,其中包括伦敦萨奇画廊主办的展览“绘画的胜利”和弗拉基米尔.洛菲德(VladimirRoitfeld)策划的展览“色彩与呐喊”。

展览作品:A Single Journey Can Change the Course of a Life, 2013, Oil on Canvas, 65x92cm
麦尔逊完成了对他香港工作室环境的解读——作品中,扭曲着的人群、自然和机器被柔和的色彩所覆盖。此次,学古斋上海空间将展出金.麦尔逊十件左右的作品。包括他的里程碑作品《死亡诞生之前》(BeforetheInventionofDeath,2009-2010)和《利维坦》(Leviathan,2010),以及《广亩城》(Broadacre,2013)、梦游者(SleepWalker,2013)等近期在香港完成的作品。

展览作品:Before the Invention of Death (detail1), 2009-2010, Oil on Canvas, 200x600cm
屏幕的重叠与画布的层次:绘画的社会性和绘图软件时代的图像建构
在过去的两年中,人们事实上形成了一种共识,即我们的文化已经进入后因特网时代。这种观点既体现在反思性的批判文本中,也出现在日常讨论的用语里。和“后现代主义”类似,“后因特网文化”这个概念不是指我们今天已经超越了因特网文化,而是指因特网文化已经成为无处不见的普遍存在。换言之,就今日艺术的生产、流通和传播而言,借助因特网的复制和传播机制已经和更为传统的当代艺术传播渠道平分秋色。当下这个历史时期使不少创造性的对话成为可能,而数码复制技术与绘画的碰撞就是其中之一:绘画的本体属性越发接近摄影或电脑图像,人们也主要在电脑或智能手机屏幕上欣赏绘画。这就促使我们思考和回答如下问题:电脑绘图软件通过何种方式媲美绘画,甚至取而代之?当然,数码技术和绘画是相互影响的,这或许更让人激动。作为一种工作室艺术实践,绘画已经突破“绘”和“画”的字面意义,在媒介和方法上都产生多样的新发展,吸收了一系列新方法和图像技术,在此基础上思考和展望我们未来的可能性。
金.麦尔逊主要进行工作室绘画的创作,他提供了一扇别样的窗口,使我们能够一览这段文化革命的近况。需要指出的是,艺术家以一种传统的方式经营着他的工作室,从创作画稿和勾勒形象,到平面地处理画面的肌理,再到最终将作品竖立起来调整画面细节,都是同训练有素的助手一起完成。但在上述创作过程的每个环节中,日常图像传播背后的技术手段都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一系列在线图像档案的搜索,艺术家获得图像素材,并最终用于包含具象和其他图像的拼贴作品:绘画作品《广亩城》(Broadacre)和《亚高山地》(Arcosanti)(都作于2013年)都借鉴了“生命之树”这个经典的视觉主题;作品中树叶和建筑这对视觉元素的素材就是通过在线图像档案搜索的方式获得的。和大部分借助数字图像进行绘画创作的艺术家不同,麦尔逊的图像素材选择过程既不是随机的,也不是仅仅关注其网络属性。他的选择过程几乎完全是工具性的,素材是否入画完全取决于艺术家的视觉判断,就像传统画家所做的那样。这使他的艺术创作能够围绕图像建立起有张力的视觉现实——几乎自成一派——并留有很大的变化空间。
这些作品创作于香港这座大都市,它们探讨了都市生态的核心问题:古树和建筑群的关系。麦尔逊对这对关系的处理令人联想到数字技术对手工绘画的影响,但他更多的是将其作为创作和图像探索的一种传统方法,而不是关注其种种潜在的神话含义。《广亩城》的画幅比例和标准的宽荧幕一样,画面中粗糙的树枝无比苍翠,蜿蜒包围着中间的矩形空间,空间四面都是香港大街上随处可见的建筑群。这件作品在创作上颇具电影的画面感,也使观众立刻感到似乎某个事件即将在画面上发生,它玩味的是空间纵深感,是在不同图像之间产生空间的层次。绘画、摄影和电脑制图的特征在这件作品中被弱化;艺术家不是将它们并置在同一个平面上,而是对其不同的特殊质感重新演绎。通过细腻的笔触和微妙的配色,艺术家创造了壮丽而富于层次的画面,将某些空间推入无尽的深渊,而使另一些空间猛地跃于画布表面。
麦尔逊同意,在作品创作和处理的过程中要重视玩味画面产生的变化,而不能一成不变地拘泥于画稿。他的绘画并不是将图像素材简单地转译为绘画的线性过程。与此相反,随着创作的进行,作品的构成也处于持续变化中。他在创作中对最初画稿的各个部分进行重画和重新排列,因此作品的最终面貌往往和初稿完全不同。艺术家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将每件作品——既在实践层面也在观念层面——视为至少数十个图层的组合。“图层”这个术语容易使人想到Photoshop或其他制图软件,这毫不令人奇怪。作为画家,麦尔逊很早就开始积极试验这种图像技术的可能性,在2001至2005年间借助Photoshop软件进行了大量创作。这几年间创作的作品常常带有漩涡和涟漪的效果,因为艺术家预先用软件处理图像素材和草图,再将其绘制在画布上。2005年之后,为了和各种图像处理软件的内建特效有所区别,麦尔逊开始尝试自己制作各种特效。他用手工的方式处理自己的画稿,其中主要的方法是先将画稿打印出来,将打印的图像置于扫描仪上,在扫描的同时移动或旋转图像,这就获得一种类似扫描故障的效果。他这么做仅仅是为了获得这种行动带来的效果,而非通过数字技术来复制图像。在他的里程碑作品《死亡诞生之前》(BeforetheInventionofDeath,作于2009至2010年),各种都市元素被混合在一起,初看上去毫无秩序,但当人眼像机器那样去观看时,或许就能够将图像的边界和线条和分辨出来,形象——尽管和原初画稿有所不同——也就从而浮现出来。这是一种抽象的形式,它是数字摄影术和手工绘画互动产生的结果,带来一种全新的图像,既不同于数字摄影,也不同于手工绘画。
在麦尔逊的创作中,扫描仪的作用值得注意。艺术家先制作了大量图层,通过手工方式进行重新表现,然后再通过扫描仪对这些图层进行扁平化处理。例如,在创作开始的时候,麦尔逊用Photoshop软件将数个图层组合为一张图稿。这些图层包括挪用的照片和工作室中制作的数字图像。他将这张图稿打印并扫描后得到整体或局部图像,并再次插入图稿中,以便用Photoshop软件进行下一步图层化处理。尽管当艺术家最后在布上绘画时,个别图层并不会被采用,但在实际的绘画过程中,起作用的图层是由艺术家通过自己的绘画眼光挑选的,而非由设计师绘图软件的工具盒决定。在最终作品中,两组不同的图层同时起作用。正是这两组“重叠”图像和技术带来了这组作品中绘画作为一种当代艺术样式的生机。著名的新媒体理论家列夫.马诺维奇(LevManovich)最近出版了新作《软件决定一切》(SoftwareTakesCommand)。他或许会赞同麦尔逊的实践,将其视为软件研究新理论的实际应用,并通过对每个图层的分析揭示艺术家如何在Photoshop软件的概念空间中建构他的绘画。但对麦尔逊自己来说,他的艺术实践相当具有模糊性,一方面借鉴了工作室艺术的传统,另一方面也从电脑带来的创新的可能性中获益。相较《广亩城》而言,《亚高山地》这件作品的画面比例——以及色彩搭配——更接近普通广播电视的效果。它同样也突出树木的有机形式和建筑物的直线形式之间的对比,但同时也应用了艺术家的扫描仪创作法,将色带围绕在树干周围,带来一种对比。尽管我们也可以对《亚高山地》进行详细分析,但赋予作品最终力量的是发亮的白色和紫外线般的机理的对比带来的冲击,再一次带来强烈的升腾感,冲进上方的虚空。

Before the Invention of Death (detail2), 2009-2010, Oil on Canvas, 200x600cm
经过制作和重绘的过程,作品最终会超越创作的阶段,继而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拥有自己的生命,开始自在地呼吸。这就是作品完成的时刻,它最终获得绘画的身份。之后,它作为绘画作品在各种展览亮相,被购买和出售,最终成为被收藏的对象。正是在此时,作品最终被拍照,以便网上流传。作品的照片将出现在不同的设备和屏幕上,并被收录到各种出版物中。这或许是一个讽刺。上述流动和传播过程的加速发展,以及它对工作室艺术创作的意义,是迈克尔.桑切斯(MichaelSanchez)和吉恩.麦克休(GeneMcHugh)等人艺术批评的关注点。尽管麦尔逊肯定意识到这些因素和自己作品的关系——不管是直接的还是间接去掉的——但他决定在作品创作阶段排除它们的影响(与之相反,桑切斯发现,很多对此问题感兴趣的艺术家都倾向创作单色绘画或灰色质地绘画)。麦尔逊更愿意直呈自己艺术实践的间接性:比如,作品始终具有一种模糊性,因为插入和并置到图稿中的大量摄影和电子图像都被艺术家手工去除了。更明显的是他的色彩空间必须包含一组多样的色彩档案(包括从Photoshop软件输出的色彩档案)和灰调(扫描的图像被置于打印件和最初的画稿之上),并且这个色彩空间在作品的整个制作过程中必须保持不变。“重叠”在这里又出现了,因为艺术家的绘画是一系列技术作用的结果,这些技术包括工作室的喷墨打印和数码摄影,以及最终展览图录的胶版印刷——在胶版印刷展览图录时,传统上在较色的时候主要参考作品原作的色彩,而不是参考作品使用的图片素材或作品创作过程中的照片。
在今天,人们不再感到亟需对绘画展开批判讨论,而逐渐将兴趣转移到对数字技术领域——包括数字技术对艺术创作和流通的影响——的研究中。在此背景下,麦尔逊为绘画的存在辩护,向我们揭示绘画在创作和材料方面的价值,也使我们明白绘画并不是被提炼出来的一组符号和策略,而在当下的理论语境中符号和策略恰恰被视为绘画的本质。通过坚持或保留某些工作室艺术创作的传统——更不用说选择绘画创作的母题时艺术家心中的具体标准——艺术家能够将绘画的社会属性融入绘画媒介的观念进化中,证明绘画作为一个艺术门类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对色彩、线条、肌理和材料的使用,也在于塑造这些艺术原则的影响,并围绕它们展开讨论。毫无疑问的是:若希望绘画在当下关于媒介和图像的思考中发挥作用,我们就必须尊重其社会属性。
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