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墨:中国画的当代实践仍是一个未完成的现代性
0条评论
2014-07-01 11:52:00 来源:99艺术网 作者:陈耀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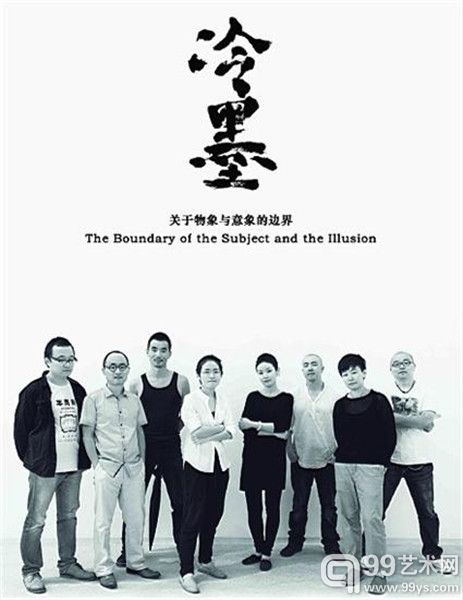
冷墨艺术小组
【编者按】在最近一段时期,“新水墨”异军突起成为一个热门话题,不管是一级市场的画廊还是二级市场的拍卖,从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水墨大展到苏富比、佳士得的水墨专场,再到全球艺博会的展场,到处都可以看到水墨的身影,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然而真实的场景又是怎样的呢?作为一线的创作者艺术家又是如何看待这件事情的?我们听听冷墨艺术小组是如何看待的。
99艺术网:“冷墨”是怎样的一个团体,为什么要组织这样一个团体?
于洋:我们是一个班的,平时大家有什么想法都会在一起谈论,刚好有都是国画专业的,就想在一起做个展览,于是就有了这一个团体。
99艺术网:为什么要叫“冷墨”这个名字呢?
李飒:既然小组成立了就得有个名分,当时也讨论了很多,最后觉着“冷墨”这个名字不错,主要是出于对今后水墨发展方向性的一个思考,在我们看来水墨今后会朝向理智型、抽象性发展,会是一个很理性的东西。
99艺术网:现在关于水墨的讨论有很多,水墨的称谓也很多,比如实验水墨、抽象水墨、城市水墨、当代水墨等等,你们这里的“冷墨”是怎样的一个概念?是一种方法论还是一种口号称谓或者说是一种态度?
李飒:之前与四川美术学院的冯斌老师有过交集,那时候他带我们参加成都双年展下面的一个新人特展,支持年轻的水墨艺术家。当时我有一个判断就是在未来水墨会成为一个热门,但冯斌老师并不这样看,他认为当代艺术会仍然是主流,从去年开始,水墨成为一个主流被大家所关注和讨论,甚至有人说2013年是水墨元年,这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我的判断。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现象是因为大环境的改变,为什么是从去年开始,我前年做过一个展览叫“后现代主义终结之后我们是谁”,当时的判断就是当代艺术会发生一次重要的转型,现在就刚好处在这个很重要的历史时期,首先是意识形态的改变,纵观当代艺术的发展,不管是张晓刚、方力钧还是徐冰,他们的作品都有意识形态冲突的脉络在里面,从改革开放到现在这三十年中国跟世界的关系是带有很强对抗性的,当代艺术是西方强势文化介入中国之后,在西方资本运作下产生的一个事物,这样背景下,中国当代艺术一开始不可避免地带有这样意识形态冲突的特征在里边。
但现在这种对抗性在逐渐的减弱,由于中国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介入到国际事务中去,不管是美国还是欧洲彼此的依赖性越来越强,现在需要的是合作而不是对抗,伴随而来的就是意识形态和文化也会朝这个方向转变,伴随而来的就是对自我文化身份的诉求,所以“后现代主义终结之后我们是谁”有一个答案就是水墨。
为什么拿水墨来说事?当我们不再完全参照西方,完全按照西方的标准去看待自己的时候,就会回归到自身文化的本源中去寻找一个能够阐述自身文化独特性的艺术形式,只有水墨可以胜任,而现在就处在这样的一个时期,水墨成为我们的表达方式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99艺术网:有了解到你们的成员是来自央美综合材料工作室,为什么会集体从事与水墨有关的创作?
于洋:这个综合材料是中国画学院下面的综合材料。
99艺术网:我以为是实验艺术系。
方智勇:当时并不是奔着中国画和水墨去的,学习的是中国传统绘画。
99艺术网:为什么会转到这个专业?
方智勇:追求更高一点的精神需要。
99艺术网:是将水墨当作一个媒介进行创作?
李飒:水墨是一种中国传统,是一个文化概念。
99艺术网:在你们的展览前沿中有看到,你们延续的是中央美术学院胡伟老师的学术体系,这是一种怎样的学术体系?
李飒:胡伟老师是国画出身,央美本科毕业后留校,之后公费去日本留学。他的艺术创作非常有成就,曾获得过国家美展的金奖,到国外之后观念受到很大的冲击,发现我们的艺术与国外相比,落后的不是一年两年,而是几十年上百年,与上世纪八十年代出去的很多艺术家一样,他回来之后的变化挺大的,开始更多的探索绘画的本体语言。
其实从国际的角度来看,艺术教育并不分国画、油画,更多的是理论教育,历史、哲学、美学等等都是他们的必须课,而在我们这里却都是选修课,在他们看来,各个画种只是表达观念的手段和技法,思想和观念是最重要的,在国际上基本上就是以语言、以材料语言为一种形态,要么就是以实验和观念为一种形态的,大概是这么两类,比如塔皮埃斯,偏向于语言本身的实践性,语言本身的探索,另外一类就是博伊斯,偏观念性的,而我们国内并不这样来分,其实今年的全国美展是一个很好的开始,让我们看到了一丝希望,因为出现了综合材料的展区和实验艺术的展区。
这预示着国内的当代艺术生态正在发生变化,我们对于当代艺术的理解也在发生改变。以前国际上只要看到毛的头像就认为是好的作品,就有人买单,现在不这样了,他们更喜欢你自身文化的东西,水墨热某种程度上也是由于环境的变化,国外不再把你简单的符号化地去认识;国内的艺术一直是官方体系,美协体系,现在美协体系下面新近成立了综合材料艺委会和实验艺术艺委会,说明国内现在文化在转型,也非常强调与国际接轨,能够进入国际平台,能够有代表自己文化形象的艺术家,重要成就的艺术家。社会在转型,文化也在转向,这里边会有很多文化的机会,水墨是一个避不开的话题,所以我们做“冷墨”还是有态度的,比较明确的态度,我们有自己的观点,在整个风格上比较形式主义,比较抽象、综合材料,媒材的,但不是实验艺术特别观念性的,政治性的,我们的方向跟其他做水墨的不太一样,我们自己对这个时代有一个清晰的判断。
于洋:在胡老师这里学习,不是单一技法的传承,更多的是一种开放性的教学,是对艺术态度和思维模式的训练。
方智勇:我们的格局比较大,做自己的东西就行。
99艺术网:刚才您谈到你们的创作会比较偏向抽象和形式主义,在“冷墨”首次展览的前言中你们也强调了对于抽象水墨的兴趣,为什么选择抽象?
李飒:之所以会强调抽象,是我们的判断有关,并且这种判断也越来越多的被证实。抽象是和理性相配合的东西,它本身不是中国自身的一种文化形态,中国的文化本身是不太可能抽象的,尽管我们有写意,但像花鸟还是很具象的,另外中国的绘画也没有这样的一个传统和线索。比如说西方的现代艺术,印象派、后印象派、立体主义、野兽派、未来主义一直到康定斯基抽象艺术的出现,有这样的一个发展过程,艺术创作也从强调人的主观性推到理性,其实这背后可以看到发挥作用的是西方的现代性传统,以理性为核心的现代文化一直在推进。
我们现在提抽象,是因为在我看来中国现在需要这样的理性精神,从清末到现在这一百多年中国一直在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现代化,从农业国家向金融国家转变,文化也伴随着社会的转型而转变,既从传统的农业文化向现代文化转变,而这种文化里面最核心的就是理性启蒙,刚开始提这种观点的时候谈论的人并不多,但现在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在谈论这个问题,佐证了我的判断,比如思想家荣剑的文章“重返现代:社会转型时代的艺术转型”就很好的说明了这个问题。
在文中他的核心观点就是我们还处在现代的阶段,另外包括邓晓芒、沈语冰等学者也有相关的论述,都认为中国目前正处在从一个农业国家向现代工商金融国家转变过程当中,因此现代文化的确立,现代文化形态的确立,现代价值的确立,这个阶段是不可跨越的,过去二三十年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主要是借鉴了当时世界最重要,最新潮、最流行的艺术潮流,其中主要借鉴的是后现代主义的方式和语言,因此中国当代艺术主要是在后现代主义的模式中在发展,不管是形态上还是价值理论上。
现在这些思想家都在提出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当你最基本的现代价值理性和启蒙都没有确立的时候,拿什么来支撑后现代的创作?后现代主义是在西方的文化语境下发展的,是现代主义价值确立后,在后来发展中出现了很多问题,尤其是一战和二战的爆发导致了西方的学界、艺术界对现代主义进行了一个强烈的反思,所以他们用后现代主义的东西批判现代主义,反思现代主义,比如提出去价值、反价值、去中心化,反逻各斯中心主义等等,后现代主义的提出是因为西方经历了那样一个过程。中国连启蒙和理性的过程还没有完全经历,在自身现代主义的价值和体系还没有确立的情况下,做后现代主义的艺术就像沈语冰老师翻译国外思想家的话说的,是一种不成熟、一种落后经过包装之后变得前卫,但这种前卫是一种伪前卫。包括批评家栗宪庭的文章现在也在反思这个问题。
其实我们的艺术界一直存在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中国的当代艺术发展到现在也三十多年了,我们并没有很认真的分析中国这些理论到底和中国的现实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中国主要的文化矛盾是什么?中国主要的文化问题是什么?什么样的观点,什么样艺术的发展才真正有助于解决和改进中国文化的状况?推动中国文化从一个传统农业文化向现代工商业文化转变。
现在开始有一些,但主要出现在思想界而不是艺术界,现在也有人开始对小清新的东西进行反思,小清新的东西确实是后现代主义文化的一部分,这种形态在中国发展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作为不同的形态,但是它究竟能解决怎样的问题?如果大家都朝这个方向发展就会有问题。其实艺术最重要的是要对自身所处的时代的文化形态有所反应和把握,继而起到推到它发展的作用。
99艺术网:确实现在很多青年艺术家的创作很自我,是一些小情绪的表达,没有触及到文化的本质,不管是题材还是内容都很“小清新”,不够刺激。
于洋:可以小清新,不是说不行,但是都是这样的就会被人怀疑,好多心态不对。我们“冷墨”避开这些东西,有一个责任共和担当的东西。
李飒:好的艺术家不光是自我状态的表达,还要有一定的社会责任感和文化使命感。
99艺术网:从您的刚才谈的,可以理解为中国现在还处在从前现代向现代转换的过程中,“冷墨”的创作和行为是对这样的文化现实的一种回应?
李飒:我们当初做抽象的时候,也有很多人提出了批评和质疑,因为抽象是西方发展过的形态,你们现在做这个是人家几十年前甚至一百年前做的东西,还有做的价值吗?反过来说西方发展工业你为什么还要发展工业?不是说西方发展过了就没有价值了,关键是要放在自己的语境里面来讨论和判断,比如苏利文对徐悲鸿的评价就不是太好,认为徐悲鸿的技法很老套,造型也不准,没有林风眠有才气,我们从今天的视角去看他确实有很多问题,他的技法确实很不完善,造型也不是完全准确,对世界也没有太大的影响,但他对中国的文化转型是不可或缺的人,是他把现实主义引到了中国文化当中,并对中国画进行了很大的改造,现实主义对于西方的艺术发展来说也是很重要的,现实主义是在西方从传统文化形态向现代文化形态转变的过程当中,非常重,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反过来像抽象也一样。
当代艺术发展这么多年了,我们会发现大众对于抽象还是不能接受,还停留在像或者不像的问题上,在西方,对于抽象的接受是根深蒂固的。尽管我们不能接受抽象,但他所代表的理性文化、现代思维是我们现在最需要的。就像你说的,我们现在处在从前现代向现代形态的过渡的阶段,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代文化,现代主义形态的确立、探索、扩展、普及,其实这个时期对中国来说非常重要,对中国艺术家来说真正重要的并不是对世界产生影响,今天没有多少艺术家能够对世界产生影响。
文化的评价不是从技术的角度来的,是要从文化史的角度考量,我觉得我们所做的意义也是从这里出发,作为一个艺术家来说,我们要对自身所处的时代、文化作出回应,所以我觉得抽象这种文化形态的确立和发展对推动中国文化的转变还是有很重要的意义的。
99艺术网: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也出现过抽象水墨,只是那时的抽象更多的是形式探索,没有提供更多的思想资源,您们在创作时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于洋:每个人差别还是挺大的,更多的还是从个人的实践角度出发。
方智勇:我的很多作品里边没有水墨,在创作上没有一个规范、局限,把想说的说清楚就行了。
99艺术网:在今年4月份你们还做了一个展览叫“水墨还是重要吗?”,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
李飒:当时欧洲有个展览叫“欧洲还重要吗?”,是欧洲的策展人在反思他们的当代艺术,我们看到后就有了这个题目,主要是很符合我们展览和创作的意愿。
99艺术网:看着很有针对性。
于洋:得有人提出问题来,我们展览,包括以后的展览作品很重要,题目也很重要,你要有针对性的。
李飒:就像于洋说的,有一个朋友从欧洲回来,在谈话时说到欧洲的一位策展人策划了一个展览叫“欧洲还重要吗?”,我们当时一听都很震撼,为什么欧洲要做这样一个展览?是因为时代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作为一个欧洲的策展人他深刻地感受到了欧洲的衰落,国外的展览都带有文化问题。现在水墨是一个很热的问题,大家都在关注,大都会博物馆、佳士得、苏富比也都有水墨专场,水墨尽管受到大家的关注,但这里面有太多的问题没有被理清楚和认真地讨论,更多的是商业资本的追逐,我们希望真正能够提一些有重要的文化观点的东西,有助于大家去梳理对于水墨的认识,所以会提“水墨还重要吗?”
从我个人来说,我们都是学水墨出身的,尽管现在用了非常当代的语言装置、空间化的方式去表达水墨,已经算是很叛逆的了,但对水墨的感情是很深的,你越是对水墨感情深,就越需要从全球化的当代角度甚至带有批判性的观点来看待水墨,而不是简单地把它的模式拿过来抄一遍,那对水墨反而是不负责任的态度。
99艺术网:水墨还重要吗?返过来问一下水墨的重要是什么?
李飒:每个人答案都不一样,我认为水墨最重要的是它的文化价值。
于洋:在我看来重不重要无所谓,因为我们的基因就是这样的,做好自己的事就OK。
方智勇:30岁以前水墨跟我没有关系,30多岁以后才开始进入水墨,重不重要我自己也很怀疑,不重要我抛不开,重要跟我生活不相关。
99艺术网:具体到水墨怎样继承传统或发展,确实是一个很头疼的问题。
李飒:我们希望从主题上做特别有观点的东西,这个时代水墨最容易被转换为商品,资本不管好坏,一方面推动现代社会飞速发展,但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资本从不关心人类的福祉,越来越认识到资本主义自毁的性质,回到水墨来说,我觉得这个时代需要有观点,文人画家他们创造一种新的文化形态的时候,,反对职业性、技术性,他们是为了整个阶层,用来表达他们共同的价值观,有了文人的价值和理想才有文人画,才有水墨画,不是有了水墨画才有市场,是不可返过来的。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文人画是阳性的,因为文人主张的价值理念是有气节,有理想,是很纯粹的精神家园的东,所以古时不好的水墨画叫做墨珠,下笔无力、无骨,今天我们看到的水墨都是隐性,消费文化,是把文化理想、信仰的东西、价值的东西全部排除掉的水墨,是伪水墨。我认为水墨应该有文人情怀,可以有俗人的理想,至少应该具备一部分文人的情怀。
编辑:陈耀杰
0条评论
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