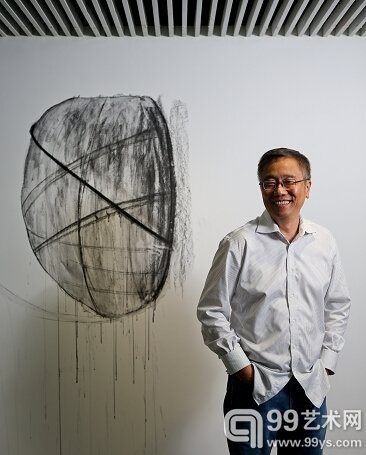以华裔人口为主的新加坡处东南亚最具战略价值的位置,亦兼容并包中华、马来、印度与西方诸文化,其当代艺术的创作与批评更是轻盈舞动于传统与现代的平衡木上。作为新加坡重要的美术史学家、策展人,新加坡美术馆前馆长郭建超前不久在上海证大喜玛拉雅美术馆举行的文化论坛期间,接受了记者专访,谈到中国水墨传统与当代艺术创作时,他表示:“水墨是很重要的文化资源,而这个资源必须找一种方式跟世界分享。其中微妙的难处在于:在新加坡,如果把水墨过度民族化,就会由于这种强烈的民族性让其他文化难以认同;如果把水墨的民族性削弱,它又会回到西方思想方式中艺术课题的主流里去,水墨本身就被淡化了。”谈新加坡艺术:
“多元性是我们珍贵的文化宝库”
记者:您作为一个新加坡策展人,怎么看后现代和中国水墨的问题?
郭建超:我觉得水墨课题必须是一个国际课题。对任何文化而言很重要的课题都必须是一个全球课题。尤其是中国的水墨有这么源远流长的历史,它从商朝末期就开始了,到现在已经将近三千年,世界上有多少艺术的传统是那么久的?所以水墨肯定是一个国际的课题,因为它也是人类的课题。
记者:因为它是人类文明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新加坡有很多华人,水墨肯定也是新加坡艺术的一部分。能不能谈谈新加坡艺术这方面的源流?
郭建超:你讲到水墨画在新加坡是不是一个重要的美术课题,它的确是的。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是兴起美术教育的时候。中国南方像广东、福建,尤其是潮汕地区有一些艺术家就来到上海受教育,变成上海现代化新美术的重要部分。他们中有一些回到了中国南方,另外有一些到了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美术也是有这样一部分背景的。
在这其中,厦门美术学院非常特殊,他们创校的时候是到菲律宾去学画的。上海这边要出国学习美术,要么就去东京,要么就到巴黎。但是菲律宾有西班牙统治的历史,经过很长一段时间,那里也建立了欧式的绘画学院。再加上厦门地区和马尼拉地区特殊的关系,所以这些厦门的艺术家就到菲律宾学西画。
那是一种双面的关系。首先有上海和其他中国南部地区的区域性差异,再加上厦门本来就跟菲律宾有着联系,所以这批画家跟东南亚画家是一种相互的双边的关系。
记者:彼此影响的关系吗?
郭建超:也不能说彼此影响。五四运动之后,这一批中国南方的艺术家来到上海,接受了上海的一些新思潮;但是他们又有在马尼拉受教育的遗泽,所以也有一定西方艺术的基础;后来又到南洋去,接受新加坡的文化的影响熏陶。这样(在多元文化的碰撞下)也产生了一些新的画派,这些新画派你可以看成是水墨画在南洋经历文化碰撞所产生的新的流派,也可以看成是一些支流。但是我们现在在一个多元的艺术框架下看问题,就不太用这样的字眼来说,什么是“支流”,什么是“主流”。我们对任何不同的潮流都感到兴趣,觉得重视。
比如说云南地区的苗族,这里(中国大陆)叫少数民族文化,其实它跟整个湄公河流域的文化是很接近的,有着一些湄公河流域的审美价值观。所以这是中国的衍生吗?还是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从泰国来看?当然这都是一种多元化的发展,也很庆幸能看到中国本身的多元化。
我们说回来,新加坡的画家也跑到巴厘岛去。作为一个画家,以画面去思考图像的问题,当你到一个地方看到当地的音乐舞蹈宗教仪式,跟绘画是不能分割的,你的基础可以是水墨画,但是整个审美的价值都被改变了。新加坡有个著名艺术家叫钟泗宾,他就走向了装饰的风格。这种装饰风格不仅仅在于把一个平面图像做得更漂亮一些,而是跟生活的节拍不可分割的,包括舞蹈和宗教艺术等。所以钟泗宾虽然是水墨画的底子,但是同时又有很多元的背景。他出自一个厦门的少数民族村落,进入厦门美术院校学习,这个美术院校又受到清末和五四新美术思潮的影响和熏陶,而这种新美术思想也是现代化和西化的基础。
那个时候海派画家讲究金石趣味,在书法上特别重视碑文。在文人画传统里,对“古朴”的推崇一直是很强烈的。钟泗宾在东南亚地区又跑到东马来西亚半岛,那边有很多本土的少数民族原住民,对于他而言,本身所带有的中国文人绘画“古朴”的审美价值和当地原住民的文化有了沟通,通过原住民的文化他又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再来理解中国的文人画传统本身的价值,再加上他本人就是在东南亚生活的,这其中是非常微妙的。当我们现在讲到后现代问题的时候,这种多元性的确是我们珍贵的文化宝库。
记者:所以我们不再用边缘和中心这样的词汇,更加会看到其中多元化的差异性。新加坡艺术的源流,除了水墨画之外还有别的,比如马来西亚当地的艺术形式。
郭建超:当然是有的,这个说来就话长了,是整个马来西亚艺术史了。
记者:新加坡的艺术家在处理后现代的问题时,和中国大陆的艺术家有什么异同吗?
郭建超:当然有很大的不同。首先是国籍的问题。
也有很多共同的地方,我们也是从很多西方的论述出发来做一些思考。甚至因为新加坡教育制度的关系,就会更直接地去接触西方文化。但是本地的文化意识也是很强烈的。对一个艺术家来说,对这些会更加敏感,但他也不可能完全把自己脱离出整个群体而站在另一个角度去面对这些问题。就好像我本人对中国艺术很感兴趣,但我也不是在中国大陆出生和长大的,那我所形成的中国艺术史的观感和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是不一样的,同样,西方的艺术理论,新加坡的艺术家可能通过教育的渠道对之也十分熟悉,但是由于客观的“身份”,就不会认为这是自己(文化)的艺术理论。
我们今天所谈的,很难从很大的角度去划分什么是民族的,什么是国家的,或者是把世界分成中西两部分这样二元论的思维方式去理解。我们最后能做出的总结还是其次,最重要的是通过解构去深入了解这些艺术。所以我要讲的“全球性”并不是全球归一趋同化的全球性,而是真正全球对话的一个论坛。
后现代单从西方的角度是不可能把国际上的多元性都涵盖的,所以上世纪90年代起他们积极地去了解世界上不同地方的艺术发展。他们有这样的走向。站在西方之外的角度,我们也不可能说:“谢谢你们,终于接受我们了。”
艺术的好处就在于我们可以慢慢地去对话、体会和了解,而不是为了给自己挂上某一国家、某一文化的标签,说我是法国的,或者我是新加坡的。这个都没有什么意思。
记者:在喜玛拉雅美术馆的展览“跨地域的水墨经验”中,我们也看到两件新加坡艺术家的作品,您觉得这两件作品中有什么“新加坡性”吗?
郭剑超:郭捷忻画的是一个新加坡的景象,有着一种新加坡民间的味道。它是描绘社区里的一些活动,日常生活的味道。从这个看,它是一件写实的作品,直接描绘新加坡的。
陈玲娜用的素材是木炭。木炭的元素和水墨的元素其实是一样的。所以你可以把它看作是对水墨进行解构的一件作品。我们说水墨画的多元化,艺术家用的就不一定是传统的墨、笔。从中也能看到对于当下的生活、当下的环境以及水墨画本身做出的一些思考。陈玲娜选择对水墨画解构的方式来创作,采用与水墨同元素的木炭来进行创作,你可以说它是水墨画,也可以说它不是水墨画。
谈水墨艺术:“找到一种方式将水墨与世界分享”
记者:现在关于水墨的讨论还蛮多的,大家都比较关心这个话题。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之前也做了一档水墨的展览。从国际视野来看,一些人可能只是把它当作一种工具或者媒介。您觉得当代水墨还有没有包涵一些文人性在其中?
郭建超:在文化史上,水墨画是一种特殊的东西。中国的科举制度和朝廷官制起源很早,所以水墨画本来就带有双重的身份特征。首先朝廷里本来就有画院的画家,但是朝中大臣的文化趣味却在于朝堂之外的山林之间,尤其在明朝董其昌之后,也就是十六世纪中期之后,整个文人画的脉络就被制度化了,文人画就被纳入了中国绘画的正统,而其实它的背景却恰恰是不在于朝廷或者制度之内的,却被朝廷所瞻仰,这是个很特殊的现象。
这个特殊的现象对当下的中国文化环境有怎么样的意义?中国官员喜欢文人画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不接受社会写实主义吗?我对此不是很了解,但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另外一种可能就是这些官员在找寻一种文化标志和符号。
然而,毕竟水墨、山水或者文人画并不是那么容易在国际上获得广泛的接受。很多人中文都不懂,更不要提书法,这对于华语文化圈以外的人是非常难的。这也不能去怪别人没有能力去理解,因为他学习中文语言可能需要十年,学书法又是十年,是很难的。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在国际上非常强势地崛起,有一些人把水墨或者文人画看作是中国文化的标志。国外的艺术界就会对此有一种情绪,一方面是出于不了解,一方面是出于抵触,他们会觉得:水墨是你们国家非常陈旧的东西,我们可没有兴趣,我们现在做的是当代艺术。这样的问题是存在的,越是存在这样的问题,我个人觉得,中国艺术界越有责任去向国际上说明解释水墨到底是什么。
我们现在面对的就是这类多层次、多视角的对话,如果我们又站回自己的身份,只关注某一种传统,文人画传统也好,别的也好,就会变成只有我们自己了解自己的传统是有价值的,但是这样一来,我们是否有必要跟别的文化圈分享我们的传统?
所以水墨的课题是很重要的。之前谈到的两个课题,首先是“文人”的概念在当下社会有什么样当代的意义?另一个就是在全球的范围里面,这些古老的价值观如何跟国际艺术界沟通?
记者:这两个也是我们现在在处理现代与后现代问题中比较重要的,需要面对的问题。
郭建超:是。水墨是很重要的文化资源,而这个资源必须找一种方式跟世界分享。
记者:上世纪上半叶,在西方,亚洲的艺术文化——比如佛教与禅——有一阵是很流行的。
郭建超:是的,这又跟日本有关,在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尤其是美国,他们对禅宗佛学非常感兴趣,进而对水墨也开始感兴趣。印度在二十世纪初期对水墨画也产生过兴趣。是一个比较小的文化圈子,那时候都是互相影响的。如果我们回过头看二十世纪初期,就会觉得我们又走回了一百年前的路。甚至在美国二战之前的一个阶段,他们很多学校把水墨编进学科设置里,因为他们觉得水墨不仅仅是新颖的艺术,更是觉得,如果要让学生具有全球化视野,就必须把其他文化中很重要的东西放到课程里去。
谈当代艺术:“现代和后现代是共存的文化现象”
记者:在现当代艺术领域,新加坡在东南亚其实类似于一个连接世界的桥头堡或者平台。
郭建超:我们说一些具体的吧。新加坡有一个区域性的收藏,国家收藏里有整个东南亚(主要是二十世纪)的收藏,它是比较完整的。而其他国家都是重视他们本国的现当代艺术收藏,但是新加坡这个地方比较小,走快一步,就出国了,所以就会比较关心整个东南亚区域的艺术。这个也是我前十多年的工作,就是收集整个东南亚的艺术。
记者:新加坡是一个港口,所以就更加愿意把眼光放得大一些。
郭建超:听起来有点诗意啊。主要是我们比较小吧。
记者:新加坡美术馆和国家美术馆如何分工呢?
郭建超:其实是时间上的不同。开始时候建起的是新加坡美术馆,后来又决定建一个新的国家美术馆,所以就有了两个馆。
国家美术馆建立之后就想比较完整地呈现东南亚的美术史,所以原本的新加坡美术馆就开始转向重视东南亚现当代艺术。这两个馆就有点像一个是当代馆,一个是艺术史馆。不过这也是很旧的二元的概念了。
比如上海,我们与其说中华艺术宫必须呈现整个上海甚至中国二十世纪的绘画艺术史,而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要做全球化的当代艺术,其实更重要的是两馆之间的桥梁。恰好,一个在浦东,一个在浦西。不应该把它看作两个完全区别分工的机构。话又说回我们今天谈论的后现代问题。其实现代和后现代不应该看作是过去断代的历史,而是应该把它看作是同时存在的文化现象。所以我想中华艺术宫和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应该是有一种同存的当代性,不应该是分得太清楚的两个区域,要保持两者对话的关系。
新加坡美术馆比较重视当代艺术,就好像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国家美术馆就好像中华艺术宫,是有这样一点区分的想法。我必须要以独立策展人的身份来讲这件事,两个馆我都是策展人。我们要把这个格局换一换,才能找出当下我们所重视的文化课题。就好像今天讨论现代与后现代的课题,你不可能把它分开来看待。
其实这个问题在英国也存在的,就是伦敦的TateModern和TateBritain之间,也不是说分工那么明晰,好像TateBritain就做比较英国的东西,而TateModern就做比较国际比较当代艺术的方面。后来他们发现这种分法也没有意义。
记者:当代艺术跟艺术市场的关系比较密切,那么当代馆要如何做收藏呢?
郭建超:当代艺术跟艺术市场的关系比较密切吗?我不这么认为。
我觉得艺术之所以是个特殊的文化领域,是因为它本身是矛盾的。因为在这个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的市场上,它必须表现出一个很开放的姿态。
收藏家群体希望找到最有时代象征性的作品,他们也很有前瞻性,今天收藏的东西,三十年后人们回过头来看,就像看杜尚的《泉》那样,完全是一个时代的象征。艺术家看到有人收藏是非常欢迎的,不论是藏家还是美术馆,都会给他们新的创作提供一些资源。但是在艺术界里也有一批艺术家是拒绝作品“被收藏”的,就会采用一个无收藏的形式来呈现作品。
在当下的国际艺术界,有这样一批理念先进的艺术家作品,这些东西越是具有批判性,收藏家们就越是愿意收,这种矛盾的现象在其他场合是看不到的。
比如今天我要做一个关于上海的课题,这个课题可能敏感,甚至我身边的人都不了解,但是我可能跟另外一个有着不同社会经验的人就能够达成互相的理解。就是说,我们可以在国际的背景下在任何时候找寻对话的对象。这种多元的开放性,我敢说,是只存在于艺术界里的,也是值得珍惜的。
记者:所以当代艺术的概念本身就是更加丰富的,不局限于传统的艺术的方式和概念。
郭建超:是的,它是针对社会,针对政治的,但是在一定层面上它又是超越政治的。比如说,我们以为上世纪60年代之后,东欧和西欧因为冷战的关系,就有着巨大的分别。受苏联影响的波兰、葡萄牙、匈牙利,还有前南斯拉夫等等,我们以为这些国家就会跟着苏联在艺术上走社会写实主义的路,而西欧就会偏向抽象艺术和现代绘画。
但是只要你去波兰,去匈牙利,就会发现,这几十年来,无论是社会主义欧洲还是资本主义欧洲,两个阵营的艺术家都一直在对话;而且更巧妙的是,你可以在艺术作品中看到,两方艺术家在艺术中探讨的问题是超越政治的。无论他们在柏林墙的哪一边,他们思考着许多共同的问题。最终两方所想的东西,可能是相当一致的,也就是人所追求的理想。这些艺术家的对话不受社会、历史或者政治的限制。
为什么说艺术家必须为本身个体来表达?就是因为一旦艺术家觉得自己是在代表社会,这个代表性就立刻削弱了艺术作品的真诚,或者是其中可能包含的更深层次的理念。我们在不同的社会都遇到同样的问题。我再次提到艺术界全球化的意义,这种全球化可以使得不同区域的艺术家在其所在的体制中有一种超越,能够在不同的社区里找到一个了解他要讲什么的人,这个人可以身在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甚至可以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段。
如果回到唐代,也许张某某所讲的东西,在某一个非洲文化里面,或者在一部分当代人的思考里,会产生一种共鸣。这种共鸣的产生我们无法掌握,但是我们就要制造一个全球化的艺术界,使得这种超越时间空间的共鸣有发生的可能性。这就是我对于全球性艺术的信任,在当下的社会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积极的机制,而它跟市场的关系,无论是叛逆或者串通,都无所谓。
说真的,一个艺术家如果只为市场创作的话也不会走得太远,这就是艺术本来就有的价值,哪怕是一个成功的艺术家,如果开始过多地着眼于市场的话,那他也就开始走下坡路了。
记者:艺术市场是本来就存在的,但是艺术本身比这个市场要丰富得多。
郭建超:那肯定的。我们不可以把市场看成一个很单一的东西。如果一个艺术家光关注市场谁的东西卖得最好,那就不是一个艺术家,市场也不会接受这样的艺术家。
编辑:文凌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