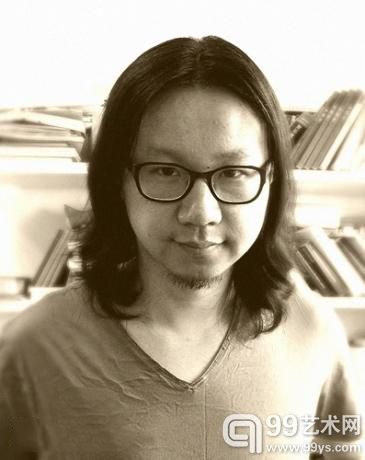
关于某一段历史或者某一历史中某一个人创造成果的描述,如果不能还原其种种细琐和微观,最基本的任务是从种种表象出发梳理出一条线索,这条线索不必客观到无可辩驳,至少可以促成精神历史中前人后者的对话,而不致让其人、其事埋没在时代的错误之中。这种时代的错误,往往是通过一些被奉为基本原则的概念和准则而造成的,比如民主、集体主义和反集体主义、个人性以及各种通过运用一定的语言、文化和社会编码而组织起来的东西。对历史或者个人进行研究,就不得不与这些概念和准则进行旷日持久的斗争,在试图揭示那些不可见的、内在的、难以一言以蔽之的思维模式的内在矛盾的同时,给予历史或者个人以平等的地位,使其不仅可以被(作为某一特定群体或者在某一特定群体中扮演某一种角色的)我们理解,也同样要被其所处的环境和周遭理解。“可理解性”(intelligibility)总是受命运驱使,在各种以抽象观念和固有的精神习惯为前提的批判方法的咄咄逼人之中,被排斥在讨论之外。然而,历史总能给我们这样的教训,这些批判方法,在几经时代周折之后,通常会变成最大的问题和亟需反思的对象。
我们的当下,正在成为一段新的历史。2014年10月15日,在北京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历史的回声再度响起:“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 文艺界的党机构领导者和代表者悉数出席,这当中也有当代艺术世界中人们熟稔的名字。尽管当代艺术在文艺界或者说当权者眼中的地位,不比文学、影视、戏剧,然而文艺是一家,在我们所必须面对的语境里,当代艺术绝不特殊。几个社交平台上都开始大量转发这次座谈会的讲话内容和出席者名单,有的人明白,事情又开始起变化了。
回想起来,三十五前的1979年,四次文代会上曾提出“文艺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乍一看,这崭新的口号是在给“文革”断句收篇,旧貌换新颜,总要有个名头,“人民”和“社会主义”正是我国的普世价值。但你细细咀嚼其中味道,这句新口号,恐怕更是要取代几十年以来“文艺为政治服务”的金科玉律。
1979年的新口号是否改变了文艺和政治之间那种根深蒂固的监护关系?看看80年代那些此起彼伏、由上及下的运动,文艺还是桥头堡和冲锋兵,批《苦恋》、批人道主义、“清除精神污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在当权者看来,文艺的服务对象只能是政治,口号再变,无非是权力更替的需要。
文艺是政治辩论的主战场,这是自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奠定的基调,在毛时代完全成为意识形态斗争领域的核心。80年代的文艺运动,比起1979年以前,真是小巫见大巫。看过学者高华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再比对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对延安这一确立文艺为意识形态理论战场前沿的非常时期的研究,前人的路,如此触目惊心。历史总是走得很快,即使当代艺术世界的“老人”,至早不过50年代出生,恐怕对那时候毛氏运用自如、“其乐无穷”的文艺斗争也没有太多记忆。批《武训传》、批旧红学、批胡风集团、批丁陈集团、反右、批《海瑞罢官》、“黑八论”,再到为我们熟知和封禁的“文革”,这些前历史,彻底把文艺卡死在政治的领域内,腾挪不得。
2014年,文艺又被提上议题,这一动,对于习惯了几年新自由主义经济环境的我们,意味着什么?艺术的格局已变,思想已变,我们的价值天平早就实实地落在“个体”之上,那好像是我们唯一的“自由”。因此,某个港口走上街头的群体运动实在至多提起揶揄的兴趣和知识主义的故作深沉,似乎经历过了,就一定看清楚了个体面对政治的位置。这是不是时代的错误?
个体价值,这就是我们的“自由”。1976-2000年的时段,我们对个体价值的态度极度鲜明,也不存疑问,这是历史自身的面貌使然。因为有了意识形态政治的存在,个体价值是斗争出来、拼取出来的产物,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内,它没有不确切性,它可以延展的范围和收缩的紧度是可以预见的。即使在商品化经济逐渐兴起的90年代,艺术界和知识界的争论也不在于个体价值正确与否、它与我们的集体主义传统能否共存,人们普遍更关心的是,个体价值可以在哪种层面上有效。
2014年,我们来到了这样一个四处不见方向的森林,退去了十几年的政治空气又如雾气一般开始聚集。这是见不到自己,也见不到同行者的特殊时刻。在艺术界内部,越来越多的同行们开始感受到一种深深的无聊和困惑。人们不愿意用“我们”这样的字眼作为表达的主体,却也发现,自己的这个“我”也没有那么坚固和强大。去政治的氛围加上政治美学化的趋势,艺术享受了、或者说经受了几年资本和市场的占领和新自由主义经济的绿卡,我们似乎身处在一个更加“艺术”、更加“当代”、因而也更“自由”、更“个体”的艺术世界。它培养了我们对自己这个“内部”的骄傲感,也短暂地让我们忘记时代的存在,以及艺术这个自由身份的由来。
然而也有些人,找到时机,通过一系列的抽象概念塑造,把艺术与政治氛围重新挂钩。今年5月份,艾未未撤展事件的发酵中,有评论者将艾未未描述为一个在中西之间贩卖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掮客形象,把“西方”、“西方观众”、“西方主流意识形态”这些其实是不断被我们想象的他者视为艾未未艺术实践的接收地。原来,西方是这样可怕,它如此乐于收集艾氏的“旅游纪念品”,不过是为了某种政治意蕴和阅读需要。我不知道,这种比殖民主义还要原始、粗糙、别有用心的论调,是怎样在我们现在这个号称已经很当代的艺术世界中形成的,甚至代表了很大一部分人的观点。不去讨论艾未未的知识分子立场,甚至也不屑质疑艾氏的某些政治手腕,而用这样一种把西方再次设立为我们的第一对手的方式进行批判——这不由让人回想起90年代以来知识界的“左派”故事。当时那些对“西方价值”、对美国留学回来的同行所带来的自由主义极力质疑的人,曾经展开过一系列针对中国现实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考察,引发左右之争。这场争论的影响,在这几年政治大变动的环境里再次显现,其论调更紧跟官方意识形态的风向,其立场不再是思想领域辩论的结果,慢慢简化为抽象的观念斗争。“西方”,连同它被我们某些人痛斥的所谓“抽象民主”,就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段里再次到来,仿佛经济地热潮一褪去,那个我们自以为可以与之平起平坐的“西方”,马上就显露了真面目。
批判艾氏实践的这种方式,不可谓嗅觉不灵敏。艾未未被树立为把自由当“名义”、无视自由之“伦理”、无视“消极自由”权力的独裁者形象——我们发现,这种抽象的道德讨论如此熟悉,它对复杂的现实与个体不体察,用肤浅的怀疑主义态度消解知识分子立场,又隐藏着现实利益和情感的需要。这让人不由得警惕,“自由”二字,和这个国度所面临的高层权力更替时局里潜在的高层理论分歧,又要发生联系。“自由”将被当做什么样的工具,我们还不知道,但是对艾氏的这场批判,似乎已经提供了一种线索。
本土艺术世界的自由其实历尽艰辛,常常是不由自主。官方的文化政策和体制构造往往是自由实验的前提。改革开放之后的文化政策,时而压制、时而放宽,试探我们的同时又要保证一条与政治合节的轨道,艺术家们也必须在这二三十年收纳能力愈加强悍的体制空间内外寻找位置。有一些艺术实践者,因时代的缘故,在开始艺术生涯之时就天然地具有体制批判者的自由身份,却在我们这个实在嘈杂和疯狂的当下,变成了内心流亡派;有一些,受惠于知识资源的开放和国际旅行,自然地享受起知识自由的好处,对任何问题都采取虚晃一枪、不加判断的姿态,把犬儒当做唯一积极的立场;有一些,把知识玄学、美学荒诞当做艺术实践的核心,宣称严肃的自由,凭靠着和理论的暧昧关系在艺术系统里寻找立足之地;还有一些已经被赋予艺术史位置的创作者,他们既受制于自身某些精神习惯限制(比如对理论生产的崇拜),又对现状无法给出如过往一样那么有力的回应,他们很多人在承受时代痛苦的同时,不得不放弃了对自由的艺术的发问。
自由不是一个可以依附的东西,一个抽象的道德,它也许只能是实践出来的结果。自由应该是强大的,它不仅仅是一个现实政治问题,它是个体政治,是动作,是身体和精神冲撞的地方。对艺术世界中的我们而言,享受自由和困惑于自由总是同时存在。最近的三十多年历史和眼下的状况向我们显明,政治意识形态的主导或者沉寂仍然是这个自由的前提,并且,它从未远去,我们的艺术生产和理论生产、我们的价值判断方式,无时不在折射出它的影响。这让我们对政治的态度如此进退两难,既希望它在,又希望它远离,一个难以治愈的心理焦虑症。然而艺术,在它的愈加组织化的体制和价值抽象化的思想现状里,真的无法面对自由了吗?
几年前,在我们热衷于消费“游击”、“寄生”这个概念之时,却遗憾地错过了一次深入讨论我们语境中自由何为的机会。源于不自信和参与到更前沿的艺术讨论中的欲望,我们把这些概念的到来视为一次可以利用的机会,也把它有意地放置在艺术机构、尤其是公共空间这种易于凸显社会价值矛盾的领域进行塑造。这种有意的自我规训,试图寻找和西方艺术世界平行的方式工作,但却忽略了对艺术游击、艺术寄生的思想探讨。这种探讨,完全可以关涉我们的艺术世界里所隐藏的各种价值叙述及其牵连的思想意识形态,完全可以关涉我们如何反思和超越自我历史中的政治意识问题。艺术的自由,无论是“游击”还是“寄生”,无非一种“野性”,但我们迫切地需要从实践而非抽象的价值辩论中,观看这种野性的边界、想象力和可能性。当这种“野性”遭遇现实政治的变革时,我们更需要艺术的自由意志,那里面,是责任、思想、独立性之间幽暗而深重的战场。而至于个人价值这种自由载体,一旦变成不言自明的标准,就到了需要重新梳理和钩沉的时刻。
中国日报网近日曾经转载一篇新加坡《联合早报》的评论员文章,文章就国庆招待会上的讲话分析了执政党新的政治诉求和变化,暗示了中国官方意识形态的进阶。作者称:
“多年来,历届总理在国庆致词中提到建国以来这一段时期时,经常使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说法,彰显改革开放的成就,而习近平讲话中却多次代之以‘65年来’的简洁用语。这表明两点:一是杜绝左右两派关于改革开放前后两段时期孰对孰错之争;二是可能鉴于改革开放的红利殆尽,因而昭示今后或许要试探另辟蹊径了。”
如果对这几十年来执政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历史有所知觉,我们会发现官方意识形态已经在试图摆脱简单的价值观斗争,而开始立体和深入地把党的意识形态核心化,超越主义之分,路线之分,从而使得政党成为唯一的价值观载体。这种新动向,是历来未见的,它体现出一种更加明确的超级政党态势。它与西方主要大国的寡头政府形态或者财团支配下的政府形态都不相同,它发出的政治信号也将是前所未有的。
对于中国的当代艺术世界,政治空气从隐匿到显现不是周期性的循环,它其实从未离去,并且已经在我们的知识生产土壤中根深蒂固。新的政治气氛,可能是某些人上交投名状的机会,可能是给了艺术又攀附上哪种派别的知识理论诉求的良机。它一定会导致艺术的对抗,引起人们“重要的是艺术还是政治”的争论。我想,接下来可以预期的发生,其故事情节,不会超出我们历史中那些波谲云诡的文艺-政治斗争所历经的一切。然而不同的是,我们所面临的新的政治态势,已经与我们老于世故的头脑中的那种政治有着本质不同。在一个“另辟蹊径”的超级党意识形态氛围里,艺术的自由,是否会在这新的局势中激发出自身的可能,还是继续在本就薄弱的自我基础上建立新的美学迷宫?
(作者系艺术策展人、批评家苏伟)编辑:罗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