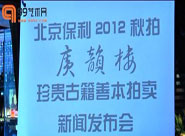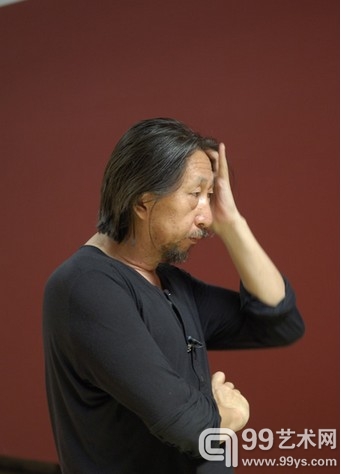
王广义
一个很轴的人,说出“随缘”这两个字,一定意味深刻。他说,生活的世俗和思想的高度其实并不纠结,年少时向往的那些这些神圣的力量没有消失,而是隐含在最最日常普通的生活中——随缘,就是经常会从一棵树,一杯水中忽然发现很形而上的东西,但这又是一种宿命。
初见王广义,你很难知道他的职业,更别说一眼看出他是艺术家。他身上几乎没有任何当代艺术家的特征:个性,自恋,愤世嫉俗,耍花腔,等等。相反,长发墨镜加上他高大的身材、不苟言笑略带粗糙的脸,跟人一种冷冷的距离感,你会想到让雷诺演的杀手莱昂。
但若是去了解他,就会发现,可能他的内心有一个无法也不肯与人分享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他是自己的王,同时又是谦卑的民。他的冷,是一道屏障,屏障后面是某种持久而热情的 坚持,坚持的仿佛固执,相信宿命。对于宿命的人来说,人生就像画一个圆,从起点到终点;从出走,到返乡;从相信宿命,到确认相信宿命。一生奔波追问,是为了确认最初的相信。
当代的古典主义者
王广义生在北方的哈尔滨,和那个年代的大多数人一样,童年时代充斥着原始的冲动、激情,同时又笼罩着迷茫和苍凉。可能寒冷的北方没有暗示给他太多温婉,他的性格里更多的是冷静、严肃,以及一种悲壮,就像临近的俄罗斯大地上行走的圣愚。这种性格,让他比别人更敏感于未知和神秘的事物,他能够从昏暗灯光下的剪纸中看到一种“神圣”的能量。这种对于未知世界的敏感和敬畏,一直贯穿在王广义的艺术和生活中,并很大程度上左右了他对世界的选择。
过早担负沉重的东西,容易让人压抑,当然也会让人从压抑中获得反弹的力量。王广义常说自己是个很“轴”的人。他曾经连续复读三年考美院不就,所以很自卑、很压抑,坊间传闻考学期间他沉默寡言,考上大学后回来见当初朋友,酒量惊人,大家发现原来他很能说。大学期间,他不像许多人选择诗歌、摇滚、文艺腔,而是迷恋于《马丁伊登》、《西西弗斯神话》这样一些宛如贝多芬命运交响曲一样的文学作品。在艺术上,他宣称自己是笃定不移的古典主义者,并且不是当时浙江美院流行的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法国古典主义,而是更像德国的古典气质——他从不屑于审美,他从古典主义中看到的,更多是真实和庄严。
实际上,确实如他所说,他身上带着很强的古典主义气场:静穆的,严肃的,自律的,甚至仿佛他本人也像古典文学、古典绘画中的某个角色:“在我精神之路上,我仍然欣赏古典。我觉得当代是一个外衣,最本质的问题在古典当中已经存在了。如果抛开古典来说当代,是很荒诞的,在我看来当代是一个浮萍,人很多最基本的东西、人得以存在的一些最基本的理由,在古典逻辑中已经存在了。我认为古典艺术之中有一种超验的精神。”这种古典主义情结在他《北方极地》系列中表达的特别明显。《凝固的北方极地》中,空旷的大地、遥远的地平线、静谧而冷寂的氛围,王广义极大摒弃人们生活经验中可感的因素,排斥感觉和情绪中非理智的偶然成分,以抽象的形和精神表现其主题:某种向上的肃穆而崇高的原则,“表现出一种崇高的理念之美,它包含有人本的永恒的协调和健康的情感”。“在这里创造者和被创造者所感受到的是肃穆与庄严,而决非一般意义的赏心悦目”。
这种古板在流行文化时代,让王广义自然地获得了一种悲剧英雄般的守望。当代艺术界很多时候是一个大秀场,艺术家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明星,最怕的是淡出,遗忘。在大众文化的逻辑中,艺术家不太敢奢求公众对自己作品的深度有所体会,反而需要不断地制造色相来满足公众的欲望。你要谈女人,你要谈政治,你要上封面,你要展示你的各种事业线。理论上讲,在文化的快餐时代,谁严肃,谁就输了。
但是王广义就是轴。摩羯座的王广义,严谨、理性,严肃,务实,还带有很强的精神洁癖。在他身上,你会联想很多形象,传教士,修行者,德国哲学家,甚至是黑衣人——正如他欣赏的安迪·沃霍尔被打造成的“黑衣人”。在杜尚和沃霍尔之后的艺术,他仍然坚持用圣·奥古斯丁的话来理解艺术:上帝从虚无中创造世界,而艺术家从虚无中创造艺术。他蔑视大众文化,认为世俗文化是对艺术庄严和神圣的稀释。因此,他说自己不参加时尚活动,拒绝自己成为明星,甚至认为“明星,是一个让艺术家蒙羞的词汇”,言辞之间流露出一种淡淡的愤怒气息。当问及他此生有没有后悔的事,他回答说,今天艺术发展到今天这个样子和他最初的想象不一样。假如他知道艺术发展到今天会变得如此下降,而且一百个同行有九十多个人都认同这个下降,他觉得悲哀。
思想是江湖的本钱
尽管他不想进入江湖,但江湖他玩得转。只不过,这种玩得转不是因为他善于投机,而是因为他的冷静、理性、果敢,他迷恋形而上,但同时又时刻清醒的判断力。他的第一次转型,就掐住了当代艺术史的关键点:从80年代以来中国文化艺术界对西方哲学的迷恋中,走向个体生命和具体现实。王广义说:“所谓宗教和哲学,不是一个决定意义上的东西。在我看来应该和我们的现实,和我生活的情境发生联系。之前我创作的《后古典》系列,完全是宗教和哲学对终极问题的追问,和我的现实经验,和我生活的文化背景是分离的,其中没有生命的关联。所以我创作了打格子的毛泽东,写了《清理人文热情》。在我的青少年时期,我被毛的光芒普照,当然我对毛的描述是一个客观描述。在我看来毛是一个宗教人物,和一般的政治评价是完全没有关系的。所以我选择把一个被偶像化的人,通过我的艺术方式还原成一般的人。”
当他画庄严、肃穆、冷峻的北方极地时,出现一个欣赏他的人;之后他一篇《清理人文热情》,并画出了《打格子的毛泽东》,朝着《大批判》的方向走去,又出现了第二个欣赏他的人;再后来,当市场面对体制的时候,又出现了第三个欣赏他的人。这三个人,基本上是中国当代艺术几个重要转折点上的关键人物。每次转折都甩掉一批人,但王广义却每一步都走在节点上。我们问他,这是不是说明你是很聪明的人——这个问题实际上带有很强的挑衅性。果然,他的反应变得强烈了一点,并且变得具有攻击性。很严肃的说,“你这个问题带有很强的世俗性,我是很自我的人,我只跟我自己在一起。只是在不同阶段、不同人,他在我身上发现了他有兴趣的东西,仅此而已。媒体的逻辑总是假设背后有看不见的手,但事实并非如此。”
但尽管如此,王广义认为他的《大批判》仍然被无法控制的被曲解。根据媒体的需要,王广义必须和裴多菲、 何塞·马蒂、切·格瓦拉这些革命浪漫主义者拉到一起。但他说,他的艺术和“革命”无关:“我的艺术呈现的图像和因素会让一般人立刻想到“革命”,其实是没有任何关系的。我在《大批判》想表现中国是一个标准的乌托邦国家,我认为乌托邦国家对人洗脑是有一个方式,他的洗脑方式是通过宣传画的方式来洗脑;西方社会是一个拜物教传统的国家,而拜物教传统国家是通过商品的设计来洗脑,它会导致人们对商品一种疯狂的追求,典型的像什么ipad的logo让人们很疯狂,我认为这种洗脑方式和乌托邦社会主义国家洗脑的方式一模一样,疯狂程度也相似,其实我想把两种洗脑方式在我的作品中呈现出来。在这里边,我没有态度,我不认为哪个好或者哪个不好,我作为一个艺术家,以中立的态度呈现人类的两种洗脑方式。”
友情与爱情
在试探着怀疑他的尊严、独立的时候,王广义会表现出一种北方人特有的霸气、刚硬。在理性和现实之下,他是一个性情中人。当年闹得轰轰烈烈的法国退展事件,原来也不过是酒后意气。他说他喜欢的男人,就是很“男人”的那种感觉,够意思、仗义,像所有老百姓认为男人之间最高的境界是一样的,此外,他特别强调在思想上有一个相通的东西——这未免有点苛刻。事实也如此,他说自己的朋友越来越少,偶尔有那么几座孤岛和自己可以互相望见,但那个岛上是洪水泛滥还是鸟语花香,他并不关心。
作为当代艺术界的四大天王之一,王广义拥有着被人称道的爱情故事 :1985年结婚至今,家庭稳定。这在风花雪月的当代艺术圈, 特别显眼。谈到爱情,他依然认为,“爱情是一种宿命”,只不过这种宿命,不像前面所说的那么严肃和神圣,而是多了些世俗的人情味。他说“如果我是一个烧锅炉的,这个事就没有什么可说的,而实际上在爱情上,我和那些普通人是一样的。在爱情上,人性都差不多,就是两个人在一起对不对,自己内心都知道在一起舒不舒服,舒服就自然会在一起。”“最好的女人,对于爱情是一种‘认信’,她不了解当代艺术,但相信我,她相信这个男人,即使在当时无法预见我今天的状况,依然相信我。”
回到宿命
经过半生追寻,该江湖的也江湖了,该市场也市场了,对王广义而言,名利都有了。但在他身上,你很难感受到一种功成名就的满足感,他总是保持着一种紧张度。他不会觉得自己的回顾展是一种成就展示,而是宁愿视为对自己的审判。你总感觉,他一生相信的,向往的神圣的力量和超验,总像达摩克利特之剑一样高悬,而他就是在这样的自律中,穿插在生活、普通人、孤独、意志力这些词汇中度过时间,仿佛是某个时代最后的悲剧英雄。
最后问起他和最初的人生观有没有改变,他说依然回到宿命,依然相信自己是古典主义者,依然向往文艺复兴时代。其实艺术,是最能契合这种宿命的方式,因为艺术要提供超验感——通过一个具体的可经验的物体让人突然有一种超验感,这种超验感实际上是一种宗教精神,在特定的天气,特定的时间段,凝视一棵树都会会容易获得一种超验感。所不同的是,年轻时候是相信,而现在是确信,并且并学会了随缘。一个很轴的人,说出“随缘”这两个字,一定意味深刻。他说,生活的世俗和思想的高度其实并不纠结,年少时向往的那些这些神圣的力量没有消失,而是隐含在最最日常普通的生活中——随缘,就是经常会从一棵树,一杯水中忽然发现很形而上的东西,但这又是一种宿命。
【编辑:李洪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