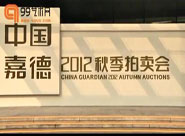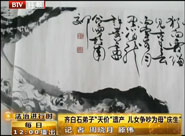杨参军认为,具象表现绘画的方法论的第二个要点,是构成境域。“每个人的观看都有他的主体意识,这种主动性追问:将“知性”悬置,我们还有什么好选择?观看一个杯子,每一个注视它的行为中,意识在不断流动。这个杯子在刚才、现在、以后呈现的样子,一直在变。天气在变,光线在变,一切都在变化。贾克梅蒂的伟大之处不在于他描述了杯子,而在于他明知道这个杯子不可描述,却还非要将它描绘在画布上”。要知道,艺术家在做这样的审美劳动时,不是在炫耀技法,而是在向共同体成员示范新的观察和审美方式,是在将艺术形式,转化成共同体的生活形式----这正是作为艺术自治和纯艺术倡导者的诗人马拉美对艺术所抱的最高理想!艺术家是审美探路者,是在将本来被认为不可感知、不可描述的东西,感知和描绘到画布上,让其余的共同体成员去接手!
第三个要点,是其未完成性。杨参军认为,未完成性体现为复去表现某个主题。像贾克梅蒂,把一张头像画得没完没了,十八次,第二天又抹掉重来。阿希加则是一次画完第二天又重新开始。画面上的未完成因素,成为呈示对象,反而展现了某种生成的因素,在不断的探索中,去发现新的可能性。具象表现主义作品的这一未完成性,召唤新的审美共同体成员的到来。它不是一种个人现象学反思严格性的反映,而是艺术家的一种积极情怀:给共同体的新到来者预留着位置,为新的共同生活创造出崭新的形式。
总之,对于中国具象表现绘画艺术的历史定位,完全取决于我们对于现代主义及其先锋派的艺术实践的理解。我们在这方面的以前的理解,可能是有问题。朗西埃最近对于我们的这种过分清高的现代主义态度的批评,会拓宽我们对于像具象表现艺术实践的理解。现代主义范式下,艺术自治是唯一目标。但是,哪怕是第一代现代主义艺术家如马拉美们,也是将诗当作共同体的新的邮戳,将绘画当作新的大艺术的科学基础。他们将纯形式当作建构共同体大厦的块件,从新生活里去找出它们。他们想要实现诗、绘画和音乐的同步。他们寻找一种新的精神性。这一现代主义倾向,可被称作马拉美-马勒维奇-苏哈(Seurat)-蒙德里安或勋伯格序列。象征主义、至上主义、共时主义、未来主义、构成主义和超现实主义汇合,其共同任务是:建构一个新的感性世界。[2]这一点也值得具象表现绘画艺术家们认真记取。
具象表现绘画艺术只有在下面这一意义上,才真正构成一种当代艺术实践:成为新审美共同体内的一种元政治,去不断影响共同体内的集体感性的重新配方,不断将与艺术无关的东西硬塞到艺术中去,一次次地去打破刚建立起来的艺术与非艺术之间的边界,使艺术向无限的可能性开放。
二、具表与抽表之争:另有怎样的故事?
1984年之后丹托所反复鼓吹的艺术终结论里,抽象表现主义和德国的新表现主义,成了反面角色。对于当代具象表现绘画实践的评估,所以,也必须建立在我们对丹托的这一影响深远的艺术终结结论的重新评估之上。
在丹托提出这一艺术终结论时,格林伯格的的保守立场仍是主流:波洛克这样的抽象表现主义者和艾列娜.德库宁这样的具象表现主义者,代表着现代主义的正宗,因为他们对自己的方法论自我批判更严格,不重复别人的方法和套路,而这,据格林伯格,才是“现代主义”的精神核心,而波普和极少主义,只是一种“趣味”。[3]而丹托的结论则刚好相反:抽象表现主义者和具象表现主义者们的实践是徒劳和无望的,是对现代主义的狗尾续貂,最后的还有点意义的探索,是波极少主义,那两样之后,就没有别的先锋了,一切听便了。
丹托认为,艺术终结了,意思有两个:艺术终于自由了,艺术再不要哲学家来管了,艺术其实从此可以彻底不哲学了。艺术从此可以爱干吗就干吗去了。同时,当代艺术也可以不服欧洲现代主义艺术史的管束了。他认为,他是从波普和极少主义那里看明白了这个道理。被扔在垃圾堆里的鲜亮的可乐罐也常向我们一闪,使我们终于也拿不定主意、不敢就直说它不是艺术品了![4]
而艺术终结后的状态,就是我们今天的艺术状态:它叫当代艺术!什么是波普?波普是艺术终结时代的最后一种艺术形式。它终结了我们对于艺术的本质和意义的追求。艺术家咬紧牙关,从此死也不肯做哲学家了:他们波普了。艺术家通过做波普来解放自己;波普的意思是:艺术家只做艺术,不要美学(它是哲学派过来对付艺术的),也不要哲学。在波普中,艺术家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从此再也没有纯艺术的标准例子。艺术品应该看上去是什么样子的,谁也休想来告诉我。艺术?还是非艺术?这不是视觉上的问题,而是个概念上的区别,无关紧要了。
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突然繁荣起所谓的新表现主义绘画,到了中期,又退潮了。突然,不再发生任何艺术运动。20世纪上半叶经历了数十个运动——立体派、野兽派、构成主义、至上主义、未来主义、达达、超现实主义、表现主义、抽象艺术等等——每一个运动都有自己的宣言。所有这一切都消失了。艺术史不再受到某种内在的必然性驱动。人们感觉不到任何的叙事方向。
波普之后还有艺术?我们怎么来理解今天的人们在鼓吹的“回到绘画”和“纯艺术”?这是中国的具象表现绘画艺术实践者们必须回应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
最直白的回答是:同时与格林伯格现代主义接续论和丹托的艺术终结论保持一定的距离。但如何来保持这种距离?具象表现艺术家们如何在接续论和终结论之间走钢丝?
对于中国具象表现艺术家们而言,保持这一距离,第一个需要警惕的,就是他们与哲学现象学的关系。他们必须非常警惕着终结论和接续论地来说清自己与哲学现象学之间的关系。
终结时代里,艺术就完全有自由用不论何种手段去追求他们自己或他们的赞助人认为重要的目标了。从那一点上开始,再也没有内在艺术的历史方向了,而这恰恰是多元主义的状态。艺术如今终于得到机会从哲学的压迫中解放了出来。而哲学本来做的也应该是这个:帮艺术去实现它的自由。哲学和艺术的共同叙述,哲学史也好,艺术史也好,应该是一部自由小说,我们终于被自由放飞了。
具象表现绘画艺术家们最终必须把哲学现象学吸收到自己的工作方法和之后的方法论辩护中;与现象学的这种邂逅,最终必须成为他们的工作进路,而不是沉淀为几条思考和观察原则。进一步说,他们与现象学家和哲学家的关系,是同路人之间的关系。具象表现绘画艺术家们必须既甩开欧洲艺术现代主义先锋传统的规训,又放弃从柏拉图以来哲学对于艺术的指导。他们与哲学现象学、与哲学家们的关系,应该像是一对结婚时互相斗角,闹得满城风雨,离婚之后反而成了知心朋友那样的男女。
实际也许应该这样建议:具象表现艺术家们与哲学家或哲学现象学的关系,应该跳出哲学家巴迪厄所说的、在艺术圈中最流行的“心理分析大师与情妇”关系:艺术家出作品,哲学家来分析,然后艺术家拿了哲学家的分析方法,再去当方法论用,用过了,再来与哲学家交流;艺术家向哲学家讨要如何达到快感的方法,老不得逞,后者成了前者的闺蜜或小三,造成了不正当关系。到放弃这种艺术与哲学的古典关系的时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