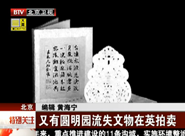一、多年以来,作为一个哲学工作者,我一直在想念尼采的一个问题:艺术、哲学与生活之间如何可能有一种意气相投的关系?尼采设问时的意向极为显赫:艺术与哲学应该意气相投,而且唯当两者亲密有间——亲密而又区分——时,生活才可能臻于美好。或问:人类何时有此良辰美景呢?尼采答:惟有古希腊“悲剧时代”,之后就失了“乐园”。那么,失乐园之后怎么办?正是揣着这样一个问题,当年我与陈嘉映教授一道进入中国美术学院,与许江教授、司徒立教授等艺术家共同创建了中国美术学院艺术现象学研究所,一晃竟然十年多过去了——我想,是到做个小结的时候了。
然而,我和嘉映教授也只是半途加入的。其实在此之前,在1990年代初,华裔法籍的司徒立教授即开始在中国美术学院开班授课,引介被认为具有现象学倾向、主要起源于法国、并且被命名为“具象表现绘画”的创作方法论。因此,中国美术学院的具象表现绘画实践,严格说来已经有20年的历史了。20年弹指一挥间,而对于中国美术学院油画专业的许多师生们来说,却是一场艰难困苦的身心磨砺。个中甘苦,持久的心灵肉搏,旁观者是无法完全体察和计量的。
而我,差不多也还只是一个旁观者——诚然应该说是一个近距离的旁观者。记得1998年12月底的一个晚上,由高士明博士接洽,我第一次进入中国美术学院油画系(当时的美院尚未改建,油画系还在一个老旧的矮楼里),做了题为《我们如何接近事物?》的演讲。正是在这次演讲中,我结识了许江教授等美院艺术家。接着,约半年后的夏天罢,我在美院大门口与司徒立教授首度会面。之后我去了德国。2011年回国后,一次西子湖畔的五人聚会(有照片为证),才有了中国美院艺术现象学研究所的艺术与哲学的长期合作。
看起来,我们的合作仿佛有着一种严重的不对等:我(以及嘉映教授?)对于艺术的了解,恐怕是远远不及美院一些艺术家对于现象学哲学的探讨和理解的。再说了,想法人人都有,手艺却并非个个具备。因此,如果说对于具表艺术家来说,他们多年纠结的问题是:什么是现象学?那么对于我来说,更大的难题恐怕在于:如何理解具象表现绘画?
二、什么是具象表现绘画?在此标识中,“具象”与“表现”这两个核心词语之间具有某种不兼容性,甚至是相互矛盾的:“具象”指向写实,偏于客观;而“表现”倾向于抽象,以主观为重。这两者如何可能结合起来而成就“具象表现”呢?在多个不同的场合,我曾跟司徒立、许江教授等艺术家讨论过这个问题。司徒立教授是坚持“具象表现”这个名称的,记得有一次,他高调地反对把“具象表现绘画”“主义化”的建议。司徒教授认为:“具象表现”不能单纯地被理解为一种“主义”,一种“风格”。“风格化”并非“具象表现”艺术家们的追求,正如海德格尔所言:现象学不是一个“学派”。
那么,这个“具象表现”,这个“具象+表现”,到底是什么?一个比较狡滑的、但万无一失的解释是:它既非具象又非表现,或者,它既是具象又是表现。
听起来有点荒谬。我则愿意认为,这样一种“既非-又非”和“既是-又是”的说法并非无话可说、说不上来的遁词,而是合乎实事本身的表述。因为,我们时代就是这样一个“既非-又非”或者“既是-又是”的时代,令人困惑、令人纠结;因为,我们时代的思想文化具有前所未有的歧义性质和动荡特质,恰恰可以用“既非-又非”或者“既是-又是”来加以表达。就此而言,至少就“具象+表现”名称而言,具象表现艺术是合乎时宜的、是有当代性的。
“具象”与“表现”可以被看作艺术史钟摆的两极。具象、写实艺术具有古典渊源,有着一个古典哲学的存在学/本体论预设,即关于外部世界、外部事物的实在性和恒定性的假设。这个预设其实是一种自然而然的信念,也是作为“自然之子”的人类秉性中固有的品质,即与自然的契合感和对自然的敬畏感。而广义的“表现”主义艺术则倒向了另一极,转向自我、主观、抽象的一极,它同样有着一个近代以来的知识论哲学的预设,即关于自我/主体确定性或者说内在世界的恒定性的假设。这个预设尤其是19世纪后期以来具有主体主义倾向的现代主义艺术的基础和前提。单纯地模写外部世界与狂热地抒写主观体验,这构成艺术史上具有时代阶段性印记的两种极端的艺术倾向,恰恰对应着哲学史(思想史)上从古典向现代的过渡——这种现象,可称为艺术与哲学的同步同调。
如果说艺术上的浪漫派和印象派终结了近代欧洲由文艺复兴运动恢复起来的古典艺术理想及其存在学/本体论预设,那么,经过包括表现主义在内的现代派艺术思潮对主体性和自我性的极端张扬之后,艺术史钟摆的另一极也岌岌可危了。艺术被逼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困境里:在“具象”与“表现”之间,艺术仿佛无所依傍了。在被动摇了的两“极”之间,在同样被置疑的物与我、世界与自我之间,同样也可以说,在达·芬奇与毕加索之间,艺术不知所从。
具现表现艺术由此入思,同时,在现象学特别是后胡塞尔的现象学那里,它找到了同道知音。
三、海德格尔说现象学是“思想的可能性”,而当安瑟姆·基弗说丢勒是一个现象学家时,他的意思恐怕是:现象学更是行动的可能性。现象学是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所以不仅是哲学的,也是艺术的;现象学不仅是用来“想”的,更是用来“做”的。当然,“想”与“做”也总难分。况且今天的情况是:思想是做出来的;做出来的思想也被叫做艺术。
就作为思想的现象学来说,它的基本品质(气质)是什么?在去年一次会上,我用四个词语来加以概括,谓之:“直接”、“务实”、“虚怀”、“专心”。“直接”是很难的事,因为中介太多了。现象学的直接性要求表现在看、说、做多个方面。胡塞尔强调“看”的直接,海德格尔则进一步,说到了“做”的直接(所谓“实行意义”优先)等等。“务实”本是现象学的原则“面向实事本身”,用不着多讲。“虚怀”呢,就是要放下架子了、放下包袱,为非理论化的事与物留一点空间,也可以是说,要对哲学和科学之外的解释可能性保持开放心态。所谓“专心”,我差不多愿意用威廉姆·洪堡对大学的要求“孤独、纯一”(Einsamkeit)来解释,洪堡说大学需要Einsamkeit,这个要求很好——现在的大学像个养鸡场,哪有对于事与物的专心了?
以上四个词语,是我目前对于现象学精神的设想,即是由“想”的现象学引出来的姿态和立场,而且显然,更多地是在海德格尔现象学意义上来讲的。而说到底,我所谓“做”的现象学其实也不新鲜。胡塞尔就说过现象学是“工作哲学”。在早期海德格尔那儿,现象学更是“做”字当先了。到这一步,哲学和哲学家就有点守不住自己了,因为要说“做”,艺术家们(广义的)更能“做”。
“做”的现象学即艺术现象学,甚至就是艺术,它不但是与材料相关的“做”,也是与观念相关的“做”——是做观念。它做了一个隐约的预设:用造型的元素表现观念是更有力量的。在新近出版的一本访谈录《艺术在没落中升起》中,安瑟姆·基弗集中讨论了五大“基本元素”,谓“火、水、气、土、空”,认为他的艺术就在做这样一种探索,是做五大“基本元素”的。基本元素的探讨难道不是哲学的事业么?现在怎么成了艺术家的工作?基弗会反问一句:谁说“基本元素”只配“想”而不能“做”?——诺,依然是艺术与哲学之关系的老旧问题。
我不想说当代艺术就是现象学的,而只想说:艺术现象学,或者我们今天看到的具象表现艺术,既是“想”的现象学又是“做”的现象学。
我于是也为自己莫名其妙的策展人身份找到了依据。
【相关阅读】
【编辑:于睿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