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篇图
王静:您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是颇具研究价值的“新刻度小组”成员,您今天的作品思维方式具有“新刻度小组”时期研究方向的延续性。因此今天的对话,我想从您的小组艺术创作开始,谈一谈“新刻度小组”的一些工作方式。当时是什么样的创作背景,“新刻度小组”的前身是“解析艺术”还是“触觉艺术”?
王鲁炎:“新刻度小组”的前身是“解析”,“解析”之前是“触觉艺术”。“新刻度小组”的理性艺术方向,与当时的非理性潮流相悖,是一个十分独立的艺术现象。“新刻度小组”的工作方法是通过合作制定规则和严格执行规则,小组的所有决定都需要通过讨论。
王静:“触觉小组”、“解析小组”和“新刻度小组”,这三个不同名称的小组,在方法上互相之间都是有联系的?
王鲁炎:它们在观念上是彼此独立的,在方法论的某些方面具有一定的相似性。“触觉小组”成立于1988年,由我和顾德新组成,“触觉艺术”是以非感官触觉方式的观念方式的“触觉艺术”。“解析小组”成立于1989年,由我和顾德新、陈少平、曹友廉、李强、吴讯六位艺术家组成,对数学意义的“点”进行测量,是“解析”作品的观念与方法。“新刻度小组”从“解析小组”开始(1989年),于1995年解散,其艺术观念与方法是取消艺术家的个性。
王静:艺术的内容和方法具体包括什么?
王鲁炎:艺术家的艺术观念或者情感内容需要与其适应的艺术载体,在艺术家都有话要讲的情况下,用什么语言以及如何讲构成了艺术的交流意义。艺术交流的过程,可以使我们知道艺术家想要表达的内容和艺术家运用语言的方法。所谓的艺术性,既是观念意义的更是语言意义的。艺术家欲要表达的内容通常需要艺术语言的转换。
王静:您刚才多次提到交流,我看到以前的一些资料。在“解析”艺术,包括之前的“触觉艺术”阶段。你们比较多的强调规则化的创作方式,要去掉艺术家的个性。在“新刻度小组”看来,艺术个性与艺术作品的关系是什么?
王鲁炎:艺术交流一直遵循着一个铁的法则,那就是相异而不是相同。艺术家作品的内容与方法须是排他和不同于以往的,艺术史和博物馆的存在,即是告知艺术家无权再重复艺术史与博物馆中已有的东西。众所周知,艺术是从个性出发的。“新刻度小组”试图通过取消艺术家赖以存在的根本——个性,达到在个性之外的艺术思考与实践,使区别更为接近本质。艺术的个性须是彼此不同的,“新刻度小组”的艺术个性,即是取消个性的个性。这一点与从个性出发的艺术不同。
王静:那作品的最终呈现方式可能比较注重规则,强调理性的线,会使用一些测量仪器。这种对规则的共识好像是一个推演的过程,需要放弃很多既有经验。
王鲁炎:对,这是一个逻辑递进的过程,这一过程的选择与推演与我们的个人好恶无关。原因在于“新刻度小组”作品的逻辑起点是取消艺术家的个性,所有负载个性的因素都是取消的对象,而所有能够取消个性的方法,则是“新刻度小组”选择的对象。这一理性方法的过程,使艺术家原有的艺术经验失效,是对艺术家个人的任意性选择与自由的否定。这也是“新刻度小组”从最初的六个人变成了四个人,又从四个人变成了最终三个人的原因。
王静:你们在艺术上的进展,或者在艺术观念上的理性思考和信念,四个人时期的你们是否已经比较坚定?
王鲁炎:相对坚定,但是四个人时期的“解析”小组,存在艺术价值观念的分歧。我们选择了已有艺术经验之外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已有艺术经验不仅失效,我们的艺术观念与方法还会因此存在“这还是艺术吗?”的质疑。我和陈少平、顾德新发现,“新刻度小组”的艺术方向从一开始就已经既定了,它的最终价值指向是彻底取消艺术家的个性。这是“新刻度小组”艺术实践意义的最大值,其他的都是附加值。而就在这一点确立之后,“新刻度小组”内部产生了很大的分歧,其中跟随“新刻度小组”时间最久的艺术家曹友廉,坚决反对取消艺术家的个性。他强调个性不仅不应取消,反而应该加强。并认为任何艺术的表达都是一种个性,取消个性是不可能的。个性是艺术家赖以存在的最为根本的东西。
王静:他是因为在讨论的过程中,意识到小组的未来可能指向的方向,与他个人的艺术观相左,所以他选择了离开?
王鲁炎:友廉离开的主要原因,在于取消艺术家个性的艺术观念,超越了他的艺术价值观念底线。每一位艺术家的内心深处,都会存在不可超越的艺术价值观的底线。我和顾德新、成少平通过“新刻度小组”的艺术实践,不断超越各自的艺术价值观念的底线。“新刻度小组”最终呈现的结果,就是我们艺术价值观念底线的极限。
王静:陌生的艺术领域也是您非常希望到达的地方。
鲁炎:在熟悉的领域里,不会有陌生领域中的探索与发现。因此,在共识性经验中,艺术家没有理由有太多的自信。艺术家自己无法认知和判断的东西,属于超验的东西。艺术家的探索,如果使自己进入到陌生、孤独、不解和充满敌意的处境是好事。艺术家长期处于已有经验和熟悉的领域之中是危险的,这意味着你已经停止了探索的脚步。实验与探索性的艺术如果马上被普遍接受,很可能说明该艺术尚在已有经验之中,属于走的不远的东西。真正实验与探索性的艺术的初始阶段,经常会在不解与敌意之中。
王静:最后留下来的三位小组成员,对于“新刻度小组”的艺术观念与方法是坚定的,这种自信来自于什么?当时批评界、策展人们怎么看?
王鲁炎:1990年,我们“新刻度小组”与批评家高明潞、范迪安、孔长安、殷双喜、周彦、侯翰如等人,在“新刻度小组”工作室举行了作品观摩和讨论。“新刻度小组”的理性艺术观念与方法,走了与当时的中国当代艺术主流方向完全不同的路,引起了批评界的关注。我们当时的自信程度,已经强大到不在乎外界的否定或认同。事实上,“新刻度小组”取消艺术家个性的艺术观念,与极端理性的艺术方法难以令人接受。常有西方策展人在听取我们陈述艺术观念与方法的时候打哈欠看手表,十分不耐烦。我们经常面对各种质疑与挑战,而这是我最为自信和兴奋的时期。因为取消艺术家个性的艺术观念,与极端理性近似于数学的乏味枯燥的艺术方法,已经超越了许多人的艺术价值观的底线,甚至令许多“专业人士”不解和厌恶。直到1994年至1995年,“新刻度小组”的展览机会不断增多,我的兴奋才逐渐减弱。
王静:当时“新刻度小组”的日常讨论和创作,艺术家可以发挥的空间是什么?就是在一张纸上,到底是用尺子还是用圆规,制定的是什么规则?
王鲁炎:参与“新刻度小组”艺术创作的每位艺术家必须通过合作制定规则和执行规则,其作品呈现方式、创作工具、纸材和尺寸都是被规则严格规定的,没有艺术家个人意义的任何发挥空间与自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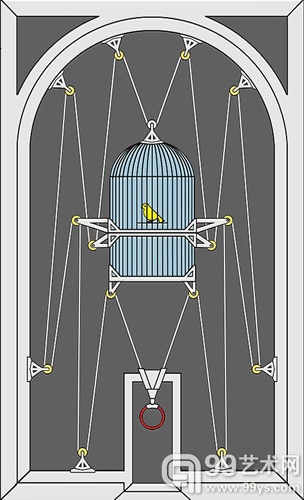
鸟笼
王静:所有环节都是规则化的。
王鲁炎:对,“新刻度小组”是规则化的,甚至制定规则的方法也是有规则严格规定的。因为,取消个性的前提,要求取消个性的规则从一开始就是非个性的。如果规则存在着个性的漏洞,执行规则之后发生的一切都没有意义。
王静:创作下一件作品的时候,你们可能会重新制订一个新的规则,产生不同的方法。
王鲁炎:“新刻度小组”历时近八年,完成了“新刻度小组”作品1——5。“新刻度小组”的每件作品都有不同的规则域方法,但结果都是取消艺术家的个性。“新刻度小组”取消个性的方法,一直处于对“严格”、“有效”的不断探索与完善中。“新刻度小组”作品——5的规则,是最为严格有效的取消艺术家个性的规则。“新刻度小组”作品——5的完成,意味着“新刻度小组”艺术观念与方法论的实现,也使得“新刻度小组”从此面对是否继续存在的问题。
王静:您说“新刻度小组”作品方法论中始终使用数量关系指的是什么?
王鲁炎:由数字、表格组成的载体系统我们称之为“数量关系”。我们发现“数量关系”是一种极为抽象、纯净的载体,它不负载任何人文热情、情感表达以及美学意义。因此,“数量关系”被“新刻度小组”作为取消艺术家个性的主要手段之一。
王静:在方法论上,“新刻度小组”有着独立存在的价值和贡献
王鲁炎:“新刻度小组”的特点在于历时八年共同完成同一个作品观念与方法,呈现了小组艺术的不可替代性。“新刻度小组”不仅提出取消艺术家个性的艺术观念,更注重探索取消艺术家个性的有效方法。在表达艺术观念的同时,呈现艺术方法的价值与意义。“新刻度小组”的艺术方法论,通过执行规则时的表格记录与对表格的“校对”,涉及到了作品的“对”与“错”问题。“新刻度小组”作品从墙上转入书中,使作品只有通过阅读方可呈现,从而取消了作品的原作概念。“新刻度小组”将合作上升为核心艺术观念,同过合作制定的规则不再是个人制定的个性化规则,使取消艺术家的个性成为可能。以上都是“新刻度小组”艺术方法论的特点。
王静:“新刻度小组”在上世纪90年代,坚守前卫艺术的精神性与纯粹性。因此才会有“新刻度小组”的解散。现在回看“新刻度小组”的历史,您怎么看那个时期的艺术探索?意义是什么?对今天的当代艺术是否仍然存在参照的价值?
王鲁炎:“新刻度小组”从制定规则到执行规则,始终遵循着艺术自身的理由,不会做任何策略性的妥协或让步。所以,在“新刻度小组”完成了其艺术观念与方法之后,解散的决定不会因为古根海姆美术馆的到来而改变。决定销毁历时八年累积的大量手稿,也不会因为市场的机会而保留。“新刻度小组”精神性与纯粹性的存在方式,是取消艺术家个性即是取消艺术家个人权利的逻辑所决定的,也许这种绝对性仅适用于“新刻度小组”。
王静:在当下的创作语境中,理性的创作观念仍很稀缺。
王鲁炎:从艺术史层面上看,感性艺术的世界辉煌灿烂,而理性艺术的世界却还是一片黑暗。更多的艺术家存在于丰富的感性艺术世界里,在感性艺术世界里不差我一个。对我来说艺术是大脑而不仅仅属于感官,艺术完全可以成为一种通过视觉达到的精确思维方式,我的兴趣在于艺术中的理性。
王静:“新刻度小组”所触及的理性方法和可能性,在您个人的艺术道路上又有了哪些变化?
王鲁炎:我个人的艺术承袭了“新刻度小组”的理性精神。我的艺术世界观是:论证的视觉。
将事物关系中不可视的悖论,转译为可视的悖论视觉形态,使视觉成为思辨与论证的视觉思维方式。我的艺术方法论是:刻度化的手工。使用度量工具创作的“手工”已经被工具刻度化,刻度化的“手工”是悖论意义的非手工的“手工”。
王静:您现在的作品把齿轮、表、注射器这类具有理性规则的物品视觉化,仍是理性艺术或规则艺术系统的延续?这个系统自“新刻度小组”时期开始,当您把这种逻辑思维转化成不同媒介作品的时候,一动手似乎就是有针对性的?
王鲁炎:我的作品是关于视觉论证的,显然属于理性艺术。我在“W腕表”、“W注射器”、“W自行车”、“W枪械”等系列作品中,表达了日常话语、社会学以及政治、军事等内容。但更为重要的是,我表达这些内容的方法是“艺术”方式而非哲学或社会学方式的。我借用腕表中的齿轮逻辑,表达了国家之间政治军事的关系,即齿轮逻辑你动我即动的联动关系。我用四颗“W注射器”,分别负载了四种社会关系——等价交换关系、不等价交换关系、抚慰何双重标准关系等,我所设计的“W枪械”,通过正反装弹,双向同时发射,揭示了杀戮的逻辑不是杀戮与被杀戮的关系,而是杀戮与杀戮的关系。我的“W自行车”向前骑时向后走,只能去往你不想去或者相反的地方。我借用不同的媒介负载不同的内容,揭示事物的相同关系——悖论,呈现艺术视觉方法论的价值与意义。
王静:从您个人的艺术线索看,您在“新刻度小组”时期关注的艺术方向与现在相比,加入了很多对社会性问题的立场和思考?
王鲁炎:我对社会性问题的思考兴趣是视觉方面的。我试图将思想的深刻性转换为视觉的深刻性,这是艺术家与思想家的区别和各自存在的理由。
王静:任何人都无法百分之百地接近作品价值的所有可能性,包括艺术家本人在内。
王鲁炎:对,开放性的当代艺术作品就解读而言具有N种可能。所以“错度”是艺术交流中的普遍存在。也正因如此,艺术家对待自己作品的态度才会有阐释和拒绝阐释的区别。
王静:您是否阐释作品?
王鲁炎:经验之内且普遍共识的感性艺术易于理解,通常不需要过多的阐释。而思辩、论证且关系转换的理性艺术晦涩难懂,需要必要的理论阐释。我的作品属于后一种,因此不得不对作品进行阐释。阐释作品与不阐释作品,都各自具有学术性的艺术理由,没有孰是孰非的问题。
王静:艺术的合法性根据与其相应的参照系,以您对艺术的理解,美术史的价值似乎是一个很重要的参照标准。
王鲁炎:刚才谈到过,美术史与博物馆的存在价值,在于它为后来的艺术实践建立了不可模仿的参照。不明白这一点的初学者,阅读美术史或参观博物馆的动机在于抄袭和模仿,而这正好与美术史与博物馆的内在逻辑相悖,因此永远不会有进入美术史或博物馆的未来,除非去做与其相悖的事。
【编辑:赵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