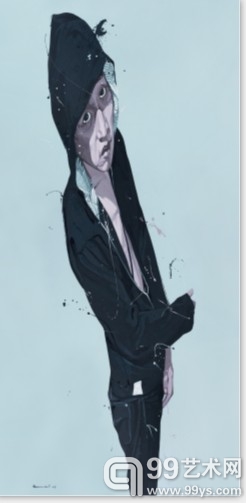
郭伟 无题No.12
布面丙烯 300cm×150cm
2008
不过,郭伟很快想再次逃离“陷阱”。1992年,他开始实验红色的人体。《室内三个纪念物》表现出之前和同时没有彻底放弃的桑多费式的超现实主义,但是,他开始强调肉体与支解的残酷特征,而不注重朦胧的戏剧性。在《战士NO.1》里,画家同时还安置了鹦鹉,这容易让我们想到之前的“死鸟”。的确,如果说之前的“包扎”系列在视觉上带给观众的更多的是戏剧性的恐惧感和距离感,以及精神上的疏离感,那么这些“红色基调”的作品中则似乎更关注某些具体“情境”和日常的细节。以后艺术家在谈到不同时期的风格的对比时这样说道:
“……最初的包扎是比较文学化的,有较强的象征性和暗喻性,这些特征应该说一直被我保留着。后来的想法是希望作品更加视觉化一点,所以在作画手段上作了一些改进,譬如通过增加肌理的办法使作品具有一定触摸感,用有凸形的线条来改变原来包扎中的一次性画法,空间处理上更为具体而原来包扎中的绳子则被我抽象出来成为覆盖画面的抽象因素,加强画面的“气力”,至于由黑白色调转变为“红色素描”也主要是考虑加强画面的力度,杜绝画面有可能产生的愉悦气氛,这恐怕是我对当今社会一切崇尚“消费”、“娱乐”的一种逆反心理,应该说我近期这批“红色素描”是“包扎”系列的逻辑延续,精神倾向并无二致。”——艺术家自述
无论如何,1992年,红色的人体出现了,郭伟将在成都的艺术家们的肌理和美学趣味保留了下来,并进行改造,他想尽可能从自己的感受中发现方法上的可能性。的确,从1993年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郭伟受培根(Francis Bacon,1908—1992)影响了一段时间,他在作品中掺入了一些表现和综合材料的实验。在部分作品里(无论是灰色调子还是红色的调子),我们可以看到郭伟分享了同一个城市里的其他画家——例如周春芽等人——对肌理的技术性处理,但是,郭伟在作品中保留了明显的对培根美学的敬意。之后,从培根的影响下脱离出来,“浸泡和类似游泳的人物形象成为他这个时期的语言核心,或者说人浸泡在水中成为他对人和生存关系的一种隐喻,深蓝色的水与烧烤般的焦红色的人体形成强烈的对比,使画面有种恐惧和不安的感觉。”4 看得出来,这个时候的郭伟没有理会来自北京(“玩世现实主义”)或者武汉(“政治波普”)的影响,他的生活环境与个人日常生活没有唤起他对开始流行的风气的接受,在精神气质上,他与其他一些年轻的画家的确继续承受着“伤痕”的余震。
然而,影响肯定是存在的,在趣味与大的语境上,郭伟必须做出选择。所以,在1994年的作品里,人物不在仅仅是支解的,而有了在水中嬉戏的内容。背景多多少少缺少了玄奥的气氛。郭伟的注意力逐渐转向了人与人、人和社会的关系上。像“游泳”系列,包括《正午》、《入水》、《艺人》等。不过,他保持了绘画性和焦虑心理结合的特征,比如游泳池,提供“热”这样一种焦灼的特征,“嬉戏”的内容与情绪,修改了“培根式的”严肃与紧张。
从1994年起,郭伟的作品主题基本围绕着人物题材展开,而且,作品的主题形象大多是儿童和少年。“我喜欢画画,又特别喜欢画小孩,因为他们歪瓜劣枣,无事生非,扭扭捏捏,而充满活力有意无意地扮演着。他们的状态令我兴奋。在我的作品里这些孩子更像是一些演员,他们在扮演自己,也在扮演别人,他们扮演成人也扮演小孩,他们扮演好人也扮演坏人,他们扮演男人也扮演女人。总之在我的作品中他们在扮演着总之‘人’才是我最感兴趣的主题。”但是,在表现内容上,郭伟的画并不只是要再现昨日的时光,作品中的人物,其实都是他刻意寻找和选择的演员,他对待这些人物形象的态度,漠然,近似毫无表情,有时甚至就像对待静物。可以说,郭伟只不过借用这些人物形象在讲述当代的故事,而这些故事,像散文一样,结构不明、情节不清、语焉不详,却主题明确。
90年代中期以后,郭伟真正开始转向对日常生活的关注。他彻底接受了由“新生代”、“玩世现实主义”和“政治波普”唤起的对现代主义本质主义的置换。的确,1992年之后,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与社会思潮有关的、轰轰烈烈的,无论是政治的、还是艺术的运动都过去了,消费文化的改变和发展,影响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使人们的生活变得愈加琐碎和日常化。艺术家的创作视点也开始投向日常生活中。另一方面,此时的郭伟已经有了自己的家庭和女儿,一种“家”的观念已经列入到他的思考范围。看着自己的女儿一天天地长大,他沉浸其中。对于他这样一个过着正常家庭生活的职业画家而言,生活的单调和无聊,不仅不会使他感到厌烦,却给了他一个创作的机缘——他常常会注意到自己生活中的细节,并能引发自己的创作的灵感。这成了他生活和创作中的重头戏。因此,观众可以发现,郭伟将关注的中心集中到自己女儿和与女儿差不多年龄的小朋友身上。他画出了在这个时期的孩子们的调皮、多动、好奇、无事生非,同时也通过对这些孩子的描绘,表达出了生活在极其日常化的琐碎和无聊的现实世界中的人们(包括他自己)的“无常感”——总观郭伟的作品,在形式方面,他似乎一直沉迷于一种他自己所理解的“简约主义”:静止的时空世界里,色彩单一、情绪模糊的人物形象,不温不火地做一个动作,或者静止在那里,无形中传达出一种对现实生活的无奈和戏谑。所以,到了1998年,郭伟几乎终结了容易导致焦虑和不稳定情绪的“红色”系列。
1998年以来,“稳定”成为郭伟作品中主要元素——这与他近年来的心态有关。作品的发生空间基本设定在室内,色彩的使用也被减少到最低限度,“在他刻意经营的室内舞台上,他的演员基本上是一群由童年向少年过渡的孩子们,他们有时孤独落寞,有时专注沉思,更多的时候,他们在没心没肺地尽情游戏着,肆无忌惮地挥霍着最漫长的人生假期”5,幼稚与成熟并存于同一时间,无聊和正常发生在同一空间。一群百无聊赖、无所事事,却似乎心事重重、信心十足的孩子,处在一个矛盾而又让人无语的场景中,或扮酷、或撒泼、或发呆、或无奈无形中强烈的视觉体验从观众的心底碾过一道沉重的痕迹。成年人一定是理性通达的吗?孩子们一定是天真无邪的吗?童年都是由甜美的回忆构建的吗?长大是痛苦的还是快乐的?一个又一个疑问使观众失去了理性判断的方向,大脑的思维在郭伟的作品面前变得已无缚鸡之力。凝视郭伟的作品,人们的判断力失去了自身的方向和自信,思维定势也被动摇和颠覆。
直到1996年前,郭伟在技术步骤上“喜欢直接在画布上构图,用丙烯颜料起稿是因为它易改动,很方便。当构图定下来之后,再用立德粉、乳胶做底,并用医用针管挤出所需的凸形线条,再用丙烯深入,最后用油画颜料润色,色干后用较锐的工具刮出一些凸形线,有时在画的过程中,也用一些网状物来拓些点状,以消除一些较流畅的笔触”。6
三
我又一次修正自己对作品的处理方式,将色调再次回到相对柔和的黑白灰。还是希望让观众的眼光投向画面,避免了让画面砸向观众眼睛的粗暴行为。画面上常出现两个人。他们看上去好像有关系,却又像没关系。就像是有情节而无故事,或有故事而无情节的荒诞情景剧。俯视成为这一时期的唯一观察角度。观众也成为一个窥视者。画中有被窥视的人物,也有用表情来调戏观众的形象。这一些都是在平静中发生。总之人是我最关注的东西,他们从未离开过我的视线。而“小孩”是我作品中很大一部分素材。他们最本能的体现出人的状态。有时候真实得像假的一样。(艺术家)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玩世现实主义”或“泼皮艺术”作品中,被艺术家“具体化”的人往往是以“非人格化”、“非人性化”的态度和形式出现站在观众面前,产生的结果是,真实的人最终还是成为演绎抽象理论、表现抽象观念的工具,失去了其本身的客观存在的意义。90年代中后期的当代艺术开始呈现纷繁而不统一的特征,作为“玩世现实主义”和“政治波普”混合的结果,产生了“艳俗艺术”。事实上,被称之为“艳俗艺术”的现象不过是后现代主义立场的滥觞,之后,艺术家再也没有创造、跟随任何潮流,个人生活与特殊的语境决定着艺术家的态度,郭伟更加将注意力放在自己熟悉的环境与对象上。
艺术家告诉我们,他的作品的图像来源,尤其是近作中的人物并不是根据写生,而是根据摄影图片改画出来的——有的是他请人摆拍的,有的是他在生活中抓拍的,有的是他从画报上拿来借用的。在这里,被故意强调的突出的透视特点,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他画面上的陌生化效果。正如我们所见,郭伟近作中画的都是当下处于青春期的另类青少年肖像——有时是一个人,有时是多个人——但与传统肖像画家追求个性表现不同,郭伟总是故意将他们弄得类型化与写意化,而且,为了突出他们生活的特点,郭伟总是让作品中有着一些基本的场景和物象,如一地烟头、卡通玩具、假发、墨镜、莫尔干发式等等。更加重要的是,由于有意突出了他们在衣着、肢体语言、生活方式上与传统价值观的大相径庭,所以也很好强调了西方文化、商业文化、电子文化与大众文化对他们的深刻影响。我们也许应该同意这样的说法,即“轻”、空虚、无聊、无奈、无目的是当下一些青年人共有的精神状态,而快乐、时尚、消费则是他们的最高哲学。至于国家的前途与人类的理想,是根本不为他们所关注的。7
郭伟的画表现了新一代都市人的渴望和空虚所交织出的内心的荒芜,这些画中人都带有作者自叙的影子(有许多画作也可视为他本人的自画像)。郭伟关心的是“人”的问题,且坚持以普通人的视点来展现他对“人与人之间非人性化和异化状态的一种谴责”。艺术家自己也说:他是将人作为一种文化问题。他表现的是现代社会的孤独者(表面和内心的)在日常生活中的欢乐,他们对美好或不那么美好的事物的热切追求,他们组成一个个浮游在主流社会边缘的巨型蜉蝣的小群落。日常生活是他们的存在,躲避和对信仰的抗拒,日常生活的表演也成为他们抵抗焦虑,抵抗外部世界的有效方式。
郭伟的画正是在纪录“无意义生活”的框架下,来表现真正的意义和从中寻找生活的非私人性质。他的画中人物既是自己又是别人,通过自己与周遭环境,生存状况的关联,通过对日常琐事的变形和夸张,来建立与时代同步的私人记忆。
的确,家人、朋友、女儿、艺术家本人,日常生活在一个小小的室内大大地寓言化了。例如“室内”系列的作品中,两根垂直的直线概括了场景,概括了人物关系,也概括了社会形态。生存经验和现实威胁也在这两根线上展开。也许因为长期在一个拥挤的室内作画,也许因为“室”是一个对自己视点或观念的有效限制,郭伟通过这个被限制的小世界来表达那个更大的世界。画中的人物关系张驰有致,夸张、变形,又有戏谑成份,像是从家庭这个广角镜头里望出去,一直广到这个时代的横切面。
室内,有时像一个舞台,上演一幕一幕超现实的游戏场景:他们(成人和孩子)回家、淋浴、撒欢、嬉戏、尖叫——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和一些象征意味的戏仿,围绕着家庭这个核心向外伸展开去,在这样一些故作轻松的家庭生活仪式中,他调侃和解释了现实社会中人物和外部世界的关系,一种既在现实中,又试图超越现实的想象关系。在他的作品中经常出现的“蚊子”,不仅是画面表现趣味的托词,也是画家内心的一种挥之不去的问题,他似乎想表明:生活中的问题不仅是日常化的,也是永远躲避不了的。
就像画家自己说的那样:“不同时段,不同视点,不同关系的人物的并置是荒诞的,⋯⋯荒诞不是别的什么东西,它是今天生活的本身。”所有这些游戏都提供给我们一个现实的真实情况,但这些真实又异常地陌生,就像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我们身在其中却又不知身在何处。
郭伟的生活经历没有太多的特殊性,他仅仅是具有一个很富于精神性的环境,有大量的艺术家在这个城市,如果能够经常见面,就足以使自己获得某种关于艺术的收获。自由的生活在市场经济的发展中逐渐扩大了空间。1997年,张晓刚与唐蕾在一条叫做沙子堰的小街上开设了一间“小酒馆”,这里成为成都地区年轻艺术家——包括音乐家和作家——喜欢聚集的地方。许多外地的艺术家到了成都,这里都是他们喝酒与聊天的地方,1998年底,赵能智与何森由重庆迁往成都,开始他们新的艺术生活。郭伟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感受生活与敏感艺术的变化的。
从1999年底开始,在成都这个城市的艺术家——张晓刚于1999年底去了北京——开始陆续到北京设立工作室。在新的世纪里,市场化的进程异常迅速,在像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城市里,新的工作室与空间成为艺术家工作的全新的环境。北京(798)、上海(苏州河)、昆明(创库)、重庆(坦克库),这是一种工作环境,更是一种生活方式。2003年秋天,郭伟和几个艺术家寻找到的蓝色屋顶的库房,构成了成都艺术家们今天的工作场所,先是三位艺术家,两个月后,共有七位艺术家将画室移到了这里,渐渐,是几十位不同年龄的艺术家将他们的工作场地放在了“蓝顶”。一开始,周春芽、郭伟、杨冕、赵能智、罗发辉、舒昊、付曦、郑德龙、唐可、屠洪涛、吉磊、张发志、吴建军、魏健翔、李南森、刘芯涛、邓先志、徐牧原、陈秋林、余极、何多苓都是蓝顶艺术中心的成员,可是,艺术市场发展的速度导致更多的艺术家陆续去了北京,最后,郭伟也在2008年在北京建立了自己的工作室。这也意味着,艺术家将他的工作空间扩大到了自由驰骋的程度,这与他早年在盐市口的居住空间里画画的情形形成了难以想象的对比。
2008年5月17日星期六
【编辑:谈玉梅】
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