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年丁衍庸
日月逾迈,丁衍庸辞世已经30余年。在丁公去世前远赴法国的展览,展出作品全属中国书画,而其在日本享誉盛名者亦是连续四年获邀参加日本南画院的展览。是则丁公以其中国书画篆刻立足国际艺坛,似已成为定评。可是,经过数十年的时光淘洗,近几年来却出现引人注目的变化,丁公的油画在鉴藏家中建立起特殊的地位。2003年台北历史博物馆举办《意象之美——丁衍庸的绘画艺术》展览,展品中油画、水墨画和篆刻鼎足而三,并在展览图录中各有专文论析,由是探讨油画在丁衍庸艺术所占的位置乃成为饶有意义的课题。
东洋取西经
20世纪初期的中国,正当西潮激荡的洪流,传统文化面临存亡绝续的考验,向东西洋取经救国,也就成为当时年轻一辈的出路。乘着这股留学报国的浪潮,丁衍庸抱着“好好的画西画,回国从事美术教育,服务于国家民族”的心愿,于1920年秋天东渡扶桑,先后在川端画学校及东京美术学校西洋画科学习。至于丁氏学习西画为何不直接往欧洲而日本,主要是受了曾经留学日本的族叔丁颖(1888-1964)的影响,同时亦由于日本明治维新后致力输入西学,国家迅速富强,因此吸引许多有志之士试图从日本学习西方,振兴中华。

丁衍庸族叔丁颖与战前的东京美术学校
归纳丁氏在东京五年潜心学习西画的成果,首要是正规的艺术训练,从素描至水彩,然后油画,题材亦是先以石膏像模型奠定基础,再对人体模特儿、静物及风景写生,最后才进行毕业创作,是循序渐进的系统性研习。其次,他所追随的教授,均曾往欧洲留学或考察,亲炙西欧的新旧画派,亦能发展各自的艺术个性。第三,东京艺坛的大环境可能对丁氏产生更大的影响。丁氏留日时期正值大正后期(1912-1925),留欧之日本画家陆续归国,西洋画之发展随而进人多元化的鼎盛期,除较早前传入之学院派及印象派外,崇尚个性及主观表现之后期印象派、野兽派、立体派及表现主义等大为流行。此时日本的美术馆、博物馆林立,展览活动频繁,美术出版事业蓬勃,令人目不暇接。丁氏纪录了他参观1922年举办的第一届法国现代绘画展览的深刻感受,自认大受印象派、后期印象派及野兽派诸大师的影响。丁氏在这活泼的艺术环境浸淫五年,学艺突飞猛进,而且促使他决意以西方现代画派作为探索的方向。

东京美术学校西洋画科教室,着西装者为指导教授藤岛武二

丁衍庸毕业作品《化妆》、《自画像》
丁氏在日本五年间的作品,经已大部散佚。有幸硕果仅存的一幅原作,是由于东京美术学校的毕业规则而保存到今天。该校西洋画科所有毕业生均须缴交两幅毕业创作,以评核成绩,其中一幅是自画像,规定留在母校,另一自由选题,原作则发还给毕业生,只有黑白照片存档。丁氏自不例外,他的自画像连同其他中国留学生的自画像共44幅至今仍珍藏于东京艺术大学美术馆,成为研究中国现代美术史宝贵的实物资料。丁氏的《自画像》画上署名“Ting”,年款为1925年,在他回国前经已完成。此画捕捉了丁氏24岁时风华正茂的形象,带着初生之犊的傲气,显示他对人物形神兼备的造诣,不愧是和田英作(1874-1959)教授的高足。然而画中那阔大遒劲的笔触,强化的线条韵律和平面涂抹的油彩,却偏离了老师的画风,应是丁氏研习画坛新兴现代流派的成果,其中以推动野兽派在日本发展的中川纪元(1892-1972)和万铁五郎(1585-1927)的影响较大。另一幅毕业创作《化妆》仅保存黑白小照,虽然无从得睹丁氏引以自豪的色彩,但其裸女梳妆的主题、华丽闲逸的意境、柔美的造型、平面化的室内空间、满布画面的装饰花纹,以至活泼的线条和主观的表现,均印证他已选择了野兽派的马蒂斯(1869-1954)画风作为自我探索的起点。
中土播新风
1925年秋天,丁衍庸挟着东京美术学校西洋画科毕业的荣衔和新颖的现代画风,返回中国。他决定以上海作为他的根据地,投身艺术教育,并推动中国艺术的现代化。此时上海已发展成为西画传播的中心,汇聚了从欧洲和日本归国的留学生,掀起引进西洋艺术及教学模式改革中国艺术的新艺术运动。以西方学院派为主的写实风格,标榜科学精神和理性主义,早在民国初年经已传入,其后在留法的徐悲鸿(1895-1953)倡导下成为改革中国传统的桥头堡。至于印象派之后兴起的现代美术思潮及流派,包括后期印象派、野兽派、表现主义、立体派,亦先后引进,其中刘海粟(1896-1994)及林风眠(l900-1991)是代表人物,然而留日的西画家则较为人多势众,更是现代主义在中国发展的中流砒柱。他们冀盼借重西方现代艺术的革命,以鲜明的色彩、豪迈自由的表现和强烈的个人主义精神,为沉滞的中国传统艺术注入活力,并使中国艺术的发展与世界同步。两个阵营的艺术思想和审美价值各有取向,对于如何革新传统、创造时代的新艺术亦不相同,因此论争不绝,而且随着中国内忧外患的历史处境的恶化,有关的讨论已超越艺术本质的对峙,现代主义画家在抗日战争时期尤其受到脱离现实的批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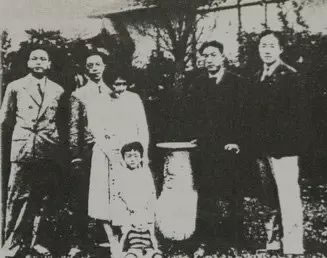
1926年的丁衍庸(左一)、徐悲鸿(右二)、陈抱一(右一)

1929年,以如何看待西方印象派和野兽派绘画为核心的“二徐之争”
不论是西方传统的写实画风,还是多姿多采的现代新兴画派,都属域外文化、异质画种,要在中国的土壤播种生根,必须与本土固有的文化艺术互相适应与交融。丁衍庸所推崇的野兽派,风靡日本现代画坛,追随者甚众,传入中国后,同样受到欢迎,连同其近亲表现主义,成为影响最广泛的现代流派。当时不少中国艺术家认为西方现代艺术发展曾受中国艺术的影响,引以为荣,丁衍庸也持有相同的看法。事实上野兽派大师马蒂斯确曾借鉴东方艺术,也收藏中国艺术品,部分藏品还在今年中假香港艺术馆展出。此外,野兽派的风格和中国画的写意传统亦有不谋而合之处。两者均重视主观精神和个性表现,抒情意境的经营;造型单纯简化、夸张变形,不求形似,同时着重线条的律动。基于这些共通点,中国现代画家较易掌握野兽派和表现主义的特色,再引入其强烈而自由的色彩运用,造就野兽派在中国的蓬勃发展,也为其民族化的努力制造有利的条件。

徐渭、八大山人作品
丁氏对西画民族化的觉醒,是快速而直接的。1925年他在上海开展其教学生涯不久,即改变其艺术主张,“极力的在线条上作功夫”。丁氏对西画民族化的觉醒,是快速而直接的。四年后,他发现了徐渭(1521-1593)、八大山人(1626-1705)、石涛(1642-1707)、金农(1687-1763)等独具风格的文人雅士,深深感受到中国书画及金石的博大精深,开始研究和收藏,甚至自学中国绘画,从此奠定其终身鉴赏及收藏中国古代文物的喜好以至书画和篆刻的创作。虽然丁氏回归传统受到一些现代画家的非议,严厉批评他的复古倾向,他却择善固执,通过“中国艺术的体系和中国固有文化精神方面去找寻新的知识和新的技法”。他深信解救当前中国艺术的契机,在于“复归于原始”,因为在原始艺术“单纯”而“真率”的表现中,“含有深远的意味”。

丁衍庸《抱琴的女人体》
丁氏也是以自己的立场汲取他所理解的马蒂斯的艺术特色,认为他的艺术“极力主张还原,在形式方面非常‘单纯’而又‘稚拙’,内容包含得非常‘广大’而‘复杂’,有原始时代的优点,他能在寥寥数笔中能够启示我们人类无穷的意味”。丁氏尤其欣赏马蒂斯晚年的风格,认为他那以简见繁、以拙驭巧、以纯葆真的艺术境界,正是自己向往的,而这些特色都可以在中国艺术中垂手而得,因此立志研究中国远古时代的艺术及文人画传统,由此开展其50年融会贯通中西艺术的创作道路。
以上述丁氏的艺术理想试图印证他的创作成果,却是令人痛心的,皆因这20多年间的作品几已全部散佚。目前能见到的,油画方面仅有十数幅在报刊上发表的黑白插图,印刷质素欠佳,更无从了解令他享有盛名的色彩运用。粗略地考察,作品题材以人物较多,亦有静物及风景;风格方面,自是近似马蒂斯,但是亦曾取法于其它野兽派和巴黎画派大家如马尔凯(1875-1947)、凡·东根(1877-1968)、杜菲(1877-1953)和毕加索(1881一1973)等。无从细睹之余,或许可以借用当时曾亲见真迹的同路人倪贻德(1901-1970)的评语,略窥丁氏在这时期的画风。倪贻德形容丁氏的油画“笔势飞舞,色彩夺目”,“爱用绚烂鲜艳的色调,但绚烂而不刺激,鲜艳而不庸俗,却是富于明快的感激,这是因为他同时善用白和黑的这两种色彩的缘故。他最喜欢描室内的女人像,而那些女人大都属于有闲的享乐的太太小姐们,他们都有快乐的表情,潇洒的态度,华丽的饰,而背景又十分的华丽精灵,充分的表现出享乐趣味来”。
丁氏参加“第一届全国美术展览会”的作品《读书之女》可视为此类风格的代表,而画中少女优雅的姿态和悠闲恬静的意境,引人入胜,更足以印证马蒂斯对他的影响。比对其毕业创作《化妆》,《读书之女》的造型和笔调渐趋单纯简练,可见他向着自己的理想迈进。30年代丁氏在钻研传统写意画之时,亦意图“把中国画的线条和墨用到西法画上”,全画的笔致流畅豪放兼而有之,弥漫着一股浪漫自由的情怀。
南迁研古道
1949年的政权易帜,丁氏面临生命中的重大转折点,甚至可以说是骤变。是年他从广州南下香港,至1978年辞世,旅居近30年。香港是他一生中居留最久的城市,已成为他的第二家乡。移居香港,他改名“丁鸿”,以示鸿雁南来之意,至其晚年,此名沿用不辍。一如当时涌至香港的离乡别井的大批难民,他的经济陷人困境,生活艰苦,又举目无亲,被形容为将“孤独、寂寞形诸笔墨”。对于自己的际遇,本来叱咤风云的艺专校长和新艺术运动的先锋,在香港这一陌生的时空,备受冷落,更是感慨万千。面对逆境,丁氏不屈不挠,以坚强的意志在香港延续新艺术运动未完成的使命,并加倍努力创作,钻研学术,终于成就其独持的艺术风格,为20世纪中国艺术写下辉煌的一章。

丁衍庸《鱼与蛙》
丁衍庸初抵香港,只能在中学执教美术科,同时开始接纳私人学生,教授中西绘画。1957年联同陈士文(1907-1984)创办新亚书院艺术专修科(即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前身),任教至1978年荣休。其间先后在数间专上学院兼职,教务繁重。在困厄的处境中,古代艺术文物就是丁氏的精神寄托。他节衣缩食,将收入几全部放在购藏书画、玺印、青铜器、石雕、陶瓷、陶俑各类文物,并深入探究,写成专文,强调中国艺术的创造和革命精神,希望引起艺术界对传统的重视和借鉴。他视之为创作的源泉和教学的辅助,而在他个人的艺术发展上足以印证其丰盛的收获。
丁氏以深入探究八大山人及写意画传统作为自我创新的起点,成就了他的水墨画风。油画创作亦呈现相同的趋势,他遨游于上下数千年的中国艺术的古道,自由地汲取丰富的灵感,将中国艺术的精粹和神韵,注入西方艺术的媒介中。他不是以取长补短的方式改革西画,也不是要排除野兽派和马蒂斯的影响,反而是消化这些影响,用中国人的精神去画油画。他以实践跨越中西绘画的矛盾和界限,又渗人他独特的现代中国人的性格和际遇,因此,不论油画或水墨,各有特色,而同出心源,都是中国人的画。

丁衍庸《甲骨文字/兰》
丁衍庸艺术发展的一大特征,就是他在20多岁时就定下清晰而明确的艺术理想和探究的对象,即是前已论及的以马蒂斯为首的野兽派、以八大山人为代表的大写意传统与象征原始审美意念的古代玺印。在丁氏活跃于中国大陆的前半生,或可称之为前期,这三条线索基本上独立发展,交汇融和的情况比较少,惜未有足够的传世油画作品去了解他已取得的成绩。移居香港的后半生或后期,虽然身处中西交汇的开放型社会,但他并不热衷于追逐西方艺术的新浪潮,反而坚定不移地深化野兽派的影响。他曾经剖白他的立场:“不断的吸收新文化以及外来的文化,哪能创造自己的新文化?好似春蚕食叶一样,不把叶子消化了,如何吐得出丝来!”至于丁氏对中国艺术的钻研,更因感到中国文化在共产政权之下有亡灭的危机,在“花果飘零”之时,产生“灵根自植”的迫切性。基于这种心态,他对钱穆、唐君毅等知识分子创办新亚书院的宏愿很有共鸣,毅然参与他们保存及发扬中国文化的事业,成为艺术系的精神象征。丁氏艺术发展的第三条线——古代玺印,从1960年开始转化为创作的源泉,引领他从鉴藏及审美角度进入篆刻的世界,是丁氏香港时期极之令人振奋的新事。而且古代玺印中不少文字和图像均先后被丁氏吸纳到他的油画、水墨画和篆刻作品中,促成前述的三条线索相互交融会合,形成丁氏鲜明的个人艺术风格。
延续与开拓
初抵香港,可能因生活的骤变而暂时欠缺创作油画的客观条件,仅借水墨怡情遣兴。然而随着他在1951年于德明中学觅得教席,生活渐趋稳定,不久即重拾油画笔,自此创作不绝,70岁后虽然所作大减,但至1977年仍有作品传世,即《红色仕女》及《黄易像》。不过,由于丁氏兼顾多个教职,又热衷于中国书画篆刻,分配给油画的时间不多,因此历年油画作品数量比起数以万计的水墨画可说是微不足道,目前所见仅百余幅,而且纪年作品分布并不平均。相信还有一些作品仍由友人及学生保存,尚待搜求,数目当有增加的可能性。此外,丁氏的油画作品,不少画在纤维板上,取其简便经济,当中甚至底面均有绘画。

匡时15秋拍 丁衍庸《钟馗纹瓶子》
丁氏油画作品还有另一情况值得注意的,便是画布、画板的重复使用,即是说画下有画。香港艺术馆曾用红外线拍摄部分展品,确认了这个情况。正常情况下,要画家亲手埋没自己的心血结晶,会有不舍的感觉,因此,纯粹以经济角度或狭迫的家居环境,也是难以充分解释的。如果我们尝试从他对处理水墨画的态度,或许得到一些启示。丁氏的水墨画,数以万计,大部分随画随散,赠与学生友好。油画创作的性质虽与水墨不同,数量也少,但他也持有相近的态度。换言之,丁氏重视创作的过程和探索的经验,也带有即兴的意趣,对于创作的成果,其聚散存没,倒是次要的,尤其在经历时空的剧变,半生收藏和作品参与散佚之后,丁氏流露着游戏人间的潇洒。
至于丁氏于50年代最突出的新发展,就是在油画中引进古文字和符号图像。这当然可追溯至30年代丁氏对中国原始艺术的浓厚兴趣,他对古代玺印尤其重视,认为可以当作原始绘画:“那种印划如画的线条,始终不懈的力量,蕴藏无尽的内容,生气蓬勃的神韵,已非其他古器所能及。而玺印形式和造型的丰富变化,足资现代艺术借鉴。丁氏以文字或古物入画,并非依样葫芦,而是取其神韵,变化其造型,创造新的结构,文字、符号、图像三结合,缔造古拙神秘的个人艺术世界,也打破现实与想象的界限,因此已远远超出马蒂斯或野兽派的启示,让油画进入中国文化的世界。
跨越与融合
60年代至70年代初是丁衍庸的油画发展的高峰期,此时期的作品雄辩地说明他已架起了跨越中西艺术的桥梁,令两者共通的艺术精神得以体现,更以强烈的个性和独特的人生练历,融合民族和文化的深层差异,为中国油画缔造新风。
1960年丁氏开始刻印,篆刻文字及图像在他的油画创作中的重要性提升,不但是装饰的纹样,更是画面的主题、结构、造型、线条和内容的依据。《鸿虎》是丁氏的生肖和他南下后采用的字号的组合,造型受古玺印文字的启发而加以变化,以长锋羊毫笔写成的粗犷线条雄劲有力。值得注意的是此画的丰富色彩感,是数十年浸淫在野兽派中的沉淀。

丁衍庸《仕女与马》
人物肖像及人体画,是丁氏数十年来锲而不舍的题材,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响至为显着,但仍然倾注了丁氏强烈的个人风格及中国艺术的精神。他经常以学生作为模特儿,用意不是要记录他们的外在样貌,而是借简化的造型和流畅的笔调,捕捉对象的神韵,《仕女与牛君》是很好的例证。丁氏的成功,是建基在多年的素描和素写的锻炼,因此寥寥数笔,对象的特征和神采,即跃现纸上。
综观丁衍庸的平生艺事,从接受西方艺术基本功的洗礼、掀动野兽派的潮流,到终身投人西画的教学,尤其是在同代留学的西洋画家或亡殁、或销声、或转向之时,他仍然创作不辍,可见西洋绘画与其所结的不解之缘。丁氏在发掘此一西方艺术语言的中国化和个性化的进程中,直溯原始艺术的本原,汲取中国传统中青藤、八大一脉的寓忧愤不恭于笔端的精神。他的油画始基于西方现代主义,而又非徒貌似而为神合地发展成为他的个人风格,正是跨越东西、游戏古今的体现。
评价丁氏的油画,值得注意的除了他在中国现代油画史上的地位,更在于他个人艺术世界中一源三脉不可或缺的一环,就是水墨酣畅、笑傲笔端的国画,竞雄奇于方寸的篆刻之外,还有一种以醇厚的色彩传达出他对生命深沉的思考的艺术语言。
文章整理自高美庆教授文章,载于台北历史博物馆出版的《意象之美:丁衍庸的绘画艺术》
编辑:江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