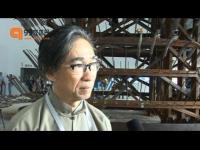高岭
——高岭访谈录
高岭:美术学博士、艺术批评家、独立策展人。1964年出生于浙江省衢州,山东省郓城人。1982-1989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先后完成了本科和研究生的七年学习,其硕士研究生的专业为美学专业,研究方向为中国绘画美学,89年毕业获硕士学位。2002年考入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攻读美术理论专业博士研究生,2005年获得美术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为《审美文化语境中的商品拜物教批判》,获优秀论文奖。
在研究中国绘画艺术理论和美学的同时,自1987年开始,将目光转向中国当代艺术的研究,翻译了许多西方艺术理论和批评的文献,并且先后在国内外许多艺术专业报刊上发表当代艺术理论、艺术批评和当代艺术家的评论文章近400篇,近200万字。其中1995年发表的《中国当代行为艺术考察报告》,成为研究中国行为艺术的最重要历史文献,被广泛收录入海内外各种出版物。
除了长于逻辑思维、视角敏锐外,先后参与了国内许多重大当代艺术展览的策划、组织和学术研讨,如1989年中国美术馆的“现代艺术大展”(学术秘书),1996年北京国际艺苑的“现实:今天与明天”首届当代艺术展览暨作品拍卖会(艺术主持之一),2001年北京泰康人寿大厦的“感受金钱”当代艺术展(艺术主持),2006年北京中华世纪坛艺术馆的“首届中国当代艺术年鉴展”(秘书长、策展人之一),2006年北京今日美术馆的“中式意识——审美营造的当代复兴”(策展人),2007年香港大会堂“何去何从——中国当代艺术展”(策展人),北京今日美术馆“黑白灰——一种主动的文化选择”(策展人),2008年“当代·红光亮”(策展人),2010年“第25届亚洲国际美术展”(中国艺术主持),2012年“第四届广州三年展第二回项目展‘第三自然——中国再造’”(策展人)等。
1995年策划编辑了《当代中国艺术批评》(湖南美术出版社《当代艺术》丛书第11辑),成为1990年代当代艺术批评和理论的重要文献。他的重要艺术批评文章被收录到《镔铁——1979—2005最有价值先锋艺术评论》(敦煌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等众多艺术批评和理论文集及书籍中。著作有《商品与拜物——审美文化语境中商品拜物教批判》(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鉴证——高岭艺术批评文集》(河北美术出版社2010年版)。中国当代活跃的艺术批评家和策展人,发起并担任独立学术读物《批评家》的编委、编辑部主任(共出版八辑,已停刊)。江西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客座教授。
刘淳:从年龄上说,你是60后生人,但在当代艺术的批评上,你却是一位老批评家。早在上世纪80年代,你就介入了中国现代艺术的研究与批评。2005年年底,我在云南艺术家毛旭辉的一种文献展上,看到了1989年“中国现代艺术展”的值班表上,还有你的名字,可见你是一位“老革命”啦。
高岭:是啊,你对我艺术经历的概括非常准确。我从1987年下半年在即将停刊的《美术思潮》倒数第二期上发表了翻译的艺术理论文章开始,迄今已经过去了25年了,时光荏苒,但往事历历在目。60年代出生的批评家和策展人,应该没有人比我更早从事新潮美术(当时的称谓)理论批评了。至于你提到的现代艺术大展上的值班表,也确有其事。原定1989年2月5日到19日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禁止掉头——中国现代艺术展”,因故两次中断。那一年的冬天北京天寒地冻,但外地来的艺术家都不愿离去,大家组织起来轮流值班,看护场地,自救自助。我当时是北京大学哲学系的三年级美学研究生,正在写毕业论文,但这个展览的重要性和运作的艰难,的确花费了大家大量的心血。我被筹委会安排作为7号那天的值班总负责人,负责协调美术馆一层黄永石水(pin)和林春、二层任戬和刘彦、三层王公懿和孙保国等艺术家共同工作。在我之前的总负责人5号当日是栗宪庭,8号是范迪安,6号停展。
刘淳:你们家里有搞艺术的吗?
高岭:我父母亲都是军人,从事医务工作,没有人与艺术有什么联系。不过,我父亲,手头很巧。记得小时侯,家里的许多东西,他都能修补,甚至于还会补烧水做饭的铝锅,要用箍子。我父亲母亲都是在部队系统学的文化,但他们都写得一手好字,父亲现在还热忠于写字。我喜欢艺术,可能与他们的这些能力有关吧。
刘淳:我认识你的时间是1993年,那是我们在北京做一个展览,晚上接受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专访,当时你作为批评家也在其中。同年,我还在《江苏画刊》上读到你的批评文章,好像是反对批评家有偿写作的,你还记得吗?
高岭:是关于包括你在内的当时你们一群山西的文艺青年,特别是以宋永平为主的画家,
到柳林县一个叫做西局岔的山沟里搞的“乡村计划·1993”的电台直播,都快20年了。我记得当时的主要倾向是面对以北京这样的少数大城市开始的商业化大潮对文化的首轮冲击,敏锐的艺术家如何反应这个层面。因为,几乎在同时,比你们山西还偏远的甘肃兰州,像成力、马云飞、杨志超等人还搞了一揽子的行为艺术“葬”,认为现代艺术尚可能被市场经济的推广所吞噬,而不少新潮美术时期的艺术家正被市场操作的热情所陶醉,一种机体腐朽的现象正在形成,中国现代艺术需要一场清理门户的革命。
其实,又何止是你们这些当时地处西北偏僻地区的艺术家对这些问题敏感!当时很多八十年代走过来的知识分子都有强烈的警觉和质疑意识。我当然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对我的同行中间出现的市场化行为有所警觉了。我曾经先后在《文化月刊》、《文艺报》和《江苏画刊》上发表了三篇前后相关联的文章,即《美术批评问谁要钱?》、《一九九三:中国美术批评家开始走向市场?》和《市场情景中美术批评的一点设想》,尤其是1993年第10期《江苏画刊》上的文章,最能体现出我当时的疑虑。为此,我当时提出了我的一种设想,当然,这个设想到今天都难以实现。我认为市场情景中美术批评家获取报酬,应该如同艺术家有经纪人或画商作为其与艺术市场发生经济关系的中介一样,也应拥有自己的经纪人或代理机构。具体看来:一。设立批评经纪人中介,使批评家与艺术家之间避免直接经济关系,有助于保持双方各自的选择自由和相对独立的学术品格与心理状态;二。有助于批评家集中不必要分散之精力于学术研究,保持学术水准不断提高;三。批评经纪人或代理机构中介,比较理想的是美术专业的报刊编辑部等新闻出版单位,但不排除独立经营的经纪公司的存在;四。新闻出版单位业务范围扩大的同时,一方面具有了选择稳固的专栏批评班子的经济权力,另一方面又担当起了解、确定批评家应得报酬标准并在批评家与艺术家双方均认可的情况下代为收支报酬的责任;五。批评中介人或机构的出现,为美术批评步入专栏化、专题化提供了可行的基础。
最近几年有些艺术网站刊登出我的这些旧文,但没有准确表明具体时间和原来刊登的刊物名称等信息,让人认为是我的近作,令人啼笑皆非。
刘淳:你的本科和硕士学业完成于北京大学,后来又在中央美院取得了博士学位,请你谈谈这一路是怎样走过来的?
高岭:我从小就喜欢画画,无奈父母亲当时所在部队在安徽农村,没有很好的老师指导, 所以1982年我高中毕业时只能报考综合性大学的文科。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后,在二年级开始有美学原理课程,这唤起了我对其中美术作品鉴赏和品评的浓厚兴趣。当时全国正兴起美学热,我决心报考美学专业的研究生,希望在以造型艺术为基础的美学研究方面有所深造,将来到艺术院校教书,把自己少年时的爱好与自己今后的志向结合起来。最终,1986年我在78名考生中考取了当时仅3名录取名额的美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后来实际情况是,系里又括招了几名代培生)。我的研究方向是中国绘画美学,导师是那个时代在绘画美学和画论领域卓有成就的葛路老师。从那时开始,我可以说整天就徜徉在学校和系里的图书馆和资料室里,当时的《文艺研究》、《美术》、《美术研究》、《世界美术》、《新美术》、《美术译丛》、《江苏画刊》和英文的《英国美学》我期期都翻阅,后来还看到了《美术思潮》和《中国美术报》,使我对课程研究之外的整个中国美术界的热点话题以及国外的艺术和美学动态有了越来越多的了解和关注。于是,自己也鼓起勇气投稿,发表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幸运的是,我的文章当时每投必中,都及时发表在刊物上。
今天回想起来,像我这样在综合性大学的研究生,能够很快融入专业的美术理论和批评的领域而且是新潮美术这样前沿性的圈子,当时是不多见的。即便是当时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论系毕业的学生里,几乎也没有人对此类前卫问题感兴趣。许多今天活跃的策展人和经纪人,当时都在热忠于抽象和一般性的理论话题和考古类的问题。而我当时哲学系里的同学,哪怕是年龄偏大的77或78级本科后来和我做同学的研究生,都没有这方面的敏感度,许多人当时根本不理解我对美术甚至是新潮美术如此感兴趣。89年毕业到北京服装学院教书的两年里,同样也没有几个同事对我所从事的艺术活动和研究表示理解。即便如此,我还是成了我直接教的学生和间接影响的学生的孩子王,我甚至利用自己有限的权力邀请了高名潞这样在新潮美术运动中的领军人物到学校做讲座。
应该说,我始终对创造性和前沿性的话题保持着浓厚的兴趣和判断意识,从不轻易动摇自己的判断和决心,否则我在艺术批评领域可能走不到今天,早就去当官搞行政了。要知道,当年学哲学的人,大多都是要到国家机关去当干部的。而我对这些似乎从来就不感兴趣。有关我艺术批评的完整经历,我在我的文集《鉴证——高岭艺术批评文集》(河北美术出版社2010年版)中的自序中已做了叙述,就不再赘述了。
刘淳:有一些非常优秀的艺术家,从事艺术创作最直接的理由就是生命中最能触动他们神经的东西,我想听听你的看法?
高岭:艺术家我了解的非常多,有些今天非常出名的艺术家,我们彼此在20多年前就认识,也有很多鲜为人知的故事。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艺术家一般都较常人偏执或者叫一根筋,对触动他们内心深处的东西格外敏感。其实,从事创新和探索性的艺术研究的人,也同样如此。
刘淳:我将与你的访谈锁定在“当代艺术”这个范畴里,尽可能在这个范围中讨论问题。
高岭:好,这样我们的对话就有了共同的判断基础。
刘淳:你是怎样理解“80年代”的?对80年代还保留着怎样的情绪和记忆?
高岭:前几年,旅美学者查建英出了本书《八十年代》,引起了热议。书中收集的是出生于上世纪四十年代后期到五十年代的人在八十年代的文化思想活动轨迹。我是六十年代生人,但有兴参与了八十年代后期美术创新和变革的活动。今天回想起来,那个时代给我留下记忆最深的是一种人文主义的理想。它可以说是一种情绪,普遍蕴涵在当时锐意变革的青年人中间。人们在一起交往,不是看你的经济地位和财富,而是看你的学识和思想,是思想和才华彼此吸引,哪怕千山万水,都隔挡不住知音之间的书信往来。那些有限的工资收入,大多用在了火车和邮费上,因为真正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太需要在一个百废待兴的时代寻求真理和创造历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