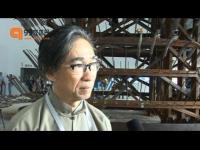刘淳:80年代有太多的话题值得我们继续讨论,有太多的事件值得我们回忆。从时间上说,80年代只是一个人为的计量。90年代之后,艺术上出现了方力钧等人,改变了80年代的基本形态。我想说的是,我们对80年代到底怀念什么?
高岭:怀念八十年代,我想最重要的是怀念对真理的执着追求,怀念在这种追求态度下人们之间开诚布公的讨论、争论和批评。而这些真挚的东西,在现在各种功利性机构、圈子和名头的包裹下,往往被肢解、被包装成了各种欺世盗名的一己私利。我的博士论文在国内首创研究商品经济下文化艺术领域的商品拜物教,今天人与人的关系,人对事物的判断,不断被物与物的关系,被符号与符号的关系,被时尚与名目的关系所遮蔽和掩盖。人们已经很难集中讨论一个问题了,总是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制造话题和自我造局。
刘淳:有一种说法:80年代的中国现代艺术,是对西方100年现代艺术模仿的结果,采用“拿来主义”的方式进行一次全面的尝试。关键是,我们拿来的恰恰是人家已经扔掉的东西,这是为什么?
高岭:在一个信息尚未开放多少的时代,我们最容易受到影响的就是西方的现代艺术,今天看来,这种拿来主义的方式是必然的,因此也就是必要的,没有它,我们拿什么来抵制文革美术?拿什么来深化美术自身的认识?在当时的时代,西方人家扔掉的对我们未必就是不必要的,只是到了九十年代以后,社会更加开放和国际交往更加方便,我们才开始认识到自己在这方面的滞后,同时,我们也开始有了更加全面和整体的对于艺术该怎么搞的比较清醒的认识,开始注重本土化和从传统中转换新的养分。
刘淳:我想请教你一个问题,改革开放初期,也就是80年代初突然冒出来一些人,他们深受西方现代主义影响,比如上海的“12人画展”,北京的“无名画会” 和“星星美展”等。我想知道,他们的营养是从哪儿来的?
高岭:他们的营养应该一部分来自于他们上一代或上两代人在1949年以前特别是三十年代所进行的中国最初的现代艺术的变革实践,因为毕竟在民间还暗藏着少量有限的印刷品。另一部分是来自于他们对文革美术的切肤之痛,是对美术政治意识形态化的本能反拨和对写实性绘画的本能涂抹、变形和挥洒。
刘淳:改革开放,国门大开。我们希望用西方的现代主义解决中国问题,希望用西方的现代主义艺术拯救社会,当然,也希望用艺术救国。其实,早在二三十年代,徐悲鸿等人赴欧留学,他们既希于艺术救国。其实,他们学到的并不是西方的现代主义而是日渐衰落的古典主义。在徐悲鸿等人看来,古典主义重视观察现实,是入世的,而中国文人画传统是出世的,所以要用西方的古典写实主义的入世精神拯救中国精神。相比之下,二三十年的引进西方艺术与八十年的有着怎样的区别?
高岭:三十年代的艺术家就整体而言是希望用艺术来直接参与民族精神的拯救,而八十年代的艺术家其实是首先希望艺术能够获得自身的独立,然后再参与更加宏观的民族精神的树立。因为,二三十年代并没有一个完整和清晰的文化政治组织强求艺术家要确立什么样的风格来为当时的政府服务,而1949年以后的27年则不然,那是一个要求艺术必须以一种现实主义的手法为社会政治制度服务的硬性时代。所以,八十年代的前卫艺术或者叫新潮美术主要是要脱离这种硬性要求,要寻找艺术自身独立的本体价值和意义。这是我们理解两个不同时代对待现代艺术的不同出发点的关键之处。这几年,人们开始怀念民国文化,但如果不明就里,则会否定了八十年代的文化贡献。
刘淳:8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理想状态是保持一种激进的、对社会批判的、非功利的、不参政的,永远有距离地保持着自己的独立意志。你认为我们的艺术家能做到吗?能具体谈一下吗?
高岭:我不是艺术家,不能替中国艺术家承诺什么。但这样的艺术家在国外,特别是发达国家却大有人在,比如李希特,比如大卫·霍克尼,比如比尔·维奥拉。中国艺术家今天其实最大的内部敌人是自己,要做好一名真正的知识分子,其实首先要约束好自己,要战胜自己。
刘淳:栗宪庭曾经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重要的不是艺术》。其实,他想说的是,重要的不在于一件作品本身的好与坏,而是你用什么样的标准来判断它,不同的判断标准会出现不同的结果。对此你如何看?
高岭:重要的是观念,是对艺术理解的观念决定了什么样的艺术为什么样的人喜欢。
刘淳:今天我们回顾80年代,好像大家当时都有一种理想主义的激情,做了很多现在看来不很现实的事情。实际上大环境还是原有的体制,都是铁饭碗,商业还没有到来。你觉得80年代与90年代、还有新世纪的头10年相比,最突出的特点是什么?
高岭:艺术本身就是非现实的产物,但它与现实却有着紧密的联系,如何理解和把握这种联系,不同时代的人会有所不同。艺术与现实在八十年代的联系在今天的人看来可能会有不现实的感觉,但还原到那个时代,那种联系是非常现实和必然必要的。
刘淳:80年代的中国新艺术实践中,有些艺术家强调理性和思想的介入艺术,实际上就是用艺术来消化他们对东西方哲学的理解和认识。20多年过去了,今天你如何看待思想和理性介入艺术这个问题?
高岭:哲学化和思想化,是八十年代新潮美术的一个最突出的特征,关于哲学、哲理与理性艺术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我在1988年第2期的《美术》杂志上曾经发表长文做了分析。从今天的角度看,艺术创造需要理性和思想观念,但最终还是要落实到视觉语言上,否则,就要成了文字性的语言,就要脱离了视觉本身了。
刘淳:90年代以后,全球化、国际化、市场等许多问题与80年代完全不同。80年代的叛逆针对的是保守与封闭、是专制和艺术的政治化。而90年代,我们面临的老问题依然存在,新的问题不断出现。于是有人断言:商业最终会消解一切,也包括叛逆。那些所谓的叛逆者在商业面前最终会成为主流的一部分。我想听听你的看法?
高岭:八十年代艺术家面对的是单一和保守的政治体制,九十年代后面对的就多了个商业经济体制,还有全球化的世界体制,因此,判断优秀艺术家的标准就丰富和复杂了,他既要冲破政治体制,又要抵制商业体制,还要在世界体制中寻求创新。这就要看艺术家的艺术在哪方面冲破了哪个体制,确立了自己的风格和面貌。所以,叛逆,永远是艺术家的座右铭。没有叛逆,就没有真正的创造性的艺术家。
刘淳:作为从80年代一路走来的批评家,在20多年后的今天,你如何评价1989年的《中国现代艺术展》?
高岭: 那个展览今天甚至于今后都无法绕过去谈,足见它的重要。它让当时在全国各地的前卫艺术家有了集中展示的机会,有了寻找归属感的场合,成了他们一生的回忆,也成了刺激和激发后来那么多艺术家投身前卫艺术的发动机,你说它能不重要吗?迄今为止,没有一个当年参加的艺术家会在自己的简历里抹去它,也没有一个当代艺术史写作者会无视它的存在,你说它不重要吗?!
刘淳:在《中国现代艺术展》上,肖鲁面对自己的装置作品《电话亭》连击两枪,枪声震动了北京,也震惊了全国甚至全世界。20多年过去了,今天你怎么看待当年的“枪击事件”?
高岭:能够在展览中动真枪,这恐怕在此前的世界各个展览上都是绝无仅有的。特别是中国是一个强制管制高度严格的国家,这样的事件,自然震动了。不过,枪击电话厅是否比用斧子或者其他方法破坏电话厅更有艺术上的必要,这就需要讨论了。无论如何,这个事件让八九现代艺术大展蜚名海内外,让世界知道了中国的一群年轻艺术家开始登上了现代艺术的舞台了,却是一件大好事。
刘淳:在今天,我觉得一个艺术家应该、也必须永远坚持自己的感觉,永远不被体制所操控。中国当代艺术在经过20多年的探索与实践之后,它的革命性在于,使艺术从繁琐的技艺和所谓的“象牙塔”中解放出来。你对过去20多年中国当代艺术的探索与实践怎么看?
高岭:过去20多年中国当代艺术最重要的成果是让艺术首先成为艺术家自己表达的工具,而在这种表达中又渗透着自己对艺术、对周围世界的理解。也就是说,艺术成为了个人表达的工具,这一点似乎很简单和肤浅,但为了实现这一点,却经过了不少的时间。
刘淳:我记得90年代有一段时间你对行为艺术特别关注,曾经写过《中国当代行为艺术考察报告》的文章,对出现在中国的行为艺术进行了全面的分析,能谈一谈为什么如此关注行为艺术吗?
高岭:那是一群活生生的人,是艺术院校毕业的青年人,他们有着太多对艺术表达的诉求,不满足于有限的画布和石料或金属,有时候,他们甚至于连这些材料都买不起,于是,他们选择了他们自己的肉身,选择了他们自己的肢体语言。我不能不对这些和我年龄相仿的同龄人无动于衷。而且,最重要的是,在中国的当时,不仅人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是被分配和控制的,甚至连人自身的行为也是被控制的,而这些人却能够以自己的行为来与社会即定的行为规范和定势搏弈,是那么的大胆和新奇,不能不使我格外关注,试图探究其背后的心理动机和艺术指向。
刘淳:你曾经说过:批评观的确立,主要的是批评立场和批评原则的确立。但是你还说:批评观的确立,也意味着批评方法的形成。能具体解释一下吗?
高岭: 任何批评和评论,在学理层面和日常语言层面都出自于一定的立场和态度,学者也罢,平民百姓也罢,都如此。但批评的原则,则是与一定的价值认同或者共同体有关,也就是说,原则是一定群体、组织、阶层所共同遵守的契约规范。但是,不同的群体、组织和阶层,会有不同的原则和标准,彼此之间会发生冲突和抵牾,有时难以判断,难辨是非,特别是在我们今天这样一个开放和自主程度越来越高的社会里。而批评之方法,则要看你的批评话语在结构、行文、论述等过程中是否具有逻辑性,是否能够在接近和形成自己的立场和原则的同时,分步骤、分层次、分要点。当然,你借鉴或者依傍各种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理论都可以,但,一定要有方法和步骤,否则,只能是意见和建议,却没有方法论支配下的批评来得条清缕析,成为一个更加稳定的文本来接受和经受时间和学术的考验。如果批评没有方法,没有方法论意识,则很难经得住时间和学理的考验,最终可能会成为一己私见或者小圈子化的义气陋见。
刘淳:中国当代艺术在近些年来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质疑甚至抨击,其中也包括所谓的“天价做局”等,对此你怎么看?
高岭:只要是市场行为,就一定有做局,就像是餐厅开张,要请亲朋好友来撑场子些时日,为的是聚人气,更为的是给餐厅之外的其他人看,然后吸引更多的人进来消费。这本身无可厚非。谁让艺术在最近些年进入了市场了呢?!不过,进入市场的艺术,或者说价格高的艺术,未必就一定是价值高的艺术,这个道理经济学家们早就分析透了一二百年了。只是有一点需要明确的,按老的说法,社会上有七十二行,行行有行规,破了行规,恐怕就别在这行里混了,改行趁早!要是魔术师把魔术给解密了,他还能继续干吗?干哪行爱哪行。揭内幕,曝猛料,不是真正热爱,而是有私心私利的欲望在作怪。你看现在的媒体总在曝这行那行的黑幕,有几个在曝媒体自家这行里的黑幕的?其实,若真正关心艺术的健康发展,就摆事实,讲道理,做一个建议者和推动者,要多看大局,少看小点。
刘淳:在中国当代艺术遭遇批评和质疑的同时,中国当代艺术批评同样遭到批评甚至公开的指责。什么收费文章,有偿写作等等。作为一名批评家,你的意见如何?
高岭:要尊重批评家的智力劳动,要让批评家活得有尊严,在市场经济尚未完善的大环境下,批评家要坚持自己的学术思想和立场,其实远要较艺术家艰难。有偿写作我认为是中国一定阶段的国情,我希望像我在前面的谈话中提到的,像我十几年前主张的那样,将来由第三方支付批评家稿酬和劳务费。希望这个理想并不遥远。
刘淳:目前许多批评家身兼策展人,你觉得艺术批评和策展之间最大的区别和不同是什么?
高岭:艺术批评使用的是文字语言,主要是用人们熟悉的文字语言去逼近视觉语言的内在奥义,让人们在思想和认识上理解视觉语言的意图和指向。展览策划既包括了文字阐释和梳理,也包括在空间上如何将艺术家创造的视觉语言完整地呈现出来的一系列环节设计,还包括宣传推广等等步骤和措施,应该说,后者是一个更加复杂的社会性活动。批评与策展,都是艺术作品产生后甚至在产生过程中挖掘其内在含义的丰富性和生动性的工作,都是艺术生态链条中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没有独立和严谨的批评,就没有艺术作品不同于日常生活行为和事件的学术价值;没有丰富的策展实践活动,就不可能将艺术作品有效地与现实世界和现实社会联系起来,就不能扩宽和生动呈现作品的开放语境和广泛价值。
我们现在有一种错误的认识,认为策展比写批评文章更重要,更能够提升自己的知名度并且获得可观的经济回报。这是市场环境对艺术批评本身的一种误读和强权。没有艺术批评和理论的支撑,策展将沦为普通的会议展览组织工作,沦为普通商品的推广,却忘了艺术品首先不是商品。
刘淳:前一段时间,尤仑斯卖掉了自己的藏品,而西克又将自己的藏品捐给了香港,一时间在国内引起轩然大波,甚至有人直言:中国当代艺术跌倒了谷底。你的看法如何?
高岭:凡藏必倒,这是收藏界的一句行话,也是普遍的行为,只要不是公立的非赢利性质的博物馆和美术馆,吐故纳新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没有一个个人能够长期将自己的资金用来收藏和维持大量的藏品,除非他想做慈善家,想把自己的所有藏品捐献给公共性的机构,我们不能这样要求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人。但一个国家或一个政府或一个公共性的机构,却应该承担起其属性本身承担的对一个时代艺术品的保护和支持,因为这是这个国家一个时代的精神的创造物。我们自己的机构或者政府又做得如何呢?真是乏善可陈。
刘淳:在我看来,说“当代艺术”是一个说不清的概念时,实际上等于拒绝承认当代艺术的合法性。甚至是有意模糊了当代艺术的价值和意义。你认为“当代艺术”面前在中国究竟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高岭:其实,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说,不管是当年的“新潮美术”、“前卫艺术”还是今天的“当代艺术”,都是一个意识上的标杆,它意在创造、创新和进取,意在对各种保守势力、政治势力、商业势力保持一种警惕和反省,只有这样人类的精神生活才会变得自由、多元、多样、丰富、公正和平等与合理。所以,所谓当代艺术概念模糊不清,无非是各种势力和利益集团从各自角度出发的一种话语争论、瓜分与挪用甚至置换。
刘淳:关于“传统”的争论和讨论,在整个20世纪的100年中始终没有停止过,直至今日,中国问题依然不断被人们提及,在今天的现实中如何理解传统?
高岭:“传统”的基本元素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文明发展的基石,但它的呈现方式在历史上从来就不是静止不变的,传统的发展史,其实就是与各个时代的各种新鲜事物不断碰撞、磨合、借鉴、吸收和同化的历史。在中国历史上,就有几次外来文化与本土中原文化相互交融的阶段。近100年来,我们其实也是处在又一次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相互发生关系的阶段,我相信,传统就在当下,当下即为一种新的传统(对于未来的人们来说)。
注: 本访谈录源自刘淳先生2013年即将重新编辑出版的《中国当代艺术批评家访谈录》(暂定名)。
【编辑:李洪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