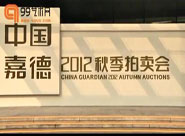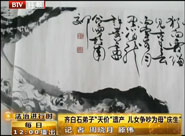赵峥嵘《简单生活》
捷克小说家米兰•昆德拉在其法语小说《缓慢》(“La Lenteur”,英文译作“Slowness)中所写的那个开快车的年轻人,“他抓住的是跟过去与未来都断开的瞬间,脱离了时间的连续性;他置身于在时间之外;换句话说,他处在出神状态,人进入这种状态就忘了自己的年纪,忘了老婆、忘了孩子,忘了忧愁,因此什么都不害怕;因为未来是害怕的根源,谁不顾未来,谁就天不怕地不怕。”[1]实际上,在这样快速度生活中的人,“不仅没有将来,也没有过去:他已和时间断裂。”[2]在《缓慢》里,昆德拉向我们揭示了一个真相:缓慢能带给我们快乐,缓慢是一切快乐的源泉,而快速与我们内心的快乐无关,只能带来暂时的快感或高潮。“那么,有什么比‘缓慢’更缓慢呢?一种对更深的记忆的涉及?”[3] 孙甘露在他的小说《呼吸》的封面上的引语:“小说仿佛是一首渐慢曲……,难道我是在说,我要越来越慢的退回到记忆的深处?那里存在着什么令我难以释怀的使灵魂震颤不已的记忆吗?或者是因为缓慢的天性使我陷于想象,有什么无比珍贵的东西仅存于近乎静止的地方呢?”。
这是一种缓慢的动作。保持这种动作,一种‘投注’般的动作——猫着腰,低着头,一只手努力伸向远方。把生命赌博于这种荒谬的游戏之中,生命不知不觉地被消耗。”[4]这是我在2008年初写下的感叹。 实际上,缓慢和等待一样本身就是一种绝症,消耗着生命。在缓慢的等待中,人们正在老去;这是一种困境,一种防碍一步步推理的困境,因为“短见”和“近视”防碍了整体和逻辑。除了缓慢的等待,没有办法;困境是永远的……
“速度是出神的形式,这是技术革命送给人的礼物。”[5]而绘画叙述着记忆的极限,或者说是记忆的灰烬,一种死去的记忆;记忆的边缘,也就是死亡的边缘。它来自于我们的生命状态、内心中最隐秘的梦想或恐惧。 它的内在的速度是缓慢的,是一种另类的速度,也是一种另类的节奏,是一种死亡的节奏。那是绘画死亡或终结后边缘的位置!我们不得不时时面对失败和隐辱,好像喝着毒品,明明知道它有毒,却无法丢弃。仿佛这“死亡在继续拥抱我们”(陈家坪),燃尽了希望。对于生活,我们的苍白的同时又是黑暗的生活,梦想慢慢褪尽了颜色;而面对作品,就像鲁塞所说的“面对作品,我不再像平时那样感觉和生活了,我被拖进一种变化之中,目睹了创造前的毁灭”。
缓慢:无处不在的遲鈍
本雅明在《德国悲剧的起源》一书中写道,“这就是心灵的迟钝或懒惰,轨道上的土星的微弱之光和缓慢的速度确立了这种状况与忧郁之间的联系”[6],迟缓是这忧郁性格的一种,“而笨拙则是另一个,这样的人注意得到诸多的可能性,却意识不到自己缺乏行动 的能力。还有一个特征是固执,自认为超凡出众。自从这种固执形成以后,‘首要的后果是,真正看到的事物恐怕还不到目力所及的三分之一’”[7]。 而面对自己的作品,看见的只是某种物质的流动,凝结,又流动,然后又不动了,每一步都是那么缓慢,动作是那么的迟钝,这是一次次让自己泄气的经验。在无数次的失败和无奈之后,这缓慢的无效的思考,是不是一种笨拙和固执?
无休止的书写——开始,停止,再开始。忘记,遗忘,失去记忆,自己都已忘了是从何时开始的?不断地开始,不断地重复,由此而迟钝,最终沦于对自己的喋喋不休。巴特为此表达了自己的 警惕与担忧:“............所发现的东西就变成了陈词滥调。”一切慢慢地变得缓慢和凝重,流动受到了阻滞。如长时间在黑暗中,就这样眼睛渐渐习惯了这黑暗,安于这黑暗,迟钝于这黑色。处于迟钝状态的自我,在漫长无尽的等待之后,就变成了一个枯竭的人,钝化了一切,对万物缺乏敏感了。
我本以为,我会习惯这简单生活。但“此刻,寻常的,流逝的/那种似有似无的快乐/在无限流溢中,无处藏身。/在此刻,那些黑暗的行为,/那浓重的阴影/流淌在生命的另一边/此刻,都只在一念之间。/看不见的快活,/无处不在的遲鈍。”[8] 在此刻,我们冥想到的是生命的虚无,和意义的流逝。汉娜.阿伦特在他的《黑暗时代的人们》中写到“知识怎样才能成功地取消死亡?人怎样才能成功地‘认识一切’?”[9] 对于我们来说,痛苦是什么?“我们为什么在这样地制造着苦难,而同时又麻木于这种苦难,安于接受于这种苦难?”。同时,幸福又意味着什么?追求另一种生活?追寻另一种现实?是否我们的“痛苦与矛盾是来自于对地狱之黑暗的窥视与恐惧,来自于恶之火的煎烤和对天国诱惑的逃避”(果戈里)?同时,是否我们的“痛苦与矛盾也来自于对现实的眷恋和拒斥,来自于对理想的圆满追求的渴望和无法真正实现的绝望”(托尔斯泰)?
事实上,绘画首先要做的就是忘记时间。时间确实是永不停留和不可逆的,我们会感叹“逝者如斯”的光阴流逝,一切早已变了样。如何去放慢时间?如何去凝固时间,哪怕只是一些敏感、脆弱、稍纵即逝的瞬间。慢一些,再慢一些,放慢作画的速度。缓慢是对与“速度”,对于“非慢”的拒绝,具有否定性的特征,而且“这否定性特征恐怕是比肯定性特点更有价值。”[10]绘画的缓慢与等待 ,在此刻,等待只是基本的状态;有时候,等待就是缓慢。 同时,缓慢是我们的一种生存状态,或是一种生命状态。在缓慢地等待过程中,在那一个个的瞬间,一切都似乎不动了,凝止了。就像芝诺所言说的飞矢不动的名言,向我们暗示了关于缓慢速度的认识。这是一种记忆的恢复——“在最严重的堕落之中,保留着对生命之纯洁的黎明的回念”。
缓慢:记忆的定格
《弗兰西斯·培根》一书的副标题为“感觉的逻辑”,这清楚指明了作者本人的逻辑出发点。“在德勒兹看来,尽管视觉征服了触觉,但触觉的功能和价值也并未完全消失,只是从此处于从属的地位。这集中体现在那些与手的动作直接相关的技法,诸如画笔等工具或手在画布上留下的一些偶然的痕迹”[11] ,而这些痕迹的本身往往“是非再现性的,非说明性的,非叙事性的。它们不再是有意义的,也不再是能指:它们是意指的痕迹。它们是感觉的痕迹。”[12] 同时“这些几乎盲目的手工痕迹证明了另一个世界对于视觉图解世界的侵入。在一定程度上,它们将绘画自那已经统治着它并事先赋予它图解性的视觉组织中脱离出来。” [13] 油画颜料的流动,偏离,堵塞——在这不断异化中重叠。流动挤破了边界,勿庸置疑,不再关注整体,这是一种自然的生长。不再受制于意志。这种不断地流淌的过程,要借助时间的堆积来完成,也就是说,用时间来完成对空间的挤压。最终,通过层层叠叠的痕迹,找到时间的某些线索。在明与暗的交界之处,在人与物的边缘,线条已不再限定体积和轮廓,这是情绪的存在,是运动的痕迹,而不仅仅是姿态和动作。
在这儿,如何把生命的体验化成了一团视觉的虚无?一切似乎都是陌生的,不再是关于“神”的崇拜,不再是个性化的再造的现实。他的简单之处,只在于简单——没有姓名的人物慢慢地被消解,淡化,逐渐失去了所拥有的一切,衣服,容貌,身体,性别,最后连个性也丧失了。在这个绝望的倦怠之地,人们没有任何的方向,也不等待,连时间也被无情地凝固了。在这儿,这些没有立体感和体积感的影子般的人物被冻结在无法明确测量的空间之中,突然变得安静了,一切似乎失去了重量——这是一种浮游的状态?这是一条无法回转的死路。随着坚硬残酷的法则和理性的结构的消逝,对它们的理解也无法借助时间来获得,日常的时间已变得暧昧不清,难以计算了。在这儿,在光与影的交合之中,在这瞬息万变的变幻流动之中,不断地涂画着这“丑陋”的表皮。人的欲望在于忙碌,关乎占用,准确地说,我们是无法进入这些微微张开的“缝隙”之中的,无法通过这些“光”进入永恒之地,尽管它们是这样无限地逼近你。在这些380x180cm的巨大画面里,每一个场景在召唤着你,去感受属于另一个人的现实和历史。渐渐,如鬼魅般的人物逼近我们,逼近我们生存的现实。它们从黑暗的尽头而来,你能微微感受到大地的振动。怎样使自己平静下来?无言的对视带来的只是深深的孤独和无法抹去的遗憾,记忆永远定格在那个“无害”的瞬间,世界早已不再流转。这些黑糊糊的团快是模糊晦涩的,是拒绝被阅读的——拒绝你进入,同时,又诱惑着你。我们除了左右为难,不知该如何表达和倾诉?
在这儿,情感如何在画面里渐渐得到升华,凝结成了一个实实在在的视觉实体?画面常常运用“聚焦”的手法,使得画面更像描绘一个事件,有着突出的中心人物,似乎在“还原”一个庄重的历史真实场景。事实上,恰恰是这个中心的“伟大的人物”却卑微地处于黑暗之中,人物被置于某种怪诞的景观之中,这是拒绝胜利者的出场?还是拒绝自由的恣意张扬?难道它们仅仅意味着失语和无为?也许可以说,对简单生活的再书写,在生活的书本上不断地书写着无效和暧昧的字体。无论是激情,震撼还是愤怒,已变得支离破碎,彼此矛盾,被充分地经过某种恰当合理的筛选与剪辑之后,被无情地贴上某种“马赛克”之后,可以安全放心地呈现给观者了。然而,我们还是被反复地纠缠在这浓重的黑色的迷雾之中,处于“终极,被动的迷茫之中”。
黑色的大气笼罩着整个画面,每个形状仿佛只是他的一种冰冻的状态。人们不得不面对自己许多“破碎的个体”,同时,自己又可以随时成为不同的自己。竭尽全力接近并接受强加于自己的全部的黑暗的阴影。这也许就是这简单生活的秘密,在不停游荡之中,实现着自己的“黑色的狂想”。
结语
尼采早早地在他的笔记中写到:“如今,哲学应是文化的毒药”。(笔记,页97)像《玫瑰之名》中的约尔格,“尼采在自己的书中涂满毒药,阴险地企图让启蒙后的文人学者们读后一个个死于非命。”[14] 绘画对于我们每一个艺术家,何尝不是毒药呢?与尼采不同的是绘画只是我们自己的毒药。绘画的缓慢在于它的无效性,无法直达目的,也就是无法立刻生效。成功的喜悦就如在本雅明的著作中那遥远而迟缓的土星,处在椭圆形轨道的最远端,它莅临的周期是如此漫长而缓慢。
“每当理智对自身茫然不解时,它便正处在一片漆黑之中,但作为探索者,它又必须去寻找;在此,已知的一切对它毫无用处--这不只是寻找,而是创造;理智面对着的是一些远未成形的东西,但又只有理智能够意识到它们”(普鲁斯特)。总之,“陌生化”的处理方式,抽象的画面结构,组合的非理性化,僵硬的造型特点,以及不断流动的表现手法——表面形象的张扬,奔放,与内心的麻木,甚至是不断伪造的激情形成了一种对比,组合成了这样一个宏大虚伪的场景。这些不断复制中的没有特点的人物,却慢慢地拥有了巨大的控制他人的力量。当代历史的大踏步快步向前,“以同质而空洞的永不可逆的暴力压抑着生命时间沉静而丰富的绵延”。如何以某种缓慢的时间方式“打断现代性的机械时间链条并尽力挽救已然逝去的经验”?[15] 我似乎在我的短诗中给出了答案: 在这短暂颤动的平常日子/要和黑夜一样的沉默/ 缓慢,以静止般的速度/等待与自己的和解。
注释:
[1][5]米兰•昆德拉著,马振骋译:《慢》(缓慢),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10月版,p2。
[2]向以鲜 《缓慢:与死亡对抗的一种方式 》
[3]孙甘露 《比“缓慢”更缓慢》
[4]赵峥嵘《谁能给我未来》发表与《国家美术》2008/8,p167。
[6]本雅明著,陈永国译:《德国悲剧的起源》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版,p124。
[7][15] 参见苏珊·桑塔格:本雅明《单向街》导读,张新颖译
[8]赵峥嵘《此刻四》《此刻》共写了四首。其他如《此刻一》此刻,/只是寻常的时间/一切正常/我已从绝望中逃脱。/在此刻,/我是卑微的/被时间吞噬,/正退化成背景。/此刻,/夜幕降临/光照在黑暗里/永无休止的只有开始;《此刻二》此刻,在黑夜里/累了,我要顺流而下。/在此刻,宁愿永远留在黑色里/没有历史/也没有未来/此刻,遇见了寂寞,伴着那黑影!/心跳急促,/我要满怀喜悦;《此刻三》此刻,仅此一次/失语已久。/已说了太多的话/在此刻,从黑夜离去,/又走入黑夜/失去了,所有的瞬间/此刻,为了/认识自己/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9]汉娜.阿伦特著,王凌云译:《黑暗时代的人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p119。
[10]参见本雅明:《致格尔斯霍姆·朔勒姆的信》,《经验与贫乏》,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p385。
[11]耿幼壮《德勒兹论培根——思考/绘画》
[12][13]Gilles Deleuze, Francis Bacon: the Logic of Sensation, p.100, p.101.
[14]刘小枫 《 尼采的微言大义》,书屋 2000(10)。
【相关阅读】
【编辑:于睿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