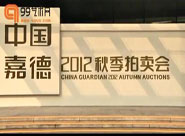推进:比较与归纳
那么,上述二十年之间,国内学术界对图像学的研究是怎样发展的?我们且看一个具体的学术案例,即易英的长文《图像学的模式》。此文旨在探讨以潘诺夫斯基和贡布里希为代表的两种图像研究模式,其探讨的依据,是这两位艺术史学家的原著,以及西方学者对他们的研究。就西方学者对潘诺夫斯基的研究而言,在英语学术界有两部著述最为重要,一是伯德罗(M. Podro)的《批评性的艺术史学者》,1982年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再是迈克尔·安·霍丽的专著《潘诺夫斯基与艺术史的基础》,1984年由康奈尔大学出版社出版。此外,研究潘诺夫斯基的重要学术论文或专著章节,还可举出凯丝·默克希(Keith Moxey)之《理论的实践:后结构主义、文化政治与艺术史》一书的第四章《潘诺夫斯基的忧郁》。后两者是美国艺术史学界最早倡导视觉文化研究的先行者。霍丽研究潘诺夫斯基的专著由易英译为中文,1991年出版。十多年后,易英发表《图像学的模式》[4],既是对潘氏图像学的研究,也涉霍丽的研究。
易英在《图像学的模式》中探讨了潘诺夫斯基的图像阐释模式“历史的重构”,也在对比中探讨了贡布里希的图像阐释模式“方案的重建”。文章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旨在说明图像学的目的是探讨作品的意义,并借霍丽对潘诺夫斯基的研究而指出了潘氏理论的符号学基础。若用索绪尔之结构主义和二元符号论的眼光看,潘氏所谓图像是作品的表象,而作品的含义则隐藏在这表象背后,二者的关系即言语和语言,或能指与所指的关系。易英认为,潘氏图像学超越了索绪尔理论,因为艺术作品具有历时和共时的双重特征,受制于某时某地之阶级、宗教、哲学等因素的制约。这样,潘诺夫斯基的图像学便走上了阐释学的路子,例如潘诺夫斯基对提香绘画《谨慎的寓言》的阐释,便在“阐释的循环”中强调语境对图像含义的决定作用。
易文第二部分探讨潘诺夫斯基在《新柏拉图主义运动》中对提香另一绘画《人间的爱和天上的爱》所做的阐释,将此画之图像文本的语境锁定为新柏拉图主义的哲学和神学观念,并通过这样的文化语境来阐释提香绘画的含义。在此,潘氏触及了图像的含义与艺术家的意图之间的失谐关系,也即图像的含义可以超越作者的原本意图,尽管是不自觉的超越。潘氏这种透过图像表象、超越作者意图的阐释,因倚重于历史文化条件的决定性而成为“历史的重构”,成为一种阐释模式。
文章第三部分讨论贡布里希的图像阐释模式,即通过重建图像的方案,来追溯作者的原意,其阐释案例是对波提切利绘画《维纳斯的诞生》的研究。贡氏模式的要义有二,一是通过历史文献的证据来追溯最初的绘画方案,例如方案的提出和设想,二是探讨这一方案怎样诉诸图像,也就是通过图像研究来逆向重构这一方案。
通过描述、比较和归纳,易英的文章指出了这两种模式的区别,这就是潘诺夫斯基偏向德国二十世纪哲学中的阐释学,而贡布里希则偏向同一时期的形式主义,却又不受制于英美形式主义的文本局限,而力图揭示作者的意图。于是,我们作为这篇文章的读者,便看到了一个递进的阐释:形式主义受制于图像文本,贡布里希超越图像文本而将作品的含义引向了作者的意图(形式主义者称此为“意图的谬说”),而潘诺夫斯基则更进一步,不仅超越图像文本,也超越作者,将作品的含义引向文化和历史的前提。于是,这里实际上有三个图像阐释的模式:形式主义、贡布里希、潘诺夫斯基。
易英对图像学的归纳总结没有停留于图像学本身,而是将这一理论引入对艺术史的研究和对中国当代艺术的批评实践中。对此有兴趣的读者,可以阅读易英的文章《图像的集体阅读与社会心理》、《图像的象征》、《图像的专治》、《公共图像与现代图像》等。其中,第一篇文章从阐释西方艺术转向阐释中国当代艺术,第二篇文章是中国当代艺术的个案分析,后两篇则从艺术阐释进入视觉文化研究,将艺术史研究领域里的图像学引向了后现代以来之文化研究的领域,使图像学理论的实践意义大为扩展。
四、深入:图像转向
由于译者和学者们的努力,图像学已在中国学术界广被接受。自21世纪初以来,无论是研究图像理论,还是将其付诸艺术史研究和艺术批评的实践,越来越多的后起学者都表现出极大热情,以至于到2007年形成一股图像批评的风尚,称“图像转向”,呼应了中国当代艺术中的图像化或图式化潮流[5]。
“图像转向”之说进入中国学术界,起自2006年米歇尔《图像理论》中译本的出版。该书作者开篇即借西方哲学研究中的“语言学转向”一语,提出了自己的“图像转向”观点,并这样阐述之:“图像转向……是对图像的一种后语言学的、后符号学的重新发现,将其看作是视觉、机器、制度、话语、身体和比喻复杂的互动”[6]。这就是说,在后现代的学术语境中,米歇尔所说的图像与潘诺夫斯基的图像不是一回事,不是潘诺夫斯基图像学的复兴,而是另起炉灶,也即从潘氏的现代图像学,转向后现代和当代图像学。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米歇尔即以图像研究而成名,他的《图像理论》原著出版于1994年,而书中首篇《图像转向》则于1992年发表于《艺术论坛》杂志。这样的年份告诉我们,西方“图像转向”的学术语境是后现代文化思潮的高峰,距其终结已为时不远,那时,文化研究已经在西方学术界出现了。对于中国学术界来说,“图像转向”这一术语在十多年后的2006年后半年被引入,于2007年在美术界引发理论研究和批评实践的热情,而这时后现代在西方已经结束,在中国也已不再时髦。语境决定含义,在中国当代艺术的语境中借用“图像转向”一语,学者们对此语含义的阐释,与米歇尔的本义并不完全相同,中国学者偏向思想文化的批评。
更重要的是,米歇尔批评潘诺夫斯基的图像学,认为其不涉视觉艺术的形式因素,而米氏的图像转向则是要在后现代的思想文化条件下,强调图像的视觉形式[7]。此时,中国的当代艺术及其批评,是一种文化批评,视觉形式从属于思想文化,因而图像批评是一种思想文化批评。在这样的学术语境中考察,我们就可看到,中国当代学者之图像批评的思想文化特征,集中反映在2007年出版的《艺术》集刊第一辑图像研究专号中。
这是四川大学艺术学院主办的集刊创刊号,共有四个专题,分别是《图像的政治》、《中国当代美术思潮》、《当代油画图像修辞学转向》和《当代文化的视觉转向》。在第一个专题中,栏目主持人的导言明确指出了中国当代艺术中图像批评的思想政治特征,这就是“揭示图像背后意识形态话语的生产与再生产,图绘一幅当代中国思想与话语的权利谱系图,以期将中国当代美术研究与写作引入与思想史相关的宽广领域”[8]。这一专题内的三篇文章,一是探讨布尔迪厄的艺术政治和权利诉求,二是探讨中国当代艺术面对西方强势文化影响的本土化问题,三是探讨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影响。这三篇文章从不同角度阐述艺术的政治问题,殊途同归,都强调了图像的思想文化和政治性。
实际上,对思想文化和政治性的强调,不仅是二十世纪中期以来中国学术研究的主导,也是中国当代学术中图像研究的主导,这在第三个专题中表现得更为具体,这便是将思想文化的探讨,引向艺术的商业化问题。在这一专题的三篇文章里,鲁虹的《中国当代油画创作中的图像修辞学转向》一文,从大众传媒的角度切入,将中国当代绘画的世俗性,归结为媒体的影响。何贵彦的《“图像转向”的依据与误区》一文,则从西方波普艺术之影响的角度切入,分析了中国当代艺术图像的符号化问题,并由此指出其低俗性。方志凌的《身体的隐喻》一文,虽未涉及大众传媒,但以“凝视”为关键词,这是当代影视研究和传媒研究的关键词,此词于有意无意间将中国当代艺术里的身体图像引向了通俗文化。
在当代学术语境里,艺术的政治性和商业性因大众传播而混然一体,《艺术》第一辑的其它专题和文章,在研究图像问题时,无不以这一现象为关注点,而这也正是中国当代学术界之图像研究的特征,是图像转向后的学术特征。
高潮:批评实践
中国学术界和艺术界的图像热,主要是借助潘诺夫斯基的图像阐释法和米歇尔的图像文化理论,来检讨今日通俗文化和当代艺术中的图像化倾向。在一定程度上说,这阵热潮是由于为这一倾向找到了“图像”一词的标签而出现的名正言顺的喧哗与骚动。所谓名正言顺,就是有了图像之名,可以对这一倾向辩症施治了。在2007和2008年的中国艺术评论界,“图像”一词成为头号关键词,各种艺术刊物,不论是官办还是民办,也不论是学术性还是商业性的,无不以图像批评为招徕。有鉴于此,中国批评家年会的会刊《批评家》杂志在2009年8月出版了专号,从视觉图像与书写语言之关系的角度,对图像热进行了总结性的梳理和匡正。
这是《批评家》第四辑,主要有五个专题,分别是《理论前沿》、《现象解剖》、《一家之言》、《反思批评》、《理论视野》。其中第一专题的主题是图像与文本的权利关系,刊发了两篇文章。第一篇是邹跃进的《视觉图像与书写语言之间的权力史》,此文从西方图像理论的发展历史和艺术哲学两方面,来探讨书写语言对视觉图像的支配,以及二者间的权利消长,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中国学者之图像研究的深度和水准。第二篇是戴陆的《媒体领域中视觉图像与书写语言的交互关系》,该文以后现代话语来讨论大众传媒里的图文关系,此文说明中国学术界的图像研究已涉及前沿话题。
第二个专题也刊发了两篇文章,从图像理论走向当代艺术的研究和批评实践,一篇讨论自然灾害的新闻图片与当代艺术的关系,另一篇讨论书法美学与当代艺术的关系,认为图像和文字的意义是没有止境的。第三个专题刊发了周彦的一篇文章,也讨论图文关系,也从西方的图像理论走向中国当代艺术的批评实践,所涉话题更为宽泛,但对当代艺术的探讨也更为深入。不过,周彦的结论是文字比图像重要,表面看是顺应了文字代表文明产生的史实,实际上是为鸡与蛋孰先孰后的问题给出了一个过于绝对的答案。
第四个专题是对图像理论的反思,其中鲁虹的文章《面对“图像转向”的批评》从作者个人的策展经历切入,通过对西方艺术理论史的叙述,来检讨中国当代学术界和批评界对“图像”概念的理解。作者在文中将图像转向的问题归纳为三点,其一,取消了艺术与生活的界限,其二,打破了经典艺术与大众文化的界限,其三,新样式新媒材取代了传统的样式和媒材。作者认为,由于这三点,旧的艺术标准动摇了,当代艺术不再以美为追求。作者的阐述把握了中国当代艺术的一个重要方面,即以图像的发展来代表当代艺术的演进。同一专题的刘晋晋文章《图像的晕头转向》是一篇个案研究,讨论米歇尔之“图像转向”概念的来龙去脉和含义,以及怎样通过翻译而进入中国学界,又怎样因翻译问题而被中国学者误读。
第五个专题中有周功华的文章《图像修辞:语义的限制与超越》,讨论艺术史研究的方法问题,从怀特·海登的“历史诗学”概念引出治史中的“图像修辞”问题。作者这样解说海登的史学研究方法:因回归历史叙事而有文学修辞的必要,这就“意味着回归到隐喻、修辞和情节化,以之取代字面上的、概念化的和论证的规则。而充当一种恰当的史学话语的成分”[9]。作者之谓“图像修辞”,实为西方新历史主义和新艺术史的符号学方法,此方法不同于旧的索绪尔和皮尔斯方法,而是以布莱逊为代表的新符号学方法,这是当代学术中进行图像分析的一种方法。这篇文章虽短,其价值却在于涉及了艺术史研究中的方法论前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