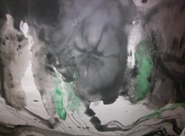陈永锵作品
陈永锵总是爱说话。陈永锵总是爱和树说话,因为树总是爱和陈永锵说话。久而久之,陈永锵有时和人说话也像是和树说话一样,因此,常常引来一些意外。因为,“人非草木,孰能无情”。这“情”就是“人情”——人的情,而“人情”是连着“世故”的,所以说“人情世故”。但在陈永锵看来,草木——树,孰能无情。而且,他们并不“世故”。所以,在这个太多“世故”而太少“人情”的世界上,陈永锵更爱和树说话。
这次的主人是——木棉,说话的是“树”,陈永锵只是“笔录”。
树要长得像“树”,你才会和他说话。就像人要长得像“人”,你才会和他说话。陈永锵的树是像“树”的——木棉就是木棉,这才是“木棉”。可能,陈永锵的木棉更“木棉”。我们往往误会了文人画的一个关键要义——“不求形似”。“不求形似”并不是——也决不是求“形不似”。它“求”的是在“形”之外,而与形的“似”或“不似”都没有关系。问题不在于“不求”什么,而在于“求”什么。
那么,陈永锵“求”的是什么。
“不求形似”的极端标杆是倪云林。但任何人看到倪云林的竹都不会是看成“芦”或者“麻”的。我们往往没注意到他的——也许是更重要的话:““长吟挥毫为君起,写其形模唯肖似,谅哉直清可与比。”(《写墨竹赠顾友善》)在这里,不但“形似”更要“唯肖似”。他“求”的是什么,是“直清”。“夫子所好者道也。放乎竹矣。”(苏辙《墨竹赋》)而陈永锵“求”的是“生命的尊严”。
这里,让我想到了“画中有诗”。这又是一个文人画的关键要义,但也像“不求形似”一样往往被误会。我们往往把诗认为是西方分类中的,与小说、散文、戏剧并立的一种文学样式,而且以抒情诗为准。但在中国文化的系统当中,“诗”是“经”是“教”是“国”,是核心价值观的表达。中国人说“文以载道”“诗以言志”。陈永锵是个诗人,他当然知道中国“诗”的意义;陈永锵是画家,他当然知道“援诗入画”的意义。“画中有诗”就是以画“言志”。陈永锵画画是“游于艺”,绝大多数画画的人也都这样说,大概也都这样想。但绝大多数画画的人都“游”不起来。为什么。我想,其中根本的原因是他们不知道“画中有诗”。“游于艺”的根本是“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然后才能“游”得起来。而陈永锵知道“诗言志”,这“志”就是“道”——“志于道”。而倪云林求的“清直”,就是“诗”就是“志”就是“道”。而这“清直”,必须“写其形模唯肖似”才能“求”得。说到“诗”,自然想起《诗经》,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论语•阳货》)“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如果“形不似”恐怕是“求之不得”的,“寤寐思服”“辗转反侧”也没用。
米兰•昆德拉说:“文学让人理解他人的真理。”陈永锵的树,让人理解“树”的“真理”。这是他在“连年”对树的“仰望和‘玄观静览’”中得来的,并“记录在案”。这就是“澄怀观道”。这就是“格物致知”。这是朱熹意义上的“格物致知”——以“树”来推究“真理”;这是王阳明意义上的“格物致知”——把“树”放到它“应该”的“正”的位置上,来理解“真理”;这也是郑玄意义上的“格物致知”——从因你而来的“树”上看出你的“品德”;这更是司马光意义上的“格物致知”——你必须“隔绝”“物”欲的干扰才能看见“真理”。康德说:“人只能够看到你知道的东西”。有心中的“道德律令”才能看到头上的“灿烂星空”。当我们“看到”陈永锵“树”里的“真理”的时候,我们也就是看到了陈永锵的心中。这“树”刷新了我们的眼光,他让我们看到了我们“自己”。他让我们为了自己能够坦然地站在“树”的面前而不自惭形秽而加油。
中国“文人画”对中国文化是有“承诺”的。他承诺,让我们“澄怀观道”。当陈永锵说自己是个“文人画家”的时候,他就是这个“承诺”的担当者——就是他举起右手紧握拳头说出了“誓言”。他说:“不知这是否对,但我由衷认定了。”于是,他“向自己的心灵深处走”去。陈永锵在“自己的心灵深处”与“树”共同寻找与铸造生命的意义与尊严,共同填充意义核心的“空洞”。
“伐木丁丁,鸟鸣嘤嘤,出自幽谷,迁于乔木。”。陈永锵“出自”广东南海西樵山之“幽谷”,“迁于”自己画的“乔木”。
放眼望去,陈永锵的“树”——“乔木”,“木秀于林”。三国魏人李康在《运命论》中说:“木秀于林,风必催之……然而志士仁人,犹蹈之而弗悔,操之而弗失,何哉?将以遂志而成名也。”“志”为何物,“志于道”也。
陈永锵的“树”是“非虚构”的。他记录的是“真话”。“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我想,陈永锵和他的“树”也“应如是”。
说到“鸟”说到“迁于乔木”说到“风必催之”,让我想起了多年前曾经流行的一首歌——《我是一只小小鸟》:“有时候我觉得自己是一只小小鸟,想要飞却怎么样也飞不高,也许有一天我攀上了枝头却成为猎人的目标,我飞上了青天才发现自己从此无依无靠。”今天,这只《诗经•伐木》中的“鸟”与他的“乔木”一起“迁于”北京。我想,他会鸣:“所有知道我的名字的人啊你们好不好,世界是如此的小我们注定无处可逃,当我尝尽人情冷暖当你决定为了你的理想燃烧,生活的压力与生命的尊严哪一个重要?!”他说:“我祈望的是:我的诚意与芳心能得到首都人、尤其是专家同行们的青睐。此刻,除了无尽的感激外,更向首都人民致敬!”“嘤其鸣矣,求其友声”。这是在向首都的“友声”们“由衷致敬”。
真理长什么样?我们寻找真理为什么就这么难。
其实,真理长得就像树一样——像陈永锵画里的树一样。
【相关阅读】
【编辑:谈玉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