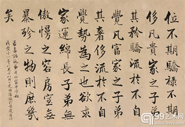我想,贺敬之说的“发了一批在北京发不出来的文章”,一定也包括我评徐冰“天书”的《“析世鉴”五解》,因为在这之前,杨成寅已在他的《新潮美术论纲》中对徐冰的作品和我文中的观点给予无情嘲弄(徐冰的《鬼打墙》的取名正是来自于他的嘲弄)。这一情况意味着不仅批评家的批评文本已经失去了生效的场所,批评家已经发出的文章更难免批判的厄运。
在1990到1991这两年中,借助89政治风波走马换将的美术界正酝酿着一场反自由化和清算新潮美术的运动。而于1991年4月由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主办的“新时期美术创作学术研讨会”(即“西山会议”)则成为这一清算的突破口。这个会议是自89政治风波以来,中国当代艺术发生逆转后批评家第一次比较大型的聚会。研讨会由当时美术研究所所长水天中、副所长王镛主持,80年代以来一些重要的理论家、批评家都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对改革开放以来美术创作的成绩(包括85美术运动)给予充分肯定,并对90年初新出现的创作倾向给予了及时关注。记得当时栗宪庭拿着一篇已经写好的稿子在谈玩世现实主义和“泼皮”问题,已经对89后的新艺术有了新的思考。但到9月,《中国文化报》发表了署名为“钟韵”的长篇批判文章——《“西山会议”的主持者坚持什么艺术方向?》,文中称 “新时期美术创作学术研讨会”的主持者把美术界这个“重灾区”当成“丰产田”来加以赞美;打着“平等”的幌子,对新潮美术的方向性错误给予辩护和肯定;鼓吹新潮美术还要继续“走向成熟,开始新阶段”。中国美协内部刊物《美术家通讯》全文转载了此文,《美术》杂志也同时连续刊发批判“新时期美术创作学术研讨会”的文章。加上此前已经刊发的其他批判文章,将美术界自89以来长达两年多的反自由化热潮再次升温。
因此,1989年在中国当代艺术史上是一个重要的分野。这一分野不仅表现在艺术的走向上发生了逆转,而且在批评介入当代艺术的方式上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如果说80年代的艺术批评主要是通过批评家和编辑家的联盟来影响当代艺术,那么,进入90年代,这种“联盟”的条件不存在了。《美术思潮》、《中国美术报》被勒令停办,担任主编和编辑的批评家(如邵大箴、高名潞)也纷纷“下野”。《江苏画刊》虽然保留下来,但主编刘典章、主力编辑陈孝信也先后被撤换。因此,刊物不再成为“文本批评”生效的场所,更失去当代批评“中心环节”的有力地位。批评家籍以实现“话语权”的“载体”被抽空了,只有改弦易辙,从单一的“文本批评”转向民间化的“展览操作”,即从批评家的编辑角色转换到“策展人”的角色。
策展:批评家身份的再度转换
“策展人”这个角色在西方艺术体制中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甚至可以说,西方的展览制度就是以策展人为中心的策展人制度。这是一种以学术为本位的体现。在中国,批评家以策展人的身份出现,完全为时代所使然,也是为批评家的学术使命所使然,它经历了一个从自发到自觉的发展的过程。应该说,这一转化最早起始于1989年的《中国现代艺术展》。这个由批评家发起并组织的艺术大展,既是对85美术运动的一次检阅和总结,也为批评家介入当代艺术提示和开启了一种新的方式:使批评家从写字台后移位到展览现场,成为一个有主题的学术性展览的策划者和组织者。虽然那时的批评家还没有明确的“策展人”意识,也没有“策展人”这一概念,但就中国现代艺术展的整个筹备过程看,高名潞、栗宪庭等批评家所扮演的已经是一个“策展人”的角色。参与到这个展览筹备中来的批评家构成了最早的策展团队。
中国现代艺术大展的筹备过程十分艰难,一方面是官方意识形态的控制,一方面是筹款的艰辛。这从高名潞1986年底给我的信中可以略知一二:“我们和《美术报》正筹备明年五、六月北京中国现代艺术大展,并拟届时成立中国现代艺术研究会……你能否在内蒙拉点赞助,目前最困难是经费,由美术报等单位出证明,必要时可派人协助你,哪怕赞助少量万、八千的,以救燃眉之急,因宣传、印刷、联络等均急需钱。”我为筹钱的事找过几个认识的企业界人士,但都无结果。他接着来信宽慰我说“赞助之事多承你如此费心,但不要为难,内蒙的大户毕竟较少,不可勉强……但展览定要如期举行,因场地已定”。他说的“场地已定”是指定在农展馆。而不是后来的中国美术馆。两个月后,即87年4月,他又在信中透露出更加无望的消息:“四月四日中宣部给文联和各协会下发了一份文件,指出目前一律不搞全国性的学术交流活动、会议、展览等,以免引起思想混乱……同时还提到,未经中宣部批准的全国性的活动,各企业、事业单位不得给予赞助,赞助者将追究责任”。虽然高名潞办展的信念坚定,但举步之维艰由此可见一斑。直到1988年底1989年初,一切筹备就绪,中国美术馆的场地也谈妥,但资金仍无着落,直到他以个人名义借资五万以解燃眉之急,后又找到三万多元的赞助,才使“中国现代艺术展”有了付诸实施的可能。虽然延至1989年2月才在中国美术馆举行,但其空前的规模(展出186位艺术家的293件作品)和突发事件所造成的新闻效应是史无前例的。枪击发事件和匿名信,展览曾被两次停展,展览期间那种不安和不确定因素以及整个展览的氛围几乎是对即将发生的历史事件的一次预演。
但从展览策划的角度看,“中国现代艺术展”也是批评家转向策展人这个角色的初次演练。可以说,出现在1989年的“中国现代艺术展”,和以往所有的大展不同,它在中国当代艺术史上构成一个十分重要的事件。这个展览从策划到联络各主办单位到寻找资金到筹展的全过程,均由批评家亲自操办。参与到这次展览筹备中来的批评家除了高名潞(展览筹委会负责人)、栗宪庭(负责展厅设计)之外,还有:费大为(负责对外联络宣传)、孔长安(负责作品销售)、唐庆年(负责经费安排)、王明贤(负责其他日常事务)。此外,刘骁纯、范迪安、周彦等都是筹委会成员,殷双喜、高岭和黄笃也都参与到具体的筹展工作之中。可以说,这个展览是新时期以来第一个由批评家组织策划的大型艺术展,也是80年代唯一的一个由批评家策划和主持的大展。这个展览不仅是对85现代美术运动的一次总的检阅,也是批评家在90年代转向一种新的工作方式的一次预演。批评家在这一活动中遇到的所有困难、问题和尴尬局面,都在90年代的此类活动中一而再地重演。因此可以说,中国现代艺术展在中国当代艺术史上所产生的影响,在意识形态领域所产生的震动,以及在社会层面所产生的新闻效应,都是批评家联同艺术家一手制造的。
进入90年代,这种角色的转换已经成为批评家的一种自觉选择。首先是王林于1991年策划的“北京西三环艺术研究文献(资料)展”第一回展,接着是吕澎策划、由十几位批评家集体参与的1992年“广州首届90年代艺术双年展”、由水天中、郎绍君、刘骁纯、贾方舟等集体策划的1993—1995年的“美术批评家年度提名展”,以及批评家个体以“独立策展人”身份策划的许多规模不等的大大小小的展览。90年代,可谓一个批评家转向策展的策展人时代。
上述三个展览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都是批评家面对新形势、新问题迅速做出的反应和创造的方式。它们都是众多批评家参与的成果,又各自创造了不同的展览模式,起到了不同的作用。
1991年6月,由王林策划并主持的“北京西三环艺术研究文献(资料)展”第一回展在中国画研究院画廊开幕。之后又到南京、四川、东北、广州等地巡回展出;后又连续举办五届,前后历经十年时间,贯穿于整个90年代。这个展览的特殊性在于,它是在批评失去传播条件的情况下创造的一种新的“传媒方式”。这个展览展出的虽然不是原作,却是89后第一个反映中国当代艺术现状的重要展览。该展相当于“刊物”的变体,可看作是以展览的方式“编辑”的一份具有文献价值的“刊物”。由于89后有关当代艺术的信息传播渠道被切断,前卫艺术的合法性成为一个问题。艺术家各自为政,失去了相互沟通的媒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批评家以非出版的文献资料(出版要经官方审查)通过民间化的展览方式呈现出来,重新架设起一座信息传播和学术交流的新渠道。这个展览打破了90年代初那种特有的沉寂气氛,让批评界和关注当代艺术的画界同人有机会了解到89后中国当代艺术的一些真实面貌和发展动向,从而使这个展览得到多方面的支持、批评家的广泛参与和关注。
由吕澎策划的“中国广州首届九十年代艺术双年展”于1992年10月在广州中央大酒店展览中心开幕。这是继89年中国现代艺术大展以来又一次由批评家出面组织、策划的一次大型展览活动。参与该展的批评家有:吕澎(总策划与艺术主持)、皮道坚(艺术总监)、彭德(监委主任)以及评委邵宏、严善錞、易丹、杨小彦、黄专、祝斌,监委殷双喜、陈孝信、易英、顾丞峰,学术秘书杨荔。
这个展览是在官方全面封杀前卫艺术的情况下,试图借助资本市场为其开辟一条生路。也是批评家在对市场缺少足够了解、不知其深浅的情况下,带着浓重的理想色彩的一次批评探险,一次试图利用市场却最终被市场所左右的的批评实验。批评家以这样的“大兵团”集结方式,以一个非常良好的愿望——试图通过学术来引导市场。实际效果是一厢情愿地将前卫艺术强加于市场,并试图通过这一努力使批评家尽快进入“市场情境”,在市场情境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确立批评的职能和批评的价值。这一“批评案例”反映了一批年轻的批评家对市场经济的悄然兴起和社会转型的敏感,以及面对新问题所取的积极应变的姿态。正是在这一新的“情境”中,他们发现了可以实施新的文化策略的机会。但他们在挫折中又很快发现,他们所建构的“市场理论”的虚妄,发现中国的艺术市场不过是他们的“不成熟理论推导的结果”,发现客观上并不存在完成他们这一文化策略的机制。
但广州双年展为在艺术市场中建立批评的权威性而创建的一套学术操作规则,却成为90年代批评家策划展览的一个基本模式,即借助民间经济力量来完成一个学术构想,或者也可以说利用批评家的学术身份说服和引导投资者向当代艺术靠拢。批评家们在90年代策划的学术性展览基本上都没有离开这一模式。批评家将希望寄托于民间资本的介入,其目的是在实现艺术的“自治”,以摆脱政治的干预。虽然在这一过程中,批评家常常陷入尴尬的处境,但出于一种学术责任,他们还是一次次地勇往直前。继广州双年展以后,如何通过批评引导市场,依然是批评家不断尝试解决的课题。几位更年轻的批评家如冷林、冯博一、钱志坚、高岭、李旭、张晓军等,在96、97两年连续与中商盛佳拍卖行合作,继续尝试把中国当代艺术推向市场。
十几位著名批评家联合行动,连续举办三届的“美术批评家年度提名展”(1993—1995),试图以一种纯学术的方式操作。三届提名展的艺术主持人分别是:郎绍君、水天中、刘晓纯。这项活动的出发点不同于广州双年展,主题不在批评如何介入市场。在《美术批评家年度提名展(1994)》画集“后记”中说,“提名与展览的目的是以集中的批评力量关注和研究有成就有创意的艺术家并逐渐提高参与批评家的学术水准”。所谓“集中的批评力量”即是对“集团批评”方式的另一种表述。虽然这种方式后来遭到不少人的反对,但毕竟是90年代中期以前批评活动普遍采用的一种形式。其目的在于加强批评的力度。90年代中期以后,由单个的“独立策展人”策划展览逐渐成为主导。这个变化反映了自发的、民间化的策展制度逐步形成的过程。
总结广州双年展在后期操作上的失控,提名展制定了如下规则:在共同参与的艺术批评家、艺术家、艺术投资人三方中,“美术创作者是主角,批评家负责学术活动,企业家负责艺术投资和经济操作。企业家不干预学术活动,批评家不干预经济操作。三方各对自己的行为独立负责”。可见,批评家提名展试图通过纯学术的“集团批评”方式的持续运作来影响当代艺术的发展,同样是一种文化理想。在实际运作过程中,既难以做到学术应有的纯度,更难以做到运作上的“持续”。因为批评的话语权最终还是操控在出钱人的手里。
策展,作为90年代的批评家在批评方式上的战略转移,既是为突然剧变的形势所迫,也是面对新的社会条件积极寻求更有效的批评方式的主动选择。通过策划一个展览来表达批评家对当代艺术的某些思考,这不仅是一种广义的批评,而且是一种“权力批评”,因为“话语权”握在策划人的手里。是批评家通过策展活动和展览主题的阐释所获得的一种话语权力。从确立主题到选择艺术家,既体现出策展人对当代艺术问题的学术判断,又体现出策展人对参展艺术家或取或捨的眼力、权利和准则。这在某种意义上是比“文本批评”更有效的批评。
策划和操持一个展览,不同于往日的批评家角色,只需要单纯的案头思考。从主题的确立到艺术家的选择,从资金的筹措到各项展事的落实,不仅需要敏锐的学术眼光,还需要有和方方面面的人周旋的耐心以及干练的办事能力。因此,策展人不只需要有批评家的素质,还需要有一种实际的组织和实践批评的能力,因此也可以说,策展人是既有案头做学问的能力,又兼具实践能力的批评家。
批评家在市场兴起的90年代,还有一个集体性的举措就是为维护智力劳动权益共同订立的“批评家公约”。1992年10月,在中国当代艺术研究文献资料展(广州)研讨会期间,批评家就维护自己合法权益问题私下磋切并达成共识,形成一个初步意向。年末, 30余位美术批评家借用在北京集会期间,就维护智力劳动权益订立公约,明确提出应邀撰写评论文稿要付报酬。记得当时是双喜负责公约的起草,并由每个批评家在公约上签了字。“公约”在《江苏画刊》以报道形式刊出后,在美术界引起很大反响。应该说,这个事件反映了作为个体的批评家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无奈与失落。为贫穷所累的批评家这种起而“保护自我”的应变措施本身,已经使他们失去了应有的学术尊严,使他们作为一个批评家的身份掉价,至少在当时看来是如此。因为,批评家的文字升值了,由文字构成的“批评”却贬值了。但已经适应市场时代的画家们很快从轻蔑、非议和抵制转变为默认和赞同,并且主动遵守“公约”的规定,以高额稿酬请批评家写评论。但对于批评家来说,稿酬的剧增(“公约”规定的稿酬是原来法定稿酬的10—20倍——每千字300-800元)虽然多少可以改善一下批评家的生存条件,却未能使他们真正摆脱精神困境。诚如易英所说,在社会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知识分子这种寻求自我保护的方式,“是以学术的牺牲为代价”的。因此,不妨说,“批评家公约”既是批评家在市场胁迫下的一次“自我拯救”,也是一次集体性的以“自我伤害”为代价的“自我保护”。在那个集权年代,这些自嘲为“爬方格子的”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排行“老九”,当他们被卷入商业大潮以后,他们发现,他们的经济地位依然使他们无法有尊严地生活。他们整天价为中国的当代艺术操心,却没有办法改善自己的生活。好在他们的心思并不在如何生活得优越,刘骁纯在1991年初给我的一封信中以凝重、悲壮而又自信的口吻说:“事实上我们是可以自慰的,我们有一批自己的峡谷中的一流理论家……这批人在精神上互相支撑,在地狱的火海中挣扎,他一面接受着旧教派的宣判,一面接受西方新教权贵们的嘲弄……我们对于非学术较量不在行,难免遭受很大损失;而我们的学术研究又不能全身心投入,水平也自然要受到严重局限。看来没有别的选择,一代又一代的赤子,用他们的血肉堆积成学术与非学术错杂而又躁乱的土丘,是填平峡谷铸起金字塔的唯一可行的过程”。这不惜牺牲的悲壮,诚如吴冠中先生在给我的信中所说:“希望在你们身上,你们应为中国的美术理论工作作出真正的贡献,粉身碎骨!”
一个刊物记者在采访我的时候曾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在当代艺术中,批评家与艺术家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我回答,批评家不是旁观者。批评家是当代艺术的亲历者、参与者、见证者和推动者。批评家不只为当代艺术推波助澜,批评家也与当代艺术家一同经风历雨,一同艰难成长。
( 发表于《艺术当代》2013年第三期)
【相关阅读】
【编辑:谈玉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