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亚特是公开不大看得上J. K. 罗琳的,以为她的魔幻不够格调,遏杀了人们的想象力。我觉得单纯从文字角度,这两个人不在一个水准。罗琳相对单调,而拜亚特能复现维多利亚时代的桂冠诗人的诗篇与书信,完全以复古的传统英文突出文章的色泽美、韵律美。
文 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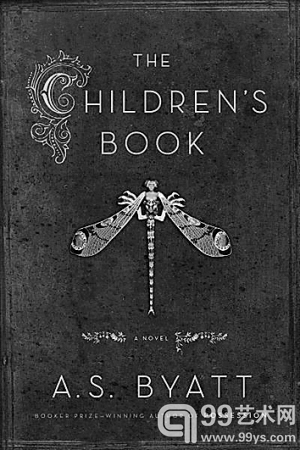
《儿童读本》
[英]A. S. 拜亚特著
Alfred A. Knoff
2009年出版
我读布克奖小说《迷恋:一则罗曼史》(Possession——A Romance)时,即疑心作者拜亚特(A. S. Byatt)大概是在童话故事书里泡大的。后来看董桥先生提安德鲁·朗(Andrew Lang)的色系童书,下意识就跟拜亚特挂钩,果不其然,她在2004年为《卫报》写文章《幸福至永远》(Happy ever after),探寻童话的源流与意义,一开首就点了朗的名。2009年,七旬老太又拿出一部近七百页的长篇《儿童读本》(The Children's Book),再度入围布克奖复选名单,虽输给了希拉里·曼特尔(Hilary Mantel)劲急的克伦威尔,我仍然对拜亚特的选题很有兴趣,一直等着新作问世。

A. S. 拜亚特像 李媛 绘
这本书里面自然涉及很多童话篇目,书本身的走势也充满了借喻,比如这个名字,这幅晦蓝的装帧,会让人想到格林兄弟;占篇幅最巨的“黄金年代”(The Golden Age)似乎呼应着儿童气质强烈的肯尼思·格雷厄姆(Kenneth Grahame)及其同名作品。故事发生的核心地点:肯特郡的托德福莱特(Todfright)门口淌着清流,铺着草场,背靠密林,浓荫拂地,小生态环境鲜活,仿佛自格雷厄姆的《杨柳风》(The Wind in the Willows)的洞天移植出来,虽然也许吉卜林乡居的影子才更有英伦气息;托德福莱特女主人,儿童作家奥丽芙·威尔伍德太太(Olive Wellwood)逐年倾心写一部故事“地下的汤姆”(Tom Underground),故事里的人物倏然投入另一重封闭世界,这场面与兔子洞里的爱丽丝、被龙卷风吹走的多萝西基本上是一致的,这一则在小说里后来被搬 上舞台,其空前盛况,直逼同期的小飞侠彼得·潘。
小说缘起伦敦城南肯辛顿博物馆,时间是1895年6月19日。馆长的儿子朱力安·凯恩(Julian Cain)及随母来访的汤姆·威尔伍德(Tom Wellwood)盯上一个日日蹲在馆里临画、休馆时又不见踪迹的男孩子。他们直捣黄龙,发现他居然真实地“遁入地下”,还不介意睡棺冢石床。苦出身而眼疾手快的少年菲利普·沃伦(Philip Warren),就此从穴居浮上陆面,受邀跟随威尔伍德母子到托德福莱特参加一年一度的仲夏舞会。莎翁的《仲夏夜之梦》(A Midsummer Night's Dream)及《暴风雨》(The Tempest)成了服装道具,提线木偶戏《灰姑娘》(Ashenputtel)、《沙人》(Der Sandmann)逢迎群童,亲朋满座,载歌载舞。格林兄弟、安徒生、吉卜林、巴里等童话名家也陆续在随后的重大场合担当谜面或背景,比如奥丽芙的大女儿多萝西去慕尼黑寻找生父时,木偶艺人安赛尔曼·施坦恩(Anselm Stern)给她表演的即是可以变形继而人格裂变的格林版“我的刺猬汉斯”(Hans Mein Igel);安徒生的《丑小鸭》经由奥丽芙的妹妹解读,演变为父母居然可能不知道孩子,孩子也居然可能识不得父母,拜亚特连用了两个“It's surprising”提起极度的惊愕,而这个故事的真人版,恰好在威尔伍德一家上演,是这个家庭明亮温和天气下的黑冰。可以说,拜亚特所谓的“真实童话”(real fairytales)及其无需解读也可传递的意思,在她的《儿童读本》里抽芽生花,无处不在。
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