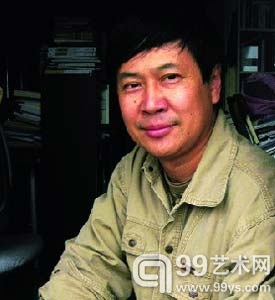
李公明 广州美术学院教授
焦虑背后的社会变迁
记者:近来,有媒体报道,湖南省委书记周强被一首由打工者翻唱的歌曲《春天里》感动至热泪盈眶。事实上,这首属于摇滚乐手汪峰的歌曲所感动的并非只有周强一人,而是无数中国网民。这很可能反映了当今社会的普遍焦虑,那就是过去我们一直相信:物质进步必然会带来幸福感的增加。但时至今天,这种愿景却渐行渐远。你怎么看?
李公明:打工者翻唱的《春天里》这首歌之所以这么热,当然反映了这个社会普遍的焦虑,这一点是肯定的。问题在于,这种焦虑背后所潜藏的社会层面乃至精神层面的问题究竟是什么。更深一层的问题在于,这些问题不是暂时的或局部的,比如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等方面的问题,不但是全方位的、长期存在的,而且随着社会贫富悬殊的拉大、物价的变化、个人年岁的增长等变化不断地向这些人提出新的难题、新的困惑。而面对这些问题,底层的民众基本上既缺乏预先的了解,也缺乏具体、有效的应对与博弈能力。我想,这种在困境中产生的无奈是更为根本的一种焦虑来源。
记者:从宏观上而言,整个社会呈现出这种集体焦虑,是否与过去几十年的社会变迁有关?
李公明:这当然是毫无疑问的。从前年开始,“改革开放30年”成为媒体不断炒作的一个热门议题,我当时就曾提出:“改革开放30年”本身这个命题成为一种现象,除了在命题下进行讨论外,对于这个命题的出现,我们应当也给予重要的反思。这30年的改革是不是铁板一块?其中大有利益分殊与重组,形成完全不同的利益格局。这些分殊与重组代表了不同的走向,对于形成我们今天的社会景观、核心问题究竟起到了怎么样的作用,亟须剖析。
记者:我看到也有学者提出这30年应当分为两段,一是1978年—1992年,一是1992年至今。在前一改革时段,物质和精神层面的扩展基本处于同步,尽管也有各个方面的问题,但大体上还是相匹配的。但1992年之后,伴随着不完全的市场化,甚至与权力勾兑的市场化,使得物质与精神的扩展在一定程度上陷入脱节的状态。
李公明:我同意你的判断,我想在上世纪80年代末之前,整个社会的精神环境基本上处在一种有理想主义的批判精神和有全面改革社会的诉求的状态。但是,知识分子的主流在80年代末的风波之后,几乎在同一时间迅速“醒悟”过来。突出的一个表现在于,他们对于“文革”和过去道路的反思中断了,他们开始关心自我利益以及自己所依附的这个体制的利益。更重要但是很隐秘的是,有些人清醒地意识到对于过去批判过的很多东西已经不能再做清算和反思了,他们开始竭力维护利益集团自身利益的巩固和延续。
记者:整个社会的不同主体都相应地做出了一些调整。比如将知识分子纳入到自己的利益共同体,而知识精英心态也普遍发生了变化。激进的理想主义者一旦碰触到了冰冷的现实,立马又会变成彻底的犬儒主义者。
李公明:我赞同你的分析,理想遭遇冰冷的现实之后,知识精英被迅速分化了,这一点非常明显。当然,这种分化的大背景是伴随着高校的迅猛扩张、科研经费的迅速攀升,在重视教育的名义下,国家把大学塑造成了一个非常衙门化、官僚化、体制化的一个机构。在这个机构的“高效”运作下,学术产品、学位产品也就源源不断地流出。而这,也就真正地伤害了知识分子的独立性、批判性。今天知识界的很多人在批评80年代,其中有部分人实际上已经在远离社会现实,或者说他们的人生价值、目标已经有所调整了。
编辑:李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