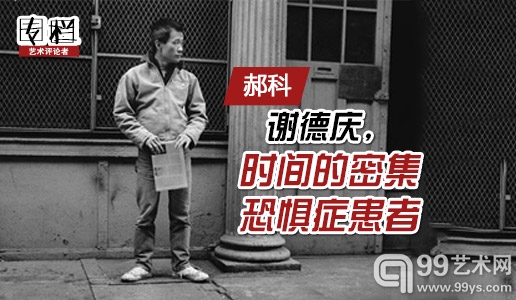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写字对我来说只是为了有个事情可做,它能够舒缓没有劳动时的罪恶感和任意闲逛时的无尽空虚。从起床睁眼后对着烈日当头的玻璃发呆,到子夜时分依然傻乎乎地坐在电脑前漫无目的的坚守,城市流离的倒影就像一群已经在冰箱中生活了一整年的鸡蛋,将每一寸流失掉的光阴都转换成阵阵刺鼻且无法形容的古怪味道。但我却抓不住它们,只有那些依然悬挂在蛋壳上的鸡屎、草芥和泥土混合而成的化石,在安静地提示着种种可能被遗忘的历史——“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的乡村生活景致,是我为它们杜撰出的美好出处,却充满了以理想主义为借口的脂粉香气;而它真实的产地很可能只是一座建立在垃圾场近旁的、流水线式的养鸡场,但当这种悲观主义的“真相”论调时刻都在以冷嘲的嘴脸出现在镜中的时候,却也会让对面的我感觉恶心无比。
北京,以温床般的丰富病毒滋养着我体内日益泛滥的大都市依赖症,而对于乡村生活的向往又总会悬停在童年的城市记忆之中:以煤渣和烟雾作为底色的阴沉冬天过后,转眼又是被卡车轮毂碾压过的炎热夏天。在进入正题之前的东拉西扯过后,我也突然想到:现在正身处同一城市我和一些朋友们,却并没有真正谈论过各自对于北京的感觉或印象,只是在终日的忙碌间遵从着生活划定的既定路线,顺时针地向前,又向前的如此寡淡如水。也正因为如此,每次在见到倒行者的逆时针旋转时才会感受到一些或大或小的激动心情。
在谢德庆的行为作品“打卡”(1980-1981)中,城市似乎被隔离在时间之外,密集的影像记录让每一寸被剪断的光阴均散发出强烈且刺鼻的味道:已经如水般流失掉的过去就是时间反馈给我们的、最为冰冷的痕迹之一,它曾经单调的节奏足以让你忘记它从不曾停歇过的狂奔脚步;然而当时间的切片以铺天盖地的赤裸姿态平躺进此刻的凝视中时,每日细微的形象变奏却又将光阴的真相铺陈的如此触目惊心,以至于除了秒针的滴答声响之外,其它任何的存在都会变成一种对于虚空的假设或呓语。
那么在切开时间密实紧致的肌肤之后,城市的躯干将藏身何处?早年忐忑的身份游移(非法移民)为谢德庆的城市体验掺入了更多混合着爱恨恐惧的复杂情感,在随时都可能都会被抓的不确定状态中,时间密不透风的嘴脸已吞没了城市空间的虚影,艺术家内心冰冷的失意也以毫无希望的闲逛姿态出现在了城市的阴影中,并在极端的封闭状态中转变成一种对于自我的严苛拷问。
正如我们在名为“笼子”(1978—1979)的作品中看到那个无所事事到极尽透明的谢德庆一样。同样是生活在时间钟摆的缝隙间,不交谈、不阅读、不书写、不收听广播、不看电视等等,日常用来打发时间的诸多手段在重复的一呼一吸间均化为了乌有,而关于城市的种种向往或失望对于那株休眠在铁笼中的灵魂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呢?与他早期的一些作品不同——如他曾把自己浸入粪桶,实验自己在其中能够闭气多久;在名为“呕吐”的作中,他则拼命地吃东西直到吃不下为止,再把所有东西都呕吐出来,盛在一个玻璃碗里等——那种极具暴力色彩的身体对抗却始终没有触及到残酷的真相,直到时间以最为沉重的密度重新压进城市的痛感中枢里时,不可逆的缓性暴力才成为在艺术家体内不断生长的恶之花——它具有不可预测的邪恶能量,可以让人在“平静”中麻木到坚强,也可以在无法抑制的疯长中将内心爆裂成一吨再也无法重新拼合完整的残片——在这些作品中,谢德庆的身体就像一根被拉伸到极限的韧带,以令人犯困的安静姿态承载着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绝对公平的、时间之刀的雕琢,而在雕刻时飘洒下的粉末正是那些被一笔带过的数字,如写下“从1978年到1979年”这几个字等。
而在名为“户外”(1981—1982)的作品中,赤裸坚硬的时间计数被变换中的城市形象披上了更加多变的外衣。将城市看做一片荒蛮的沙地,无论雨雪风霜只能将身体敞开给头顶的天空,而脚下的柏油路或身边的高楼大厦则更像是一片片虚幻的海市蜃楼,在彰显着舒适诱惑的种种媚态的同时,又让难耐的时间的成为了一声声抵抗着城市结构的沉重鼓击。从最早带有恐惧感的自闭体验到完全开放后的若即若离,城市作为一个在符号意义上充满生机的生存之地,在时间的横线上却始终保留着死一般寂静的底色。
在名为“绳子”(1983-1984)的作品中,谢德庆内心的寂静或嘶鸣也因另一个个体——美国女艺术家LINDA ——的出现,而被拓展为另一种沾染着时间污渍的内心较量。用一根8英尺长的绳子将两个人拴在一起生活一整年的时间,期间有了更多可以被作为花边新闻来谈论的细节,不可避免的冲突、抹掉“尊严”的歇斯底里等等,似乎让时间和城市的印记又回归到人们喜闻乐见的剧情之中。但关于人性的谈论又始终离不开那挥之不去的恶念,而这种生生不息的恶念是因为人总是要死的潜在紧迫,在逼使着我们要时刻彰显着自己的存在吗?当各自相同的时间被一条可见的绳子拴在一起的时候,对于自我时间被他者占有的本能厌恶,会导致的唯一结果可能就是对于自我存在感的莫名争夺。不论是谢德庆还是LINDA,毫无间隙的彼此侵扰都将本就无际的时间堤岸推向了更远的远方,依然是在城市体系的荫庇下——有媒体采访、有舒适的浴室和卫生间灯等——的自我溺亡,在剥离开声名的负累和外界的关注之后,反馈给个体的却是对于密集时间的深深恐惧,这恐惧像一道道被数字的表征所割开的细小伤口,可以被文字和影像记忆,却永远也无法复原。
但当这种时间的恐惧症成为一种固执的个人风格之后,无可避免的思维习惯也会将创作引向一种看似“顺畅”的延续之中,如谢德庆此后创作的“不做艺术”(1985-1986)和“不发表”(1986-1999)等作品,尽管依然是在对于时间的分解中抵抗着生命的阶段性进程,却也渐渐透露出了江郎才尽的固执坚持,或许这也是我们此后再未见到谢德庆新作品的原因吧——患上时间恐惧症的倒行逆施者,在陈列了时间的每一寸细节之后却也再无时间可言了。
声明:本文为99艺术网特约独家专栏文章,未经协议授权,请勿转载使用。如需转载请来信xinwen@99ys.com,或拨打合作电话:010-51374001-807 联系。
编辑:文凌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