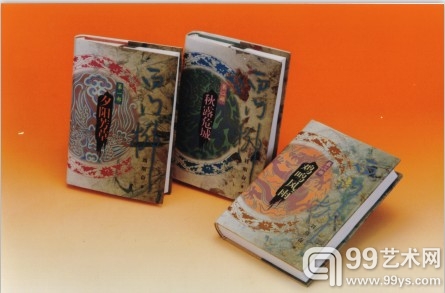
白门柳二版
记者:80年代以来,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广东经济的迅猛发展在全国有目共睹,与此同时,发展中的广东该展现出什么样的文化景观也成为很多人谈论的话题。在这期间,您是主管全省的文学艺术工作的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有压力吗?您上任不久就点了一把火,1994年您的《批评标准和广东文学》首先在广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到1992年10月,《朝阳文化、盛世传统和巨人精神》在《南方日报》全文发表后,随即于《人民日报》转载。您从批评标准的问题展开,就现代化建设背景下的文化发展,如何调整自身的价值趋向和行动模式等等进行了深入论述。您的观点在当时引起全国文艺界的关注,不过,时至今日广东文化仍然受到一些人的质疑,这似乎已经是一种观念。您认为这到底是什么原因?
刘斯奋:作为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的地区,广东的经济发展引起了全国的高度关注,在这个快速发展起来的地方产生了什么新的文化现象,当然也成了备受关注的一个话题。当时还有过广东将会变成文化沙漠的危言。其时,作为分管全省的文学艺术工作的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我必须和同事们一起面对这种质疑,做出自己的判断,并预测其发展,以此建立我们的信心和确定相应的对策。事实上,当时我们就认为:广东出现的文化滑坡,是社会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一种“阵痛”过程。广东先行一步,所以先遇上了。文艺界不能因此丧失信心,自乱阵脚,而应知难而进,勇于创新,积极探索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生存方式和发展方式。事实证明,这种判断和主张是符合实际的。不只是文艺的批评标准,而且整个文艺界的状况;也不只是广东,而且在全国,与十多年前相比,已经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
当然,从更深层次来说,持什么样的观念来评判文化的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一元的、静止的观念在不少国人心目中还是根深蒂固,总习惯于用历史的、过时的标准来排斥已经极大地变化发展了的文化现实。这对于我国当代文化的建设其实是不利的。事实上,文化的生成,存在和发展变化,是受到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制约的。时代在推移,评判文化也要相应有一个变化的,发展的观点。另一方面,就空间而言,不同地域的存在,不同生成环境的存在,决定了文化的格局也不可能是纯粹的,划一的。因此评判文化还要相应有一个多元的,包容的观点。当代中国对于世界各种不同文化的个性与价值抱有充分的认识与尊重,在国际交往中倡导和谐和多元的理念,从而获得越来越广泛的好评。这使我受到启发:对待世界各国不同的文化,固然应当用发展和多元的观念作为评判的出发点;同样,对待我们自身文化的内部结构时,恐怕也需要这样。如果这样来看问题,那么对于广东和其他地域文化,恐怕就会有完全不同的观感和认识。
记者:您认为广东文化有何主要的特点?同时它又有何比较明显的缺陷?
刘斯奋:我觉得广东文化的特点主要体现在这几个方面:一是“杂交型”。大致说来,广东文化的形成是一个杂交的过程,主要有三个源头:一是古代百越族,即当地土着居民创造的原生态文化;第二个源头是中原文化的决定性影响,由历史上几次大规模移民形成,这是今天所说的广东文化的主体部分;第三个源头就是来自西洋,南洋,甚至包括着美洲,非洲等地的异域文化的影响。
二是个性鲜明。这是因为其土着文化非常独特,同时又大量吸收,融合了异域文化,所以看上去和中原正统文化不太相同,就算其中受中原文化决定的那个部分,也发生了较大的流变,所以说岭南文化个性鲜明,共性中也包含了个性。
三是就是因为广东是杂交生成的,所以创造力盛,包容力大,生命力强,适应性广。
至于说到缺陷,那就是广东长期以来作为对外贸易的口岸,其文化也往往呈现出来的口岸的特点。这在近代尤其明显。许多第一都是在岭南的土地上开花,却在别的地方结果。比如在国内,广东人最早“发明”了电影,但上海却是第一个建立电影厂并成为电影业中心的。当年的陈白沙在京城成名,梁启超也在离开广东之后才获得最大的成就。同样,讲到文化的创造力,广东文化往往表现为感觉敏锐,反应迅速,用于尝试,开风气的爆发力好,但往往耐力不足,定力和持久力不够,这使得发明创造难以做到根深叶茂。历史上的岭南,文化巨子虽不时出现,却从来没有出现群星璀璨的局面。往往是某个大人物突兀而起,却看不到一个深厚的文化渊源和长盛不衰的流派。大概就是与这个特点有关。
记者:1994年4月广东省作家协会召开“广东文学创作座谈会”,您提出在工业社会的进程中,人民群众不需要对苦难的渲染和描述,不需要发泄、哀叹、颓废的消极诉求,而是要用快乐、向上的基调,激励他们积极面对现实生活的矛盾,实现人生的理想。为此文艺工作者应该面对群众这种生活的要求。近来,在深圳举办的关于打工文学的座谈会上,很多打工文学作家以及研究者都提到了您对打工文学发展的支持。这给大家的感觉好像是体现了您思考上的一种转变,您也这么认为吗?您认为广东当代文学对社会底层话语权的重视和关注意义何在?您对这些表现社会底层呼声的文学的作者们有什么期待?
刘斯奋:坦白讲,我比较喜欢那些关注当下、关注时代的文学作品,而关注当下、关注时代的作品当然也包括底层写作。在西方的文学史上,现实主义取得了相当高的成就,涌现了很多优秀的作家与作品,这些作家作品不少都与底层写作有关,他们写出了在时代变迁社会转型过程中底层生活的人生百态,写得很大气,很有档次。因此,在当下中国社会巨大的转型过程中,打工文学作家们若能够从底层的命运转变来反映出这个时代变革,不仅仅是弱势群体的呼声,而是站在更高、更有历史感的角度下去记录、去表现、去思考这个大时代,是有可能出大作品的。因此,文学界、批评界都应该给予他们更多的关注和支持。这是从艺术创作的角度来看。同时,从构建和谐社会的角度来看,社会各界关注底层呼声当然是很重要的。
记者:2000年,由于提倡干部的年轻化,您主动提出自己任副部长8年了,应该轮岗。2003年,您从宣传部的领导岗位上完全退下来,任省文联主席和画院院长的时候,说自己是“去留无碍”,又说从今往后是“挥霍余生”。在大家都以为您会来一个转身重拾小说创作之笔的时候,您举起的却是画笔。您为什么不写了?
刘斯奋:人生毕竟有限,精力更加有限。我写《白门柳》从37岁写到53岁,可以说将人生最好的时光都奉献给这个三部曲了,写得很认真、很痛快、也真的很累,今后恐怕很难再有这样的精力来投入小说创作了。就我自己的标准而言,既然是创作,就应该能有突破,如果做不到,即使在原来的水平上踏步,也已经没有意思。那么又何必浪费自己的精力和读者的时间呢。演艺界的人不是喜欢说,在最灿烂的时候退出就成为永恒吗?我也认为这样,免得江郎才尽时才离开,大家都没有意思。(笑)
记者:您进入书画界后,引人注意的动作也不少啊。您举办了的多次书画展,不仅深受书画界的好评,还深得读者和观众的喜爱。能谈谈您在书画方面的想法吗?
刘斯奋:实际上就我个人来说,童年时期我最初的梦想是当个画家,后来还差点成为美院的学生。但由于种种原因走上学文这条路,可是少年这个梦想却始终没有淡忘,在《白门柳》之后,我自然而然兴趣又转了回来,再拿起画笔。我把自己定位为文化人,我对文人画很有兴趣。所谓文人画,以今天的理解,乃是把文人之情怀,以概略和简约的形象于以演绎;由此反过来,又把这种写意式的造型艺术推向一种更高的文化层次。我现在探索着一个主题,就是用文人画的手法描写现代生活现代人物。
记者:嗯,关于这一点,旅美艺术家钟耕略就赞扬您的现代都市系列画作“已然跨入了一个现代艺术的领域”。又表示“刘斯奋描写的是21世纪之都市女士风情,他那敏感的都市掠影,留下了现代人生活的特有片断,比如打手机、拖着行李车、等候巴士、溜狗、背着时髦挂包等,都是中国水墨艺术尚未广泛涉足的领域。
如何让现代生活走进中国水墨艺术,正是中国画求新求变的一个重要环节。刘斯奋不斤斤于严谨的传统中国画的笔墨线条,使他能自由随意地绘出他对现代都市生活的感受。故此他的现代人物作品虽稍欠传统笔墨的历练,但却换来了活生生的意象,那既现实又写意的人物形象与观者产生共鸣,从而映照出作者热爱生活的真意。
刘君不拘泥于传统笔墨的画风,或不见容于科班出身之规矩尺度,然而它的立意在于以简朴纯真之笔法,捕捉住现代都市人的灵魂。正如西方的波普艺术一样,以现代生活之平庸题材入画,重情而不重法,让艺术回归大众。然而刘君的画与波普不同者,乃是于通俗之中,保留了一种文人的雅逸趣味。那疏宕而温婉的书卷气,以及洞悉世俗文化的心象。
正因为刘斯奋的现代人物作品打破了传统笔墨的桎梏,在意念与境界上开拓了一片新天地。所以从他的作品中,可以找到更多与现代艺术相关的元素。譬如在《沙发》一画中,其粗犷率意的线条,以及构图运笔的感觉,几与野兽派的马谛斯(Matisse)作品有共通的韵味。当代美国油画名家阿里卡(Arikha)的宣纸毛笔素描作品,以焦墨皴擦捕捉人物形象见称。虽然与刘君苍润朴拙之线条有别,但若然将两者作品安排在同一展览里展出,则会有相得益彰的协调感。可见大家从不同角度跨进了一个东西文化的现代交汇点。
中国画的现代化问题,困扰了我们一个世纪。如何寻求突破,如何建立一个有时代气息的现代体系,尚有待我们不断实践和努力。可以肯定的一点,就是必须开拓我们的视野,西方艺术的借鉴不可或缺;而中国文学的素养,以及文化层次上的升华,更有助于我们的创作达至一个深厚高超的艺术境界。而刘斯奋的绘画艺术正是朝着这个方向所折射出的一道奇光。”钟耕略对您的评价不可谓不高了。
刘斯奋:那就承蒙他的抬爱了。(笑)
记者:您说自己:“在写作界的眼里,我是从政的(或者还是画画的);在绘画界的眼里,我也是从政的(或者还是写作的);而在从政的同事当中,我又是写作和画画的。这情形,十足就像老故事当中那只似丝丝鸟非鸟、是兽非兽的蝙蝠。”我觉得这话透出了您对自己的独特的自豪。同时拥有这些不太一样的身份,这些身份会不会产生一些矛盾?在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您会不会很自然就产生各种跨界的视点和思考?
刘斯奋:古人云“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也就是说各种素养其实是相通的,可以相辅相成,关键是如何将人生的经历内化为自我的素养。就我的个人体会而言,“入仕”的确影响了艺术创作的时间和精力,但对拓宽自己的眼界,胸襟,以及提高我协调人际关系的能力无疑会有很大的帮助。正样的历练,会在写文章,画画时的视野、格局和内涵上呈现出来。
同时,也正因为不对自己身份作明确的界定,让我的兴趣和潜能的发挥有了更多选择自由。这对于保持创造的个性和激情来说,是很有好处的。
记者:从官场到民间,从作家到画家,是基于对自己什么样的认识,什么样的基点让您在每次进出转身时总能如此淡定?
刘斯奋:这可能是出于一种典型的岭南文化人的心态,就是喜欢自由自在,不拘一格,不定一尊,不守一隅。不刻意拒绝名利,但也不受名缰利锁的束缚,只管在人生旅途上率真随意地行走。屈指算来,我可算已经一一圆了少年时的梦,就连从来未曾做过的梦也变成现实塞给了我。还想怎么样呢?命运已经对我很好了。人生到了这份上,应该知足了,真的。
记者:今后,您这位快乐的“似鸟非鸟、是兽非兽的蝙蝠”还有什么计划吗?
刘斯奋:主要用还是画画写字来“挥霍馀生”吧。而且刚刚也说过了,我在探索着一个主题,就是用传统中国文人画的手法描写现代生活现代人物。我正兴趣盎然,劲头十足呢。(大笑)
【编辑:谈玉梅】
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