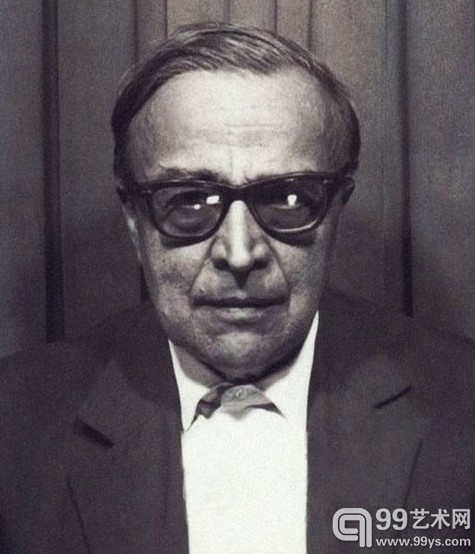
有人热衷于讨论当代艺术的发展,也有人在思考它的终结。
“发展”与“终结”,还有比这更为尖锐对立的概念吗?然而,我们却在几乎所有的领域中看到“终结”在发展,“发展”则依赖于终结。可以说,有哪一种发展不被它的敌人咒为终结呢?又有哪一种发展不拿终结这个罪名去诅咒更急速的发展呢?
从这一事实中可以得出两个结论:“发展”与“终结”已经被全世界的一切关系公认为一种关系;
现在是认真思考存在于思想与审美领域中的各种发展论、终结论并试图说明我们的观点、目的、意图并且以此来审辨各种当代艺术的神话的时候了。
在谈论发展或者终结之前,理应先谈谈“开始”。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在我的词典里,“开始”开始与一个诗人链接在一起。胡风于“一九四九、十一月十一日夜十时半”写成长诗《时间开始了》,以幻觉和崇高体讴歌“开始”,竟然鬼使神差地引用了诗人但丁在地狱门上写下的金言:“到这里来的,/一切希望都要放弃!”当然,他是为了否定与反衬,他是诗人中最热情洋溢的辉格党人。诗人豪迈地询问,那些以“挂在电线柱子上的头颅”、“倒毙在暗牢里的尸体”、“埋进土里的半截身子”为代表的过去,在这胜利时刻曾在脑子里“闪现过了吗?”不幸的是,他诗意地宣布已经终结的过去实际上才刚刚开始,终结论被历史无情地还原为开始论;或者说,20世纪浪漫主义的开始论被无情地还原为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的开始论。
画家李斌敏锐地把握了胡风的终极论与开始论,创作了油画《时间开始了》,他让胡风站在金水桥上放飞鸽子,宣布“时间开始了”。有意思的是,他让身穿人民装的鲁迅站在胡风旁边。鲁迅不是一辈子荷?彷徨于过去与现在、终结与开始之间的吗?更有意思的是,胡风所讴歌的巨人在金水桥后面俯瞰着这对文学师徒,他对“时间开始了”以后的鲁迅不是有过坦诚得惊人的说法吗——那意思就是说让他终结过去,或者终结他自己,二者选一。就这样,画家以绘画颠覆了诗歌,以终结论颠覆了开始论。
其实,在科耶夫笔下的黑格尔的“开始论”才具有历史性质的真正含义。“对于黑格尔而言,历史要等到第一次为承认而开始的战斗之后,才开始,而这种战斗如果不是真的冒着死的危险,也就不算。”(科耶夫《黑格尔导论》)应该认真思考黑格尔的意思,尽管在这里是由科耶夫解读的。“第一次为承认而开始的战斗”,有动人的崇高感,但是首先要明白“承认”这个概念在法哲学、政治哲学中的重要性。
从“终结”、“发展”到“开始”,再到“承认”,看来我们只能像在林中空地捡到一个七彩大宝盒子的小孩一样,迫不急待地打开里面的一个又一个盒子。
据研究者指出,“承认”一词首先出现在费希特的《自然法权基础》之中,黑格尔借用了这一概念,并推演出主奴生死斗争意义上的人的自我意识的发展路线。对于黑格尔,承认以及获得承认是人的一种欲望。因此,“承认”是人的“开始”的第一步,人的历史开始于为获得承认的战斗,也就是说,开始于为了确认欲望而开始的战斗。
但是,在神学和政治哲学中,“承认”又有着远比抽象的人的“开始论”更为具体和严重的意义。列维纳斯对“原罪”的阐释是:原罪就是承认我们应该肩负世界不幸的重负并且把与恶的斗争作为我们的人生方向;只要世界上存在苦难,我们都应该感到自己在某种程度上负有责任。显然,“承认”在神学中具有奠基性的意义和重要性。
在“二战”以后的政治哲学中,“承认”也成为政治伦理的基石。
雅斯贝尔斯关于“承认罪责是迈向政治自由和成熟的第一步”的思想在历史学家的言述中获得更明晰、也更沉重的表达。著名历史学家托尼·朱特指出,对历史上国家罪恶的承认和忏悔,是进入当代公共生活无法逃避的途径,“否认或者漠视‘浩劫’——也就是‘大屠杀’,则被视为文明的公共话语中无法忍受的行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认为,“对‘大屠杀’的承认,是我们进入当代欧洲的门票”(《战后欧洲史》)。事实上,战后欧洲对“大屠杀”的承认问题,一直延续到21世纪来临之际。
与学者相比,艺术家的“承认”风暴来得更猛烈、更感性,同样值得我们关注。德国艺术家约瑟夫·波伊斯不遗余力地公开宣传他的“扩展的艺术概念”,他在这种概念中掩藏着一种深刻、内在的指向:一名前帝国军人、现在的艺术家对有关大屠杀的记忆的承认与召唤。
一位从未参与过任何与大屠杀相关的军事行为的前军人对于战争屠杀罪责的承认,这是一个非常敏感和复杂的问题。吉恩·雷指出过去已有评论家洞察到在波依斯的作品中有一种隐秘的叙述指向和暗示着大屠杀,但是分析得并不具体,也缺少对作品整体的系统解读。在这里我们不妨反身追问的是,我们的艺术评论家有多少人会有这种兴趣与洞察力呢?
吉恩·雷认为关键在于不应该依赖艺术家个人的自我解释,而必须把他的作品放置于那段罪恶的创伤性的公共历史中去,他对种族灭绝的态度、作品中的那种使我们震撼、惊诧、感染的力量以及崇高的美学效果才会浮现出来。但是,把人物放置于罪恶的公共历史之中究竟是否合适?波依斯没有参与大屠杀,也没有因为这种历史而获得过好处,为什么要把这种联系添加到他身上?作者的解释是,“大屠杀是历史强加在他身上的……他跟他那一代人中的每个德国退役军人一样,无法逃避与大屠杀的关系……他保持着公共历史给他标出的位置:一名纳粹帝国军队的退役军人。无论他本人的意图如何,他的艺术创作都必然会跟那一时代的大规模创伤性事件联系起来。”
其实,这就是历史与人的最内在、也是最真实的联系,没有人、尤其是那些曾在历史中穿着各种制服的人能够彻底逃脱这种联系。关于战后普通德国人对于那段历史与个人的关系的认识有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那一代人并没有正视、清算国家的邪恶与罪行,而吉恩·雷则认为“清算大屠杀并哀悼其死难者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它将历经数代人,到达不同的层面”。
那么,波伊斯的艺术创作作为一种承认与记忆是完全可能的。其实,他在1957年、1958年参加奥斯维辛屠杀中心纪念馆纪念性艺术大赛就已经说明了这种联系的存在。以此为出发点,我们看到他以后不断地以迂回的、视觉隐喻的方式深入那片哀悼与纪念之地。“波伊斯唤起和承认大屠杀的策略是一种迂回战术。他最强有力的作品也只是通过形式和材料的相似以及寓言来产生效果,而不是直接地呈现或面对。”于是,毛毡、油脂、温度计等等都成了强有力的象征物,作者认为,“波依斯作品的伟大之处在于,它有力并同时表现了过去与将来。走出罪恶、伤害的过往之路,正是通向赎罪的未来之路”。
所谓的过去与未来,不正是终结论和发展论各自的视域吗?在这中间存在的“开始”与“承认”,是连结两者的核心途径,关键是是否愿意踏上这条途径。
跨过了“开始”与“承认”,让我们尽快接近科耶夫的历史终结论吧。
编辑:江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