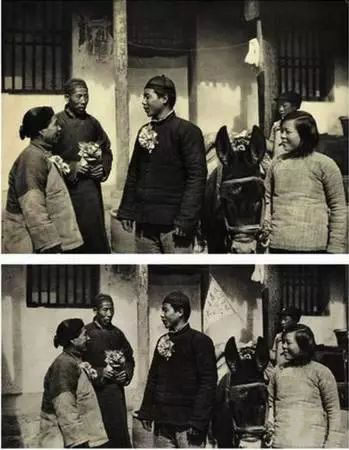
于:从开始的《对话》到《AK47》系列,很多理论家把你的创作归到“政治波普”或“玩世现实主义”。你对“政治波普”这个概念界定怎样看? 你怎样为自己的作品定位?
张:我不是波普艺术家,这是别人强加给我的。我认为评价一个艺术家,不仅要看他近几年的作品,更要看他二十年、三十年甚至一直到死的创作,因为只有这样你才知道他是什么风格的。至于艺术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我认为每个人都活在这个意识形态之中,没有人能够超脱。正像你前面说的,我所关注的“暴力”,是软性和精神的外力影响,它是更深刻的一种力量,而我们对抗或者挽回这种“暴力”所造成的影响,表现在不同方面,有的人把注意力转移到赚钱上,而我把注意力放在艺术表现上。
于:从《AK47》系列到你的新作《口号》,这样的批判是不是更直接了?
张:我认为是这样。艺术作品与我们的生活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是一体性的、不可分的,在这个语境之中,艺术是生活的反照。《口号》系列运用了与《AK47》系列一样的形式和手法,用标语、口号代替了原来的武器名称。
于:你的作品在现实针对性上显得很突出,而且作为这些作品的创作者,你对于自己作品的阐释也反映了你平时的思考。文艺理论上有个一直在争论的老话题,就是关于艺术家和艺术作品的关系,你怎样看?
张:每个艺术家的创作都是有动力的。但是我发现越来越多的艺术家,他自己都不知道他创作的动力在哪里。我们过去的理论认为艺术家可以不解释自己的作品,那是早期现代主义时期的观念;但当代艺术家,必须能说明自己作品的创作初衷,否则他就不是一个合格的艺术家——你可以做的不好,但是你必须要知道你在做什么。当一个艺术家不能解释自己作品的时候,我认为他的创作动机是值得怀疑的。这样的尴尬现象也呈现在我们今天大大小小的艺术展览中,艺术家与艺术家之间、评论家与艺术家之间,互相看不懂,也不敢说。
于:的确有一些艺术家,他自己的创作目的本身就是模糊的,他等待别人阐释自己的作品,他们像浮萍一样在水面上漂浮,等待着理论家用某一种“观念”去“认领”。
张:尤其在杜尚以后,这样的影响越来越大。我认为现代的中国艺术,很重要的是要“去观念化”,当很多作品的“观念”外衣被去掉之后,他的动机就暴露了,或者原来他根本就没有动机。还有更滥的一种作品,如果你把它的市场价值去掉以后,它就是空洞和没有价值的。所谓“人人都是艺术家”,都可以创作作品,这样的观念在杜尚的时代是可以的。但面对现在这样的口号我们应该去反对它,不是人人都可以做作品,或者做所谓的“现成品”艺术,这是很令艺术蒙羞的事情。观念加上市场的影响,对于当代艺术创作的影像是消极的。如果除去这两层外衣,一件作品仍然是朴素的、感人的,这才是真正的好作品。当年的罗中立、陈丹青的作品,就是感人的、真诚的,有人看了他们的画甚至流泪了,现在我们看不到这样的作品,这样的作品越来越少。只靠“观念”是不能感动人的。
于:是这样,尤其当“观念”泛滥成灾,甚至形成某种模式的时候。就像你说的,去观念化,去玄虚化,让艺术能被看懂,确实是更重要的事情。
张:艺术是被要求能让人看懂的,否则它的真诚性和有效性都值得我们质疑。至少在八十年代,多数画家的展览是能让人看懂,尤其是在画家圈子里,当你画了一幅好画,会有人跟你说“这件作品画的真棒”;但现在不会有人这样说,因为看不懂了。包括现在的电影、音乐、小说,都有这样的可怕趋向,虚假的观念在泛滥,这的确是当代艺术的现状,我相信终有一天这样的虚假和迷惑人的东西会被人唾弃,哪怕技术差一点但初衷是真诚的作品,会被人们肯定和铭记。
2008年8月
编辑:江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