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穿越达达主义百年的瑞士艺术之旅
0条评论
2016-04-05 11:35:07 来源:艺术与设计

“达达的开始是重新发现活生生的体验及其可能的乐趣——它的结束时对所有观点的颠覆,它创造了一个崭新的宇宙。”从达达主义起源地伏尔泰酒馆,到保罗·克利艺术中心与伯尔尼艺术博物馆的《中国私语》大展,再到疯狂机械的让·丁格利艺术馆,一场穿越百年古今的旅行与对话。
谁能治疗理性的疯狂?
清晨六点多钟,蓝色有轨电车弥散出黄色灯光,叮叮当当在苏黎世歌剧院广场前转弯。它低头耸肩,似乎正费力穿越一场风雪——然而,费力只是旁观者的一种假想,实际上,它,以及这座城市中的一切,都像瑞士制造的钟表一样,日复一日精准运行,毫不费力地在时间中将笛卡尔式的理性主义推送得更远。车窗中那些神情严肃赶往未来的人类剪影,既是理性主义的造物,亦是快递相应自负的齿轮、弹簧与传送杆,早年的超现实主义者、晚年的存在主义者阿尔贝托·贾科梅蒂所创造的那些瘦削而向前倾斜(屈服于线性时间与地心引力)的塑像,已经成为他们最好的注解,其中相当一部分,就被收藏在一公里之内的苏黎世艺术博物馆。
隔开沉睡的艺术博物馆与车灯穿梭的利马河岸的一片古城,此刻静悄悄地躺在山坡上,至少四个小时以后,游客才会大批涌入——它属于消费和娱乐,合法的红灯区也蜷缩在那里,时髦的店铺橱窗提示着它从未滞留于启蒙时代之前。我踩着新雪湿滑的石子路面,走过格罗斯大教堂前的小广场。消瘦但并不倾斜的双塔代表上帝注视一切,包括一步一顿走向伏尔泰酒馆(Cabaret Voltaire)的我,以及一百年前那些醉醺醺的诗人、艺术家和野心勃勃的革命者的影子。

达达主义诞生地伏尔泰酒馆
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并非瑞士国民,而是被另一种人类理性的产物——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炮弹驱逐至此,中立的瑞士吸引并容留了他们,一如德法双籍的诗人及艺术家汉斯/让·阿尔普所说:“出于对1914年世界战争无谓杀戮的厌恶,我们在苏黎世献身于艺术。当枪声在远方发出持续而低沉的隆隆声时,我们竭尽全力唱歌、绘画、拼图、写诗。我们在寻求一种基于基本原则的艺术来治疗时代的疯狂,寻找一种可以在天堂和地狱之间恢复平衡的事物的新秩序。”
虽然并非所有苏黎世的流亡者都像阿尔普一样积极乐观,认为可以寻找到一种新秩序,甚至艺术可以重新被发明,成为混乱多变的二十世纪的新宗教,但艺术家们的确因为厌恶战争而正在发明一种全新的运动。1916年2月5日,德国诗人及理论家雨果·巴尔(Hugo Ball)和他的女友艾米·亨宁斯(Emmy Hennings),以慕尼黑和柏林的酒馆为原型,在苏黎世老城中被称作“下村”的尼德道尔夫区域(Niederdorf Quarter)的镜子胡同一号(Spiegelgasse 1),开出一家与法国启蒙运动旗手伏尔泰同名的酒馆。

伏尔泰酒馆内的正厅墙饰
酒馆内设一个小舞台,一架钢琴,以及供约五十人就坐的桌椅。每当夜幕降临,这里便轮番上演街头歌谣、“黑人舞蹈”、诗歌朗诵等各式各样体现“现代情感”(人们在享受欢愉的同时也感到灾难迫在眉睫,生活支离破碎,失去了传统秩序的统一性与连续性)的节目,观演之间几乎没有任何空隙,观者经常对演者报之以嘲弄,演者则以噪音相对抗。艺术家们声称自己部分地重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引发的心灵动荡,释放出连他们自己都觉得心神不宁的力量。
经常出没于伏尔泰酒馆的诗人和艺术家,除了汉斯/让·阿尔普——他在此展览依据“机会定律”(类似于借助《易经》打卦,旨在发现混乱无序的自然模式与艺术的内在模式之间的交互作用)拼贴而成的极简作品——以及他的女友,瑞士纺织设计师兼舞蹈家索菲亚·陶贝尔(Sophie Taeuber),她的头像将在数十年后被印制在五十瑞士法郎的纸币上。

五十瑞士法郎的纸币上的索菲亚·陶贝尔
创造出这一艺术流派的“作品”销量纪录,还包括罗马尼亚诗人特里斯坦·查拉(TristanTzara)、罗马尼亚艺术家马塞尔·杨科(Marcel Janco)、德国诗人理查德·许尔森贝克(Richard Huelsenbeck)、德国作家瓦尔特·塞纳(Walter Serner)、德国实验派电影制片人汉斯·李希特(Hans Richter)、瑞典实验派电影制片人维金·埃格林(Viking Eggeling)等。
当时,他们最希望做的事,就是挑衅并颠覆以往的艺术观念,因为他们对人类的理性提出了质疑,比如汉斯/让·阿尔普,他在创作中转而寻求人类理性之外的“机遇”,而且,在他们眼中,传统艺术已经被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严重侵蚀,油画和雕塑成为了闺房之中无聊的摆设,所以他们选用廉价的纸张或是随处可见的现成品,组合出新的结构,专注于表达观念,丝毫也不考虑作品的销路问题。在马塞尔·杨科的一幅原作业已遗失的绘画《伏尔泰酒馆》中,我们可以看到舞台上方悬挂着非洲面具。

马塞尔·杨科《伏尔泰酒馆》
对于传统欧洲艺术家来说,那是一个他者的符号,伏尔泰酒馆的艺术家则平等看待来自不同地域的文化现象,并借此表达着对于现代战争的根源——民族主义——的厌恶。他们多半深深认同于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当然,酒馆中的观众也包括少数共产主义者,比如从俄国流亡而来的列宁,从酒馆门口扔块石头,就能打到他租住在同一条街上的那幢公寓,镜子胡同十四号),认同于艺术首先要解决普遍的人性问题。正是基于这样的共识与默契,酒馆开业两个月之后,“达达”这一自我命名诞生了。
当时,诗人和艺术家们决定出版一份刊物。依据雨果·巴尔的日记《逃离那个时代》的叙述,是他本人提出了“达达”的概念,创造出这一凸显国际流动性的文化世界语:“达达”在罗马尼亚语中意谓“是的,是的”,在法语中则为“木马”和“竹马”,对德国人来说,它又指向愚蠢的天真、生育的快乐以及对婴儿车的全神贯注的痴迷……不过,德国达达的代表人物理查德·许尔森贝克却声称,是他和巴尔一起快速翻阅词典的时候,发现了这个词,“达达”强调的是破裂与新生的观念:这是孩童发出的第一个声音,表达了一种原始感,它从零开始,是艺术的新生。
除此之外,关于“达达”的命名,还有形形色色的其他阐释,不一而足,无穷无尽,一如“达达”本身,自相矛盾地代表一切,又似乎什么都不是,只是将肯定和否定荒谬地混合在一起。仅我在苏黎世亲耳听到,便有强调彼此呼应的“跷跷板说”,以及源自同名品牌的“肥皂广告说”,等等。

达达主义肥皂起源说
早已为达达主义问世百年系列活动准备就绪的伏尔泰酒馆,在其内部被辟作纪念品商店的部分,悬挂着“达达”品牌的大幅沐浴用品广告,只不过,那不是1916年的原版,而是1966年的戏谑版,纪念达达运动发轫五十周年,套用《哈姆莱特》的著名独白,喊出两行口号:达达还是不达达,这是个问题。广告下面,整齐码放出货真价实的肥皂,复刻版,价格很不达达,但也许会创造出达达主义艺术衍生品的年度销量纪录。
爱因斯坦之后的《中国私语》
“每天下午,伯尔尼市民聚集在克拉姆巷的西端。三点差四分,即是钟楼向时间致敬的时刻。在高高的彩楼上,小丑跳舞,小公鸡鸣唱,而小狗熊呢,则是又吹笛又打鼓。他们机械的动作和声音,是完全依照各式齿轮的转动而同时合成的;当然也是时间的完美性质予人灵感,有以致之的。三点整,巨钟响三次,聚集的人群跟着钟声对表,然后回到斯派克巷中的办公室,回到马可巷上的店铺,回到阿勒河桥外的农场里去。”
美国理论物理学家艾伦·莱特曼的小说《爱因斯坦的梦》,如此记叙瑞士首都伯尔尼城中那座修建于1530年的钟楼。当我被怀揣钥匙的导游引往钟楼上方的中央机械室,即置身于笛卡尔时代之前的权力心脏——时间产房。在这座钟楼与不远处的大教堂刚刚竣工的十六世纪,时间是绝对的,是无限的统治者,更是世间有神的证据,因为所有的绝对都是“唯一绝对”的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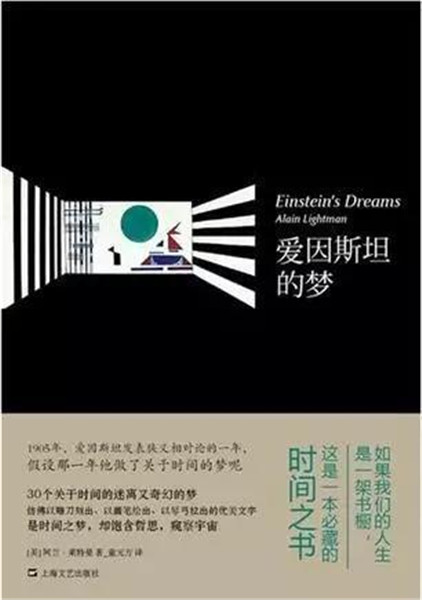
上海文艺出版社2014年出版的艾伦·莱特曼《爱因斯坦的梦》
伯尔尼大教堂正门上方,石雕全本《最后的审判》,恫吓妓女及出轨之人必将赤身裸体坠入地狱——人可疑,而时间不可疑,“最后”审判一切,时间绝对的世界似乎不乏慰藉。钟楼便是追寻并测量绝对时间的工具——至少要等到二十世纪初,伯尔尼专利局的小职员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的身影出现在钟楼脚下的克拉姆大街的时候,时间的绝对性才会受到不乏依据的质疑。
中央机械室的原理并不复杂:纠集石头、绳子、铁杆、铁轴和铁球这些受制于地心引力的简单器材,将其精密而勤勉地组合,旨在传递误差最小的自然能量,接生口含银勺身为神迹的动态时间,并将每一声初啼交由外墙张悬的恢弘彩钟,以及那些按时旋转的小丑、公鸡和狗熊,化作一场又一场赞美“唯一绝对”的公众仪式。

伯尔尼钟楼中央机械室
“时间产房”让我联想起四百多年之后,同样出现在瑞士的另一类机械装置,它纠集钢铁、铜、铬或其合金、陶瓷、纤维、棉线、电线、弹簧、橡胶、电机、塑料玩具、鸟羽、皮毛、动物骨骼、酒瓶、帽子、车轮、木桶等现成品,借助焊接、电镀、喷涂、缠绕、弯折和拼插的方式,将各色材料不精密而不勤勉地组合,并催生疏松而荒谬的运动。如果说伯尔尼钟楼的所有努力都是为了向意义,且是绝对意义致敬,那么归于艺术家让·丁格利名下的那些动态雕塑,则既不摹写时间,亦不生产物质,除去躁动便是盲目,乃是不折不扣地向无意义,且是绝对无意义致敬——自由而无用。
二者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爱因斯坦对于宇宙和时间的思考,肯定是改变二十世纪人类意识的一个重要原因,尽管其并非唯一原因。当他租住克拉姆大街四十九号(Kramgasse49)的时候,爱因斯坦想明白了一件事:时间没有绝对的定义。在艾伦·莱特曼的小说里,其后果便是“一些人发现,运动的时候,时间过得比较慢,于是焦急的人便以高速运动来增加时间”,而另一些人则发现,“离地心越远,时间流动得越慢,一些热衷于青春永驻的人,便搬到山上去了,占据着阿尔卑斯山上的诸峰。”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极大地改变了人类对于宇宙和自然的“常识性”观念,时间的相对性当然不只包括运动的时钟会变慢,更意味着时间的最基本概念——它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性质——发生了巨大变化。根据相对论的观点,对于在不同的方向或以不同速度运动的观测者来说,事件的时态没有绝对的过去,也没有绝对的将来。不同观测者的结论,在他们各自的参考系内,可能都是正确的,但在相对论里没有普遍一致的“现在”。如此一来,要命的问题出现了,“唯一绝对”的“最后”怎么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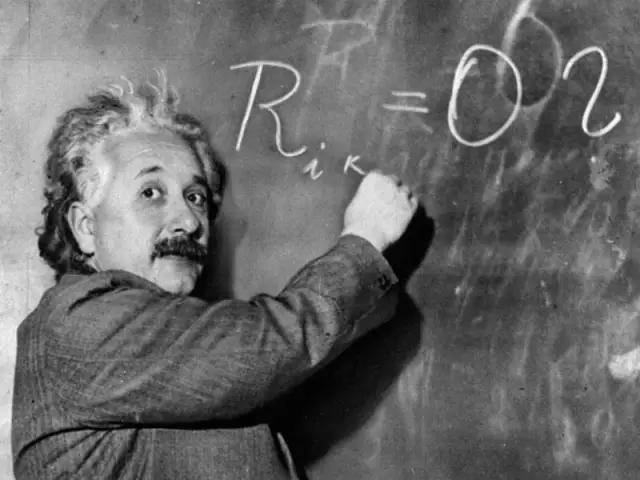
爱因斯坦
爱因斯坦的思考,与奥地利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对于人类潜意识的研究,以及作为“中央机械室”后裔的机器时代技术革新在武器领域的应用造成的后果,乃至从苏黎世伏尔泰酒馆所在的小街回到俄国的列宁发动的十月革命……共同改变了二十世纪“观测者”的意识,扭转了人们对于世界的理解。一方面是时间的绝对性被推翻,传统的“唯一绝对”深受挑战,另一方面,戴上新面具的“唯一绝对”又层出不穷,形形色色自我加冕的意识形态新势力,利用某些方向或速度领域的价值真空,匆忙搭建威权,杜撰标尺,打击其余。
1937年,“德意志第三帝国”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唆使举办过一场《退化艺术》(Entartete Kunst)展览。展品汇聚于慕尼黑,由“帝国文化协会”从全德国的博物馆和艺术收藏机构所没收的五千多件艺术品中剔选出的六百五十多件油画、雕塑、版画和图书组成。展览结构按照亵渎神明、侮辱女性、嘲弄士兵和农民、犹太艺术家作品等类别划分,意在引发公众对被贴上“退化艺术”标签的现代艺术的厌恶。

《退化艺术》展览
出自梵·高、克利姆特、席勒、夏加尔、康定斯基、基尔希纳、诺尔德和科柯施卡等艺术家之手的作品被摆放得混乱又拥挤,而且与普林茨霍恩医生从海德堡精神病院搜集来的病人作品并置于一处,策展者泼污水的意图昭然若揭,无非想说明现代艺术奇奇怪怪乃至堕落至极。然而,出乎“德意志第三帝国”统治者意料的是,《退化艺术》展览竟然吸引了超过二百万参观者,这一数字是同期举办的专门呈现官方艺术标准的《伟大的德国艺术》展览参观人数的近三倍半,乃至被国际社会戏称为德国人向现代艺术的一次朝圣,以及暂时的依依不舍的告别。
《退化艺术》展览的盛况
曾就读于慕尼黑艺术学院,并先后执教于包豪斯学院与杜塞尔多夫学院的瑞士艺术家保罗·克利,已于1933年被纳粹驱逐,回到故乡伯尔尼。《退化艺术》展出了他的十七件作品,他也被“第三帝国”的“唯一绝对”扣上了堕落的帽子。然而,在今天,他收获的却是这样的评价:“保罗·克利是二十世纪最多产的全能艺术家之一,由于他的天分是多方面的,因此很容易引起误解——似乎你可以任意选择一种方式来理解他……在克利的作品里,你能找到任何你想要的东西——它很深刻,也很复杂。”
这段话出自意大利建筑师伦佐·皮亚诺之口,2005年6月,他设计的保罗·克利艺术中心(Zentrum Paul Klee)在伯尔尼郊外正式开放。而在2016年3月,当我第二次造访该地,中心正在举办两个意味深长的展览:《保罗·克利:运动图景》(Paul Klee.Pictures in Motion)与《中国私语》(Chinese Whispers)。
保罗·克利艺术中心
《保罗·克利:运动图景》甄选自四千余件馆藏作品,尤其是那些与运动相关的绘画。其主题既包括受制于重力的运动,比如行走,也包括试图超越于重力的运动,比如舞蹈。展厅中播放的录像显示,保罗·克利关注的舞蹈,上承自苏黎世达达团体的“黑人舞蹈”,下衔于包豪斯运动的“几何芭蕾”。他所描绘的那些试图超越重力的运动,由“原始主义”的视野直通“理论化的时刻”。保罗·克利的作品中没有绝对真理,更因借助于爱因斯坦时代的视野,而使得所有试图杜撰“绝对真理”的意识形态骗术显得幼稚可笑。

保罗·克利,《南方舞者》,1908
《中国私语》由瑞士联邦政府所在地两大艺术机构——伯尔尼艺术博物馆(Kunst Museum Bern)携手保罗·克利艺术中心共同举办。70位中国艺术家创作于2002年至2015年间的150件参展作品,悉数出自前瑞士驻中国大使乌利·希克(Uli Sigg)的收藏体系,而且是其此类收藏最后一次亮相瑞士,这些展品将在2017年至维也纳巡展后,正式落户香港M+视觉文化博物馆。策展人凯撒琳·布勒(Kathleen Bühler)将展览分为“变化的痕迹”、“来自中国的全球艺术”、“与传统的关系”及“在消费狂热与精神追求之间”四个部分,其中,旨在记录和反思中国近期社会剧变的“变化的痕迹”,被设置于保罗·克利艺术中心,其余三个更专注于文化互动与全球化议题的部分,则借由伯尼尔艺术博物馆循序铺展。
对我来说,参展《中国私语》的大多数艺术家及其作品并不陌生,因为当前瑞士电梯公司员工希克入职北京大使馆,并以放弃个人审美趣味的百科全书式收藏方法,着手于“替中国保存当代艺术品文献”的时候,我恰好也担任着一份艺术杂志的特邀编辑,甚至与若干被希克收藏作品的艺术家保持着良好的私交。但是在与策展人凯撒琳·布勒朝夕相处的两天里——她坚持亲自为每一幅作品导览——却发现了许多新鲜的视角,一如爱因斯坦的观点所揭示:不同观测者的结论各有参考体系,但没有普遍一致的“现在”。

《中国私语》展览,毛同强《地契》
“中国私语”这一命名,来自于全世界小孩都爱玩的耳语传话游戏,其英语名称即为“Chinese Whispers”。耳语传话意味着期待、想象、误解、谣传和失真,这是全球化游戏的真相,但另一方面,作为陌生、难懂的“他者”本身,却并不会因为外界的误读和曲解而丧失原初的生机。布勒希望将这个展览放在欧洲正面临的空前难民危机的背景下来看待。
我理解她所代表的欧洲知识分子的焦虑——自巴塞尔离开瑞士边境进入德国,我便在公共汽车上遇见大批手持难民证的叙利亚人。虽然目前瑞士境内难民较少,亦无炸弹威胁,但不能闭上眼睛假装天下太平——瑞士国家旅游局全球客户主任包西蒙在苏黎世的一次招待晚宴上说道:那只是迟早的事。布勒抛出的问题有着这样的迫切性:我们在这样一个对外来文化充满疑虑,甚至恐惧的时刻,是否能够继续开放并思索新的可能性?
置身于如此时代背景之下,对于历经两次世界大战的欧洲来说,《中国私语》便不只是一项私人收藏的呈现,更是关于另一个文化,另一种身份认同的思考。虽然《中国私语》来自于百科全书式的收藏,作品的话语各有指向,但不难看出,当中国式的“绝对唯一”失效之后,艺术家们面对多重价值标准的交叉路口呈现出共有的复杂心态。实际上,如果剔除民族标签在国际市场上的商业价值,中国当代艺术便剩下一具持续向质疑开放的骨骼,相对主义立场弥散在大部分作品中。

《中国私语》展览,孙原和彭禹《老人院》
孙原和彭禹的电动装置作品《老人院》即是如此,一张张轮椅上,那些以让·丁格利的机械装置式节奏无规则移动的垂垂老者,正是来自二十世纪的“绝对唯一”自我加冕者群像,他们所抱持的全局性思想体系,不仅被爱因斯坦,亦被早期达达主义者所怀疑——“逻辑总是错的,它将概念和字词肤浅地引向虚假的结论和中心”。
站在2016年初,即便仅以来自亚洲的《中国私语》为例,亦不难看出达达主义在一百年间的诸种胜利。比如,达达将传统艺术中的人质——“美”,从二者的关系中释放,宣布现代艺术与传统美感的婚姻结束。特里斯坦·查拉写在1918年《达达宣言》中的那句话至今奏效,并为当代艺术背书:“客观地说,一件艺术作品决不为任何人呈现美感”。这意味着,不再存有任何标准化的美的经历。再者,达达主义者对于现成品的运用及其衍化,则更是成为当代艺术的一种基本手段。
如果说旅居美国的达达主义者马塞尔·杜尚(Marcel Duchamp)使用的现成品概念,以及他对大众文化的兴趣,为日后的波普艺术提供了一种参照,并促成了从视觉艺术到音乐、表演等领域的诸多精妙推演,其影响足以写成半部战后文化史,那么在中国艺术家手中,现成品则更接近于一种物证。毛同强的大型装置作品《地契》,搜集了从清代到文革时期的各种地契,见证了土地所有权如何沦为一张张废纸;而以李松松的《温都尔汗》为代表的一批新绘画,则将照片之类的现成品重新演绎为用途可疑的非现成品;何翔宇聪明地利用路易·威登的皮革和手工艺,制作出一只巨大的撒了气的坦克,指向硬实力向软实力的笨拙转换……可以说,如果没有达达主义,我很难在今天看到这些作品。

《中国私语》展览,何翔宇《坦克项目》
“没有什么意味”的魔力
让·丁格利拒绝承认自己是达达主义者。
可是,他不是达达主义者又是什么呢?
让·丁格利
他创造的动态机械雕塑《荷尔拜因喷泉》,不正是“愚蠢的天真”(雨果·巴尔认为德语“达达”含有此意)的化身吗?
让·丁格利从废旧金属中唤醒的那一大堆黑乎乎的“决不为任何人呈现美感”的形体,自1977年以来,已在巴塞尔老城剧院旧址前的水池里忙碌了近四十个年头:旋转,翻滚,喷水……但《荷尔拜因喷泉》的忙碌,绝无半点伯尔尼钟楼上“小丑跳舞,小公鸡鸣唱,小狗熊又吹笛又打鼓”那般为赞美绝对而忙碌的和谐,反倒更像是《等待戈多》舞台上的一伙货色,为混合肯定与否定而忙碌,荒谬地忙碌。
喷泉雕塑的“舞蹈”场景,据说与文艺复兴时期德国画家汉斯·荷尔拜因的一幅作品有关,遂有此总题,而水池中央“风笛演奏者”的灵感,则要拜阿尔布雷特·丢勒(Duerer)的画作所赐。荷尔拜因和丢勒的“照相写实主义”,在今天看来,虽有被摄影师夺去饭碗的风险,却属名门正派,《荷尔拜因喷泉》与其相比,一看便不是“赵家人”,不是“非艺术”就是“反艺术”。
让·丁格利《荷尔拜因喷泉》
让·丁格利对此供认不讳:“在我看来,真正的艺术显然是对整体文化的一种彻底叛逆,而且表明了一种政治的倾向。”毫无疑问,此说正是达达的主张。如果说启蒙运动主要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断定,“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那么后启蒙时代的达达主义者,便是铁了心地要为自己加持启蒙主义者眼里的“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让·丁格利即是如此,他自己也承认,“我的作品都是‘非艺术’,这些作品在画廊中看起来很有意思,它们表达了达达理念……那些仍在世的达达主义艺术大师认为我的作品体现的‘反艺术’正是他们所寻找的……我使达达主义步入正轨”,但他坚持嘴硬的权利——“我却并不是达达主义者”。此中纠结,简直是一出达达主义版哈姆莱特独白。
提契诺建筑师马里奥·博塔为巴塞尔设计的让·丁格利艺术馆,仿佛另一处《等待戈多》的舞台:代表自我加持的成熟收藏自我加持的不成熟,代表“整体文化”收藏对于整体文化的反叛。如果想在一百年后彻底厘清瑞士境内的达达主义,让·丁格利艺术馆应该是不可或缺的一站,他那些以“没有什么意味的”作品反对着作品本身的作品,只不过是从伏尔泰酒馆出发的登山专用齿轨铁路所抵达的山腰一站。他冒充现世上帝杜撰的那些机械,似乎比纽约达达马塞尔·杜尚对于“作品—工业产品”的形式关注更进一步,他着手拆解并重组“作品—工业产品”的具体“功能”,借助功能无效性对抗“整体文化”之于功能的期待。
让·丁格利艺术馆
走进让·丁格利艺术馆的展厅,仿佛置身于人类失败博物馆。被特里斯坦·查拉册封为“标志人类绘画死亡”的《形而上·机器》,已经花了半个多世纪的时间戏谑抽象绘画,至今依然会应观众的要求而转上几圈,再度将绘画作品祛魅乃至降格为机器产品——只要你伸出脚去,对准地上的开关猛踩几下。《形而上·机器》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在巴黎展出引发轰动后,让·丁格利便甩开手脚,大规模制作各种各样自由而无用的祛魅“产品”。他甚至发明出一种破坏性装置《打碎盘子的机器》,销售给一家销售盘子的百货公司,成为现代社会这台大机器运作状态中的一个有趣悖论。
美国过程哲学家大卫·格里芬(D·R·Griffin)从后现代科学的角度阐释了祛魅世界观的来龙去脉,比如其在《后现代科学--科学魅力的再现》一书中所说,“这种祛魅的世界观既是现代科学的依据,又是现代科学产生的先决条件,并几乎被一致认为是科学本身的结果和前提。‘现代’哲学、神学和艺术之所以与众不同,在于它们把现代性的祛魅的世界观当作了科学的必然条件”,“不仅在‘自然界’,而且在整个世界中,经验都不占有真正重要的地位。因而,宇宙间的目的、价值、理想和可能性都不重要,也没有什么自由、创造性、暂时性或神性。不存在规范甚至真理,一切最终都是毫无意义的”。
这么说来,达达主义反对的一切,即启蒙主义呼唤的理性,理性创造的科学,恰恰催生了达达主义,这真是一件达达得不能再达达的事。那种自我加持的不成熟状态,无非来源于“一切最终都是毫无意义的”祛魅的世界观。只不过,过程毕竟远非“最终”,《等待戈多》舞台上的角色毕竟要等待下去,甚至忘记了为什么而等待,高兴地唱起歌来。我在巴塞尔街头遇见过一位祛魅的鼓手,演奏的时候,他致力于将每一节奏击错,却创造出另一种魅惑。
让·丁格利艺术馆
让·丁格利的动力机械装置的强烈“过程性”所释放出来的音响效果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展厅上下,将艺术家、机械与受众置于整件“作品”之中的走了调的合鸣与变奏此起彼伏。而且,那些受制于地心引力的机械,总是在每一段演奏的末尾流露出疲态与衰竭,短暂的高潮之后,他们会像人类一样体力不支,总要休息一段时间,才能再次为急切地踩踏开关的观众演示“一切最终都是毫无意义的”努力与勤勉。
1959年底,让·丁格利在英国现代研究院举办了题为“Static, static, static! Bestatic!”的演讲,从头至尾不置一词,仅由录音机播放演讲内容。其现场效果,与早期达达创造的语音诗歌(Poème Simulatane)颇为类似,而达达主义经由诗歌产生的对于语言的颠覆,已经深深地影响了二十世纪迄今的写作、艺术、思维方式与意识状态。
好吧,还是让我们回到伏尔泰酒馆。十几年间,我每次来到苏黎世,都会路过这家酒馆,但直到两年前,才意识到它就是达达主义的起源地。
伏尔泰酒馆内的达达主义创始人群像
虽然在1917年后,苏黎世达达因为声名鹊起而逐渐将主要活动场所搬到了利马河对岸的豪华大楼,比如以彩色玻璃、花砖火炉和鱼类烹饪而闻名的沃格会馆餐厅(Restaurant Zunfthaus Zur Waag),达达主义者就像修正主义者那样出售昂贵的晚会门票,预先拟好客人名单,以期吸引具有良好教育背景的“开明观众”,也就是他们在一年前强烈反对的资产阶级,乃至此类活动被理查德·许尔森贝克讽刺为“工艺美术的修甲沙龙,其特征是一群喝茶的老妇人借助于某种’疯狂之物’,试图恢复期正在失去的性能力”,而且伏尔泰酒馆所在的老屋,实际上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各国艺术家返乡之后,便在二十世纪的多半剩余时光中处于空置状态,甚至差点儿被拆迁、变卖,但它总算被本地艺术家的占领行动以及随后的议会辩论保留了下来。
2002年2月2日,马克·迪沃(Mark Divo)率领十几个人闯了进去,所有人都穿上正装,在这座破败的“前卫的纪念碑”里举办了一场音乐会。2004年9月30日,借助于苏黎世市政府资金的补贴,伏尔泰酒馆重新开业。“如果谈到达达主义,只把它看作一场时代思潮,那么就会把它与伏尔泰酒馆分离开。但群众就是群众,他们喜欢将达达主义和伏尔泰酒馆绑定在一起。”酒馆现任经理艾德里安·诺兹(AdrianNotz)以近乎列宁的口吻如此表示:“即使伏尔泰酒馆不复存在,这对于达达来说也算不上灾难,但这对于苏黎世来说却将会是一场灾难。即使其他地方认可达达,例如巴黎和柏林,但是达达的发源地终也只有一个。”
我不清楚真正的达达主义者是否喜欢原教旨主义一般追溯历史的方式:酒馆的正厅努力恢复成1916年的风格,与伏尔泰胸像相伴的,是墙壁和立柱上悬挂的那些达达主义“经典样式”的图画、拼贴和照片,桌椅看上去也很陈旧,依然仅供五十人左右使用,小舞台一侧的小钢琴看上去的确超过了一百岁……
伏尔泰酒馆正厅
不过,伏尔泰酒馆中也有一些新鲜的东西,比如摆满艺术衍生品的商店,以及穿过商店继续下行所抵达的那个洞穴里的剧场,中间是一座闪闪发光的金属舞台,阶梯状,就像小型金字塔,塔顶矗立一根同样材质的烟囱或柱子,将观众的视线引向天花板,那上面以达达的方式记录着达达的历史,以及从未参加过达达主义运动的达达主义者的名字,比如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卡尔·荣格(Carl Gustav Jung),等等——实际上,苏黎世歌剧院旁边的大使酒店(Hotel Ambassador)也是这么干的,楼梯一侧旋转向上的墙壁成为了展览空间,陈列着推翻“唯一绝对”阵营的“一百单八将”的肖像与生平,其中包括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与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
伏尔泰酒馆地下剧场
这是一场彻底的狂欢。整个苏黎世都已沉浸在这种追溯与狂欢之中:名为《达达苏黎世》的城市地图上标出了163个与这一运动相关的地点;瑞士境内拥有最多达达艺术品的收藏机构苏黎世艺术博物馆,正在举办《重建全球达达》(Dadaglobe Reconstructed)展览,并着手将档案柜中沉睡多年的达达文献和540件艺术作品进行数字化;火车站附近的国家博物馆则在举办“全世界的达达”(Dada Universal)展览,意在阐释达达的国际化及其对后世的影响,其副策展人巨日·斯坦纳(Juri Steiner)亦是创建纪念达达一百周年网站和组织相关活动的协会主席;此外,还有无数的其他展览、演出、朗诵会、讨论会、化妆舞会、城市游、图书出版、纪录片以及网络项目……
伏尔泰酒馆正在举办为期165天的马拉松式庆祝活动,并推出一个名为《痴迷达达》(Obsession Dada)的展览。我之所以会像让·丁格利的装置中的一小截弹簧那样在清晨六点冒雪赶往伏尔泰酒馆,就是为了去聆听马拉松式纪念活动中的一场晨祷般的诗歌朗诵。
前一天夜里,我刚刚在酒馆听过一场朗诵。一位漫游欧洲的诗人,带来两台彩色速印机,将镶嵌着自己诗句的达达主义风格招贴画现场打印出来,分赠与观众。活动结束,正当我准备离开伏尔泰,前往对面的Baltho酒店尝一杯最新推出的“达达主义苦艾酒”的时候,负责艺术项目的诺拉·豪斯维特(NoraHauswiehrt)叫住了我,她提醒道,明天六点半还有一场朗诵。哦,很遗憾,明天中午我就离开苏黎世了。不,她说,不是下午六点半,而是早上,艾德里安·诺兹每天在那个时刻朗诵一位达达主义者的作品。喔,这真有点意思。于是,第二天一早,我和其他三位本地观众,以及另一位国际观众一道,在一片灰黑的黯淡之中,再度钻入刚刚亮起灯光的伏尔泰酒馆。
朗诵现场打印的达达主义式作品
朗诵并未准时开始——否则真不达达——差不多六点三刻的时候,身着正装的艾德里安·诺兹扫视了一下所有观众,然后转问我:英文朗诵,怎么样?当然好。于是,他打开一本书,面向观众介绍今天的诗歌作者,达达主义艺术家奥托·格里贝尔(OttoGriebel)的生平,身旁竖着一只高科技的乐谱架——如果仔细观察,会发现应该摆放纸质乐谱的位置夹着一台平板电脑,设置为自拍模式。而后,他转过身去,背对着观众朗诵。
伏尔泰酒馆的达达主义诗歌朗诵
1916年6月23日,雨果·巴尔在这里朗诵语音诗歌的“经典照片”张悬在他身前的墙壁上,仿佛一具圣像。雨果·巴尔的日记还原了那个时刻:“我的两腿被包在一个闪闪发光的用蓝色硬纸板做成的圆柱里,圆柱高到臀部,因此我看起来像座方尖塔……我在外面套了一件用硬纸板裁剪而成的高高的外套衣领,里面猩红外面金黄……我还戴了一顶高耸的蓝白条纹相间的巫医帽。”那个晚上,他被带往一排绘有涂鸦的乐谱架前,开始大声朗诵咒语:gadji beribimba/ glandridi lauli lonni cadori/ gadjama bim beri glassala……

雨果·巴尔1916年朗诵造型
语音诗歌朗诵中一连串刺耳的无意义的噪音,既来自于达达主义者对意大利未来主义者诗歌表演的借鉴,更来自于雨果·巴尔的“发明”——他将诗歌拆碎,将基本词汇与生造词汇混杂于一处,从而比意大利先驱的作品更“抽象”,成为含混不清的咒语。他强调,“在语音诗歌里,我们完全抛弃了已被新闻界滥用的语言……我们必须恢复字词最幽深之处的魔力。”这种拒绝接受语言的符号能力,即传达意义的能力,转而试图回归语言的基本单位,并试图为事物寻找新名称的神秘欲望,又何尝不是对德国哲学家尼采的若干观点的回应。后者对雨果·巴尔那一代艺术家产生了重要影响,他把语言视作已经疲惫的“移动的隐喻大军”,并声称在单词及其对应物之间产生过不搭配的感觉。
我没能听懂一个字。朗诵结束,没有人发出早期达达主义者必须面对的嘲笑,唯有一连串礼貌的掌声。艾德里安·诺兹投桃报李,提出请大家喝杯咖啡。但当他钻入吧台,奋力捣鼓了一阵之后,又严肃地走回正厅宣布:咖啡机坏了,没有咖啡了。

多么完美!否则多么不达达!这让我想起范内哲姆在1968年撰写的《日常生活的革命》中的一句话:“达达的开始是重新发现活生生的体验及其可能的乐趣——它的结束时对所有观点的颠覆,它创造了一个崭新的宇宙。”
编辑:徐啸岚
相关新闻
0条评论
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