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
为了纪念安迪·沃霍尔诞辰88周年,展览《安迪·沃霍尔:接触》正在798艺术区木木美术馆进行,旨在以“一系列最具划时代意义的影像、摄影及互动装置,展现大师的别样艺术才华”,展览的全部作品均来自于安迪·沃霍尔博物馆,将一直持续到2017年1月7日。这并非安迪·沃霍尔第一次来到中国,对于他的一头白发和梦露型波普模板,即便是不太懂艺术的人们,或许也早已熟悉,能够在现代艺术的茫茫汪洋中一眼识出。
安迪·沃霍尔的名字从开始就与商业文化绑在一起。他享受并获益于商业化,又在作品中见缝插针地对此进行批判。下面这篇文章节选自《绝对批评:关于艺术和艺术家的评论》(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6月版)一书,美国最具争议的艺术评论家罗伯特·休斯(Robert Hughes)以充满才智与批判的眼光,重新审视安迪·沃霍尔其人以及其艺术作品与价值,“提出了决不妥协的观点”,或可为我们提供看待沃霍尔的不同视角。

沃霍尔似乎长期以来就渴望能有一种最即时的能见度和受欢迎程度,如丽兹·泰勒(Liz Taylor)这样的“真正”明星所具有的那种。而且,他有时还被人诱使,表现得好像他真的获得了这两样东西。他一做广告,支持波多黎各朗姆酒或先锋牌收音机时,艺术界就呻吟起来,却暗中嫉妒:有人花大钱请你做代言,而且越拒绝,感觉就越爽,哪个艺术家不想占据这样一种有利形势呢?但是,靠他形象卖掉的朗姆酒和收音机很少。先是主要给边缘人当偷窥者,接着是给富人当偷窥者,一当就是20年,沃霍尔依然没有从世人那儿得到足够的爱,人们看到的仍然是那个怪怪的、冷漠的戴假发的家伙。与此同时,实际置身于广告的那种作态,与沃霍尔在艺术界的名望则十分龃龉。就他作品达到的颠覆性程度来讲(60年代稍微有点颠覆性),它之所以能达到这个程度,也是因为它对广告的大众诉求进行了粗粝的、冷峻的拙劣模仿——重复制造商标形象,如坎贝尔汤、布里洛盒或玛莉莲·梦露(成了人体商标形象的一个明星),到了这样一个地步,以至于可以看到推销话语的下面有一个巨大的空洞。

沃霍尔式波普模板。
这就造成了一种紧张状态,这种紧张状态取决于60年代依然有效的那种假设,即在对高雅艺术的看法和通俗文化日常产生的不计其数的消遣和知识之间,有着质量上的差别。自从那时以来,沃霍尔比其他任何一位在世艺术家做得更多的事,就是把这个差距抹得越来越小。但他这么做时,也磨平了自己作品的锋缘。同时,他朝身着天蓝色聚酯薄膜的勒罗伊·内曼绝对受欢迎的高天行进的过程中,还是遇到了困难。要做到这一点,他就必须让人能够接近他本人。但一让人接近,他就会失去魔力。
《波普主义:沃霍尔的六十年代》和《曝光》这两本书合在一起,是沃霍尔在1968年被枪击前后所关注诸事的很好的写照。两本书都没有文学价值,写得就像聊大天,偶尔会闪现出微弱的讽刺来——正好是套餐所许诺的内容。《波普主义》大部分内容都是很肤浅的闲聊,《曝光》则完全是闲聊。作为一个一生都被纠缠不休的闲言碎语包围的男人,沃霍尔给人一种印象,仿佛特别不受性格的影响。“我从来都不知道该如何看待埃里克。”他谈到他60年代朋友圈里的一个人时这样说。此人是个小伙子,一个马大哈,蓄着亚麻色的卷发。按后记中所述,他的尸体在哈德森大街的路中央被人发现,根据“谣言”,是在吸食过量海洛因后被人很随便地抛尸大街的。“他说的话有时很有见解、很有创意,但跟着说出的话却愚蠢至极。很多小孩子都像那个样子,但埃里克对我来说最有意思,因为他是最极端的个案——你绝对没法分清他是天才还是低能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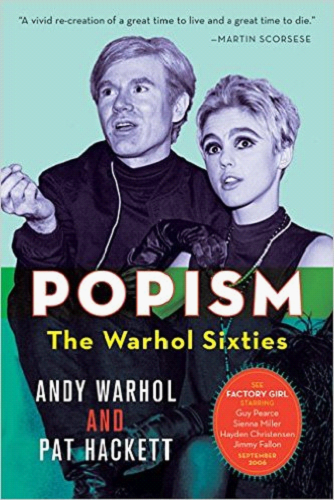
《波普主义:沃霍尔的六十年代》
当然,可怜的埃里克·埃默森(Eric Emerson)几乎就像“工厂”周围的所有人一样——“工厂”是沃霍尔画室后来为人所知的名字——两者都不是。他们都是文化太空垃圾,从60年代各种各样的亚文化中漂流出来的碎片(变性人、吸毒者、性虐狂和受虐狂、摇滚歌手、富家小可怜、犯罪分子、大街混混,以及所有这些属性的排列组合);才能本来就浅薄,而且在这个极小的宇宙中分得很散。它在音乐中有所浮现,代表人物是卢·里德(Lou Reed)和约翰·凯尔(John Cale)。70年代各种不同的朋克团体就是沃霍尔地下丝绒乐队的子息。但是,那些想继续干自己活儿的人就会对“工厂”避之唯恐不及,而那些怪胎、“骨肉皮”和喜欢猎奇的人会把“工厂”塞得满满当当,身后什么也没留下。
“工厂”贴满锡箔的墙壁形成了一个玩具剧场,美国60年代的一个方面,即通过终极的自我表露把自己强加给世界的小儿科般的希望,就在里面逐渐展开。它令人不快的锋刃把处于边缘的那些人的偏执逼成某种类似风格的东西,某种能让人回忆起艺术的东西。如果沃霍尔的“超级明星”——他就是这么称呼他们的——真有才能、真有素养或真能持之以恒,那他们本来就不需要他。话又说回来,他也不会需要他们。他们给了他一个幽灵般的权力光环。如果他收回凝视的目光,收回仔细分配的认可和承认,他们就会不复存在了。穷一点的就会冰消雪化,滚回大街上满是泥泞、不分你我的混乱状态中去,而富一点的结果就是钻进某家适合他们的诊所里去。这也就是为什么开枪射杀沃霍尔的瓦莱丽·索拉纳斯(Valerie Solanas)说,他对她的生活取得了过多的控制。
那些挨父母骂,说他们疯了的人,那些欲望得不到满足、野心大得让人讨厌的人,那些对一切都感到有罪的人,就像受了地心引力一样都聚集到沃霍尔那里。他仿佛给他们下了一道特赦令,就像一面空镜子的凝望,拒绝接受任何评判。在这方面,摄影机(他拍电影时用的摄影机)充当了他的代表,把发脾气、秀痛苦、性发作、搞同性恋以及挖鼻孔这类鸡毛蒜皮的事情成小时地收集起来。这其实也是一种显示权力的工具,不是针对观众——因为沃霍尔拍的电影一般都很无聊,拒人于千里之外——而是针对演员。

沃霍尔是第一位使公开宣传成为其艺术生涯固有特征的美国艺术家。公开宣传对四五十年代的艺术家来说并不是一个问题。公开宣传可能会像晴天霹雳一样从市侩的天空中闪现,就像《生活》杂志让杰克逊·波洛克一举成名天下知时那样。但是,这种事情太罕见了,不仅达到了异乎寻常的程度,甚至可以说它怪异到畸形变态的地步。按今日的标准,那时的艺术界对大众传媒及其能力的看法天真得好像处女似的。反过来说,电视和报界对还可以称之为先锋的艺术家是漠不关心的。艺术家的生活方式、装修方案、婚姻和意见,更不用说低到让人产生不了兴趣的价格标准,等等,没人想要大量发表有关这方面的东西。所谓公开宣传,就是在《纽约时报》发表一则只有一两段文字的通知,最后跟着在《艺术新闻》写一篇文章,可能只有5000人看这篇文章。别的一切都会被视为作品的外在之物——令人生疑的东西,说好听点是次偶然,说难听点根本就是免费转移视线的东西。你可能去拉拢评论家,但不会去拉拢时装记者、电视制作人,也不会去拉拢《时尚》(Vogue)杂志的编辑。在四五十年代的纽约艺术家眼中,穿上一套为自己捞取公共关系的服装,那几乎是不可想象的——这就是为什么他们都瞧不起萨尔瓦多·达利。但在20世纪60年代,随着艺术界褪去了理想主义的偏见,放弃了甘当局外人的感觉,开始进入美国艺术产业时,这一切都开始变化。
沃霍尔成了一个典型,而且在不小的程度上,也成了促进这一变化的工具。
要想进入这种湍流,只需要出生就行——正如沃霍尔那句俏皮话说的那样:“将来,人人都可以著名15分钟。”但是,想永远待在这个湍流中,想被推销文化喷射出的闪闪发光之物淋个浑身透湿,你还需要其他素质。其一就是扮出一种超然物外的神态。花花公子是不能直盯着相机镜头的。其二是要有一种强烈的微妙感,眼睛要盯在时尚的潮流和漩涡上,它可以调节其他的感官和胃口,只有这样,才能使保持超然物外的态度显出自己的道理来。
沃霍尔费尽心血,又冷到极处,他在这两方面都达到了惊人的程度。他不是一个“炙手可热”的艺术家,那种为一个特殊的愿景所支配并急于将之强加给世界的人。杰克逊·波洛克曾宣称,他要成为大自然。沃霍尔与他适成对照,要成为的是文化——而且只成为文化:“我要成为一台机器。”许多抽象表现主义之后成名的美国艺术家,如贾斯珀·约翰斯和罗伯特·劳森伯格,为了生存都做了商业艺术。当然,除了沃霍尔之外的其他波普艺术家,也都从美国的大型广告传媒形象库中自由随意地汲取材料。但沃霍尔是唯一一个把这类推销文化具体化的人。他作为一个商业艺术家,享有惊人的成功。他什么都做,从鞋子广告到食谱插图,后者是用从本·沙恩(Ben Shahn)那里派生来的一种颇有生气的污渍线条来描绘的。他还不是“贵族”,但试图成为“贵族”,他太了解这个难以对付的小世界了。在这个世界里,时尚、飞短流长、操纵形象和新潮自恋的机器弹出了它轻快的拨弦曲。他知道如何包装,而且还能授人以术。

1983年,头戴沃霍尔式假发的人们。
正如哈罗德·罗森伯格所说:“沃霍尔在通过演示证明艺术是艺术市场的一种产品,可与其他专业市场的产品相比拟时,就已经把严肃艺术家和多数人文化之间几百年之久的紧张状态给消解了。”沃霍尔画什么内容已经几乎没有关系了。对他的客户来说,只有签名才完全可见。工厂在运作,产品的流动没有中断,市场支配着市场逻辑。客户要的就是一个沃霍尔的签名,一个盖上他图章,能够识别的产品。这就是为什么说任何偏离正轨的明显标记,如与世界发生虚构的关系而可能产生的结果,事实上都会显得怪里怪气、令人不快。沃霍尔的至高卖点就是以重复来舒缓客户,同时维持虚构出来的独一无二的感觉。风格本来被认为是真实的经验残余,但现在却成了商业艺术的把兄弟,成了风格化。
沃霍尔在这一点上从不自欺欺人:“把同一种东西一遍遍地画下去,真是无聊得要死。”他在60年代后期抱怨说。因此,他必须在套餐里引入一些小的变异,把上一次的产品弄得有点过时(并限制它的繁殖,这样才能保证它比较罕见),因为如果沃霍尔的所有产品都一模一样,新产品就没有市场了。这就是他对创新的恶搞,这在市场主宰的艺术世界里现在看起来已经很正常了。其工业化的性质需要同样工业化的制作法:做法是用照片,一般都是拍立得照片,来制作银幕,通过降为单色的方式放血一样地放掉形象中的大量信息,然后印在模糊的装饰色彩背景上,再用宽宽的蘸满颜料的画刷子在上面刷过,使画面给人一种富有神韵的印象。形象和背景之间哪怕有一点形式上的关系,这种情况也极为罕见。
首发于1982年《纽约书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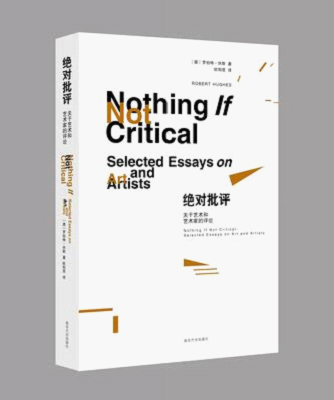
编辑:隋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