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侯瀚如
2017年12月,第七届“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UABB)在深圳南头古城开幕。此次双年展,将原有的建筑、城市讨论扩大至艺术领域,并邀请了侯瀚如担任艺术板块总策展人。在创造性地将展场移植到城中村之后,大量的艺术家也参与了这一建筑师的盛宴,而这,与侯瀚如不无关系。
作为当代艺术界为数不多的城市议题研究者,侯瀚如早在1997年就开始了对亚洲当代城市建设和艺术的互动及其在全球化过程中的发展展开了研究。他策划的“运动中的城市”,在7个国际城市的巡回过程中,引起了艺术和建筑界的热议。而此次他在UABB中主导的“艺术造城”板块,通过遍布城市、展场的影像、摄影、装置、行为作品完成了艺术与建筑、城市之间的对话。
我们在2017年冬日的深圳南头古城,乘着“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忙碌的间隙采访了他,就有关艺术、建筑与城市以及策展的诸多问题展开了以下交谈。
走进“城中村”
典:是什么契机让你加入此次“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的策展团队?你与刘晓都、孟岩等策展团队成员有着怎样的分工?
侯:早在十几年前,我曾与皮力一起参与过何香凝美术馆、华侨城主办的深圳雕塑双年展的一些项目。从此,就与深圳结下了一些缘分。从那个时候起,我陆续认识了深圳的许多艺术家、建筑师,包括这次“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中“艺术造城”的联合策展人杨勇、“都市实践”的孟岩他们。前几年,很偶然的一次机会,我恰巧从深圳经过拜访杨勇。彼时,正值“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每两年换策展人之际,杨勇便提及试一下。在提交完方案后,我便回了法国,几乎没再想过这个事情。后来,这个方案颇为顺利通过了,我也就加入了“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的策展团队。至于分工,刘晓都与孟岩当然主要是负责建筑部分,包括“世界| 南方”“都市| 村庄”两个板块。而双年展的艺术板块“艺术造城”,则是我和杨勇。

李燎,《单人床》
典:作为一种新的尝试,2017年的深双从“城中村”中展开。现代城市系统中“城中村”所展现的是怎样的城市经验与语境?而深圳的南头古城与香港的九龙城等典型的“城中村”比,又有什么不一样?以南头古城作为展场,能为展览提供怎样的经验和实验可能?
侯:“城中村”是一种临时状态。对于居住在其中的人而言,它是人们进入城市的途径,它是医院、图书馆,或是客栈。它是一种自下而上的体系,拥有现代城市体系中缺少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从某种角度来说,“城中村”也呈现出了一种文化自信。
至于南头古城,拿九龙城与它类比当然可以,但这种比对只是一种比较方便的说法。深圳与香港相比,更像是一个分散却又有规划的城市试验场。它是政府主导的,而香港则由商业主导。两者之间,有一个土地权利所属的问题。九龙城相比南头古城而言要更加复杂,它包括了抗日战争时期大量内陆居民的移民、英国殖民等大量的历史遗留问题。而南头古城除了拥有现代都市体系中“城中村”的特点、隐喻之外,它亦是当代中国改革开放、高速造城运动的一个缩影,而这些与深圳这个城市所隐含的象征性密切相关。深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符号,与“速度”不可割裂。在短暂的三十年,迅速完成了城市化,这在欧洲是不可想象的。在巴黎,我家门口一条地铁线建了好几年仍旧没有完成,并且听说工期仍在不停的延后,而这种情况在深圳几乎不大会出现的。但是,快的代价,也是复杂的。双年展作为生活流中的放大时刻,这种复杂的代价会自然地反映在双年展和展场之中。在此基础上,速度背后所依赖的研究积累,建筑本体存在的教育性,都给到了南头古城以新的经验和语境。
开放的“现场”
典:从当代艺术自身的发展来看,它也面临日渐同质与单一的问题。同时,面对当代中国三十多年裹挟在权力和资本下的高速造城运动,当代艺术也同样裹挟在权力与资本之下。这就引起了一个疑问,当代艺术的介入是否真正是城市反抗同质化和单一化的有效途径?如此相似的时代境况,当代艺术又能为建筑及城市生活补充什么?
侯:坦诚地说,当代艺术其实做不了什么。
从功能性来看,大多数人会觉得艺术是美化与装饰,而建筑则是对于城市规划、总体议题的讨论。但是,现实并不是这样。从上个世纪以来,当代艺术越发偏重于对于观念、问题的讨论,艺术家会制造事件、营造议题,试图撩拨大众心理、共识来引发批判性思考。而建筑则是越来越下沉至城市细节,为具体的生活矛盾提供解决方案和结论,并承担起了一部分装饰与美化的功能。
艺术对于具体的城市改造而言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即便有,也是虚的。表面上,建筑与艺术有互相刺激的作用。这次双年展中的几个大项目,包括犬吠工作室《火焰美食家+俱乐部》、蔡荣基《大排档花牌》、徐坦等人的作品都是艺术作品,而非纯粹的、传统意义上的建筑。似乎,艺术为建筑带来了新的活力。但事实上,面对城市、建筑,艺术是无法造城的,艺术能造的只是某种意识。它让人们重新去看待自己生存的环境,从而赋予空间、城市以新的变化。当代艺术从固有问题、认知的逆行而上,艺术家们通过剥除依附于事物身上的日常性,将习以为常的事物从日常生产场景中抽出、变形、复杂化,从而获得新的空间意识、政治社会意识,以及对自我的反思。

林一林,《安全渡过林和路 某一天》
典:此次由你主导的“艺术造城”板块,是以大量的“现场”来构成的。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策展方式?“现场”又如何理解?
侯:“现场”是开放的,每个人皆可参与其中,每个人都可以携带着自己的经验而来做出阐释。在“现场”中,一切都在发生变化,它是偶然的、临时的。在“艺术造城”中,城中村这一展场本身,是“现场”;水泥的毛坯旧厂房,是“现场”;作品与观众之间的互动、解读,也是“现场”。来到这样的环境之中,观众、艺术家、作品都与普通的展览不一样,它所面临的问题并不是传统的白盒子空间所会遇到的。在当代艺术常规的白盒子展示空间中,艺术本身就是真理。它通过与外界完全的割裂、自我孤立、空白赋予艺术新的语境。但“艺术造城”的展场并不是如此。它是完全开放的,与现实生活紧密联系,会与城中村的日常发生近距离的流动。在这样的状态中,艺术作品被迫再次回到现实语境之中,无法单纯依赖空间的割裂来获得阐释。艺术在这里,不需要教育,不依靠文字解释,不需要讲述某个完整的故事,它本身就有自己的感染力。这些,都与“现场”契合。
我希望展览呈现出的是一种真实状态,而不是停留于一个抽象的概念。所以,在策展的时候,我们并没有试图改造这座旧工厂,不刷墙、不封闭窗户,保留其原有的痕迹,只做简单的清扫,尽量还原出“现场”的原生状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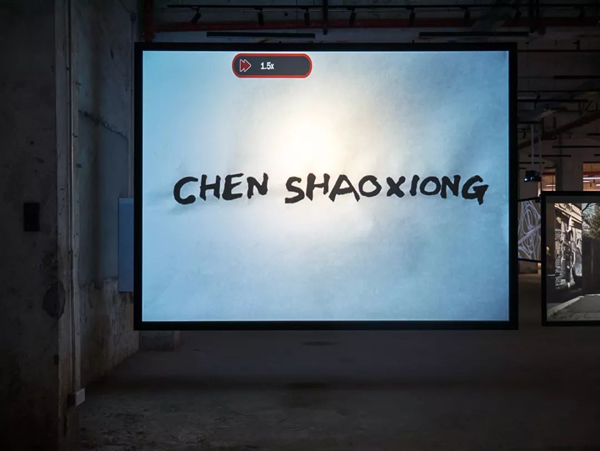
陈劭雄,《墨水日记 墨水城市》
典:在“艺术造城”板块中,众多作品在类型上呈现出了高度的一致性,即影像。这是否是策展团队刻意选择的结果?如果是,为什么会做这样的选择?
侯:在选择作品时,确实是比较偏向于影像与摄影作品的。一方面,影像在今日确实成为大众语言。随着影像技术、手机等载体的普及,今天所有人都在使用影像语言,每个人都可以拿手机拍电影、拍照片来讲故事,大众对于影像感受力是非常强的,也可以调动起观众的参与度与潜在创造力。城中村的居民进入展场,亦能很好地进入其中。而另一方面,影像与废旧工厂环境、水泥墙结合,提供了一种别样的感受。影像作品拥有极大的叙事能力和感染力,对于文字并没有特别的依靠,适合“现场”的原生状态。

鸟头(季炜煜 x 宋涛)影像作品展览现场
典:影像作品在展场常常会遇到一个问题,即时长问题。许多作品常常会达到半个小时以上,观众要完全看完每个作品非常困难。在“艺术造城”板块中,是否有遇到这个问题?应对影像作品的展示问题,线上的展览方式是否是最佳的替代方案?
侯:这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或多或少会遇到。观众在展场,是否真的需要全部看完呢?
我想我还是比较老派的,还是会迷恋从一个影像片段穿梭到另一个影像片段,在影像与空间探索的感觉,以及其它更为私人的体验与感受。如果完全将影像作品放置于虚拟网络上,或许时长的问题可以得到解决,但很多真实的细节、观感便会失去。
“非典型”共生
典:在展览中,为什么会选择林一林、曹斐、李燎、鸟头等当代艺术家们作为切入、实验与观察的线索?作为实验的观察切片,他们是否具有典型性?
侯:讨论典型性是没有太大意义的。个体存在复杂性,每位艺术家及其作品在观念、风格等方面都不是停滞与固化的。认知中的“典型性”,会随着时间、环境等众多因素而快速消解。所以,在选择这些艺术家作为实验与观察的线索时,其中的部分原因是我们彼此熟悉,了解他们近期的创作现状、观念认知。在这种相对熟悉的状况下,主题的切入才得以准确、深入。当然,作为双年展的一部分,这些艺术家及其作品身上确实也展示出了与观众、展场之间的互动、引导与偶然。比如,林一林这次的行为表演。在城中村的街市,各种食物被逐一按着一条直线在地面排开,存放了近一个小时。这些日常的事物,在日常的环境之中,因为摆放方式的改变而得到了一种新的意涵。居民们观看、参与而后产生疑问,或是思考,随着短暂的表演结束、消失,疑问与思考的痕迹会留下来,渗透到空气中,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编辑:江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