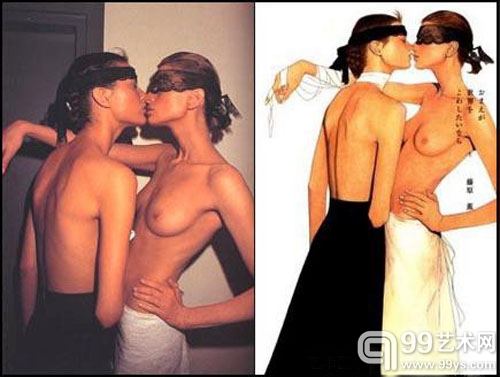
当代艺术史学始终是在“语言转向” 与“图像转向”的张力之间摸索化解“形式与内容”、“文本与情境”间的复杂关系。把形式分析与图像学研究结合起来,被美国艺术史家萨默森(David Summers)称之为“后形式主义”。一件艺术作品被视作一个集合了很多符号的“文本”,由“解读/阅读”(reading)取代“观看” (seeing),也就改变了艺术的表述方式。对应于语言“再现”的阐释功能,就需要用“上下文”来读取艺术的情境,而视觉图像的再现阐释则主要是模仿和 象征。
“模仿”的历史
柏拉图说艺术的模仿是“模仿之模仿”,“与真理隔了三层”。柏拉图害怕图像削弱人的心志,或混淆现实甚至取代现实,因此批判模仿,贬抑表象的美感,同时也置不实的“拟像”(simulation)于真理的阴影之中。
到 了亚理斯多德时代,开始揭示自然的现象和本质,肯定艺术模仿自然的真实性再现。以此,现象与本质、形式与内容的传统再现方式具有了合理性。所谓三种模仿方 式:(一)照自然事物本来的样子去模仿;(二)照自然事物为人所说的样子去模仿;(三)照自然事物应当有的样子去模仿。亚里士多德推崇的是第三种方式。以 此,事物无论是“可感知的”或“超感知的”、“可见的”或“不可见的”,也无论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何,都统统归到“模仿”的名义之下。
在漫 长的中世纪,模仿论受到压制。基督教思想认为模仿是真理的“沐猴而冠,相信上帝会禁止对这个世界的任何模仿”。文艺复兴让人认识到人的自身就是一个能反映 大自然的小自然,从而进入了人文主义与基督教妥协的折衷时代。主观及物质感官的介入,视觉感官产生的“符号” 开始阐示想像力及记忆的幻影,但视觉仍离不开心灵的统摄,“拟像”仍然居于劣势。
十七世纪西方思想史发生重大转变,笛卡儿(René Descartes)强调是由心灵“看”到符号,而不是必须与视觉有关。以此,“再现”就不再以视觉形式为依据,而是由内因性生成的感觉来作为代表。由此 模仿由“本体论”向“认识论”转化。从“艺术作为反映自然的镜子”,转而反映作为思维主体的内省的人。艺术家开始从人的理性思想去寻找真理的根据。 如康德(Immanuel Kant)说:“ 想像力有强大的力量,能根据自然现实所提供的材料,创造出彷佛是一种第二自然,即超自然的东西。” 黑格尔(Hegel)更进了一步,说艺术的发展并非通过模仿自然,而是观念的表现。具体的感性形象仅是显现精神理念的载体;而精神最终要摆脱物质形式的依 赖,获得精神的最後解放,(但换来的将是“艺术的消亡”)。
进入20世纪的现代主义,艺术不但要再现自己的视觉经验,更重要的是找到再现 的形式和属於自己的语言。加上尼采主体的参与,“再现”就成为“如何产生”,而不是“像什么”的问题了。艺术经过不断的“简化”和“抽离” (Abstraction),到了抽象绘画,已除净了任何自然参照,剩下的只是色彩符号构成的形式之美。
当形式主义的抽象艺术被视作符号时,“再现”就并不仅仅是关涉视觉表象的意指行为,不再仅仅在于再现的对象,还可以转过身来关心自身的象征和思想传达,抽象形式和观念符号,也就此一变而为超越事物表象的“非具象” (拟像)再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