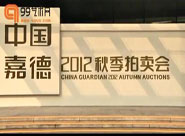许多技能本来可以在一线的实践部门更容易轻松学会,却硬生生地被拖进了院墙之内,到一个被叫做大学的地方去进行抽象的空谈。转弯抹角地采集来一些花俏的视频,费尽心机地设计出一套规范的图标或制造出一大堆可以乱真的模型,其实都只能是脱离原样的模拟示意,一种自欺欺人的貌似而已。那就肯定不会再有现场的生动性、随机性和感染性。在一处人造的景篷中扭捏地仿效真实必然拙劣。这既降低了探究学问的自身高度,又把实践中本来容易的触景生情之事儿人为地复杂化了。
注解这类做派的最堂皇的标签就是包豪斯(Bauhaus)的“learning by doing”.其实包豪斯不仅注重实际操作,那里的老师不仅是下车间的领队,在事后更要带着徒弟们再次回到学生的位置,一起对个体的感受进行理性的分析和深入的探讨。就这样,在现场中感受、到课堂中领悟,继而又回到操作中去运用。由此循环往复,渐次升华,实现吸取、咀嚼和消化才是它的完整的全过程。包豪斯总是有效地联系起教室和车间,充分发挥它们的各自侧重,对这样的双向互动从来都没有厚此薄彼。包豪斯并没有把学习和研究笼统为传说中那样,一个简单的学会,更无意于混淆师徒与师生的不同担当。
包豪斯倡导的艺术家进入工业化的规模生产,到了我们的地面儿上就水土不服了,便演绎为另一种面目:或让摊贩老板登堂入室占领教学讲坛?或变相为挂牌几间工作室,由老师带领学生为自己的店铺打工?让大学再次回到蔡元培抨击过的“重术而轻学”?
“由技入道”并非一种现成的必然,不是一钻进了雕虫小技就搭上了奔向大道的直通车。那得看现场的师傅是否还兼具有教师的能耐,能否把徒弟转换为学生,直到引领为学者。过余瞄准市场的即时见效,就会只顾产品而轻视了学生,以人为本的教育就会偏道进入邪门儿。市场中,明确地存在着应对和沟通、时机把握和让步妥协,唯有人的质量才是一个较稳定的标准。现场的经验之谈与教学的规律探讨是无法等同的。
包豪斯的老师都是大师级的人物。如果说他们都是著名的画家或设计师,那并不重要,因为那更多地属于老师个人与院子以外发生的私事?我们可以笑话“相声中歌唱得最好的”,却还是会对那些“教书中画卖得最好的和登台演出最多的”表现出由衷的赞赏。艳羡当前的市场效果是时下人的超级本领,完全忘了付钱进校门是来向老师讨教,探究学问才是学生与老师的直接关联。那些画家、歌唱家以及商业上的成功人士都可以与教学之外的明星偶像等同。他们的足迹可能为成长带来一些启发、触及一些联想,但都有别于师生之间的面对面解惑、悉心陪护。学校的课堂更侧重对学生的具体状况予以针对性互动。
包豪斯还有康定斯(VassilyKandinsky,1897—1944),他把点线面的抽象与音乐和食品的进行联系,影响至今。他让画面的再现对象都减缩为视觉元素,让教学从对实际物象的罗列中抽象出来,给学生予形式法则去应对现实的万千琐碎。而我们,至今还执迷地把写实再现当作绘画和设计专业的基础,教学的内容还是领班监工下的感性操练多于老师引导下的理性分析。课堂与作坊极端混淆。
名画家约翰内斯·伊顿(Johannes Itten,1888—1967)到了包豪斯,更是创造了现代设计基础的课程系统。那可不是眼下这种迎合格式化的官样文件。现在的名曰“课程建设”等条款句式大多水分太重,旨在应付教学评估、职称评审等自欺欺人的教育游戏。
伊顿在强调的设计教学要领,明确表述出对形态、色彩、材料、肌理的深入理解与体验,包括平面与立体形式的探讨与理解。他在教室内通过对绘画的分析,找出视觉元素在韵律和结构的形式规律。注重对学生观看方式的引导,培养他们对自然事物要有一种特殊的视觉敏感性。那样的教学瞄准的还是学生,绝对有别于教唆学生做一些短平快的手工活,如时下流行的那些能让外行热闹的展览或演出。试想一下,练习曲能上台演唱吗?同理,绘画的专业性作业也不可能招揽常人起哄。当教学的重心已经不是落实到人,而是组织一帮人来制造某些绩效产品、追求轰动围观效应的时候。教室就等同于作坊了。
伊顿设计出的二十四色相环,恰到好处地把握了绘画色彩的理性分寸,把运用色彩的学习内容真诚地控制在感性层面,而没有如其他的借道者那样,把对专业的自身研究取巧为对其它学科成果的倾心依附和彻底寄生。伊顿还十分注重启发学生的个性,把学生分为倾向精神表现的、倾向理性结构的和倾向真实再现的三种类型,予以不同的指导,真正落实因材施教。即便他离开包豪斯校园之后,伊顿也在从事艺术创作。就在继续研究中国哲学时,他还敏感地以东方传统的精神文化与西方的科学进步相结合,及时地应对物质文明所带来的危机。由此足以见出包豪斯的大师是怎样在从教中把育人化作了自己的生命形态,而不是求财谋生的职业手段。这正好对比出那些端坐麻将桌边的现任在岗的师长教员们。
在高举包豪斯大旗下,我们总会发明出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应对策略,试可有如下的对比赏析:
1.包豪斯打破了将“纯粹艺术”与“实用艺术”截然分割的陈腐落伍的教育观念。——我们便会把它变形为“低就”。进而提出极具实用性的全新教育招式。把个人体验才有的深切领悟偷换作了团队组合。让所谓的群体创造性集中在讨论市场动向,合力解读政策条文。严重混淆创造的孤独性、生产的合作性和应对的变通性。
2.包豪斯完成了在“艺术”与“工业”的鸿沟之间的架桥工作,使艺术与技术获得新的统一。——“工艺与艺术的结合”到了这儿的就被简单化为产销挂钩。学校的教学流于掌握设备熟悉工具,讲堂应有的思辨堕落成了技工培训。卖弄技术、炫耀技巧在这无情无义的群体中已经直接就被吹嘘为艺术。
3.包豪斯接受了机械作为艺术家的创造工具,并研究出大量生产的方法。要求设计师“向死的机械产品注入灵魂”。——他们志在拯救冰冷的机械,我们在机械系统芯片软件面前大胆依赖,干脆就拜倒在工具和设备的面前,直至放弃大脑。背诵软件菜单成为了教学的主打课程。
4.包豪斯认清了“技术知识”可以传授,而“创作能力”只能启发的事实。——对此我们是绝对地看了个一清二楚,所以就只捡可操作的来及时炒作。只以传授技能为己任,对工具使用法的传帮带成为了教学的核心内容。各校之间用复制、仿效和抄袭出的的传帮带东西自诩为创造和设计,相互炫耀,引导学生养成沽名钓誉的卑劣恶习。
5.包豪斯发展了现代的设计风格,为现代设计指示出正确方向。为现代设计教育立下良好的规范。——包豪斯是被后世逐渐认定,今人对此却亟不可待。我们已提速为当朝互认。工艺美术大师、国学大师、重点名校、划时代意义等名号都可以在同桌对座中当场加封,只要事前有符合潜规则的勾兑和相应的付费。
其实,包豪斯的注重实践,并不是以削弱教学的理性探讨去作为反衬条件。是那些附庸官僚的学霸们,视办学为敛财之道,全然不顾树人的千秋大业。他们之所以只关注包豪斯陈列的机床、车间、工场等实训硬件,目的在于要掩盖自己教学设备的简陋,混淆生产工具与教学设备的区别。许多所谓的包豪斯追随者,其实更像是“借刀者”,他们的博学不在“取经”而在“镀金”。他们经受住了鲁迅的嘲讽,且托“盛世”之福,家族更加兴旺,从“西仔”蝶变为“海龟”,游戏在华洋之间。他们不惜盘缠,(反正叫公费,是别人的,)执意远涉重洋,去采撷些他乡的零星碎片来为自己的装扮作时髦的花边。四处收罗些异域的词条为自己镶嵌出满口的金牙,为的是能在同胞面前哇啦哇啦地洋腔洋调,拉虎皮做大旗,既可以在所谓的学术圈内守垭口占山头。也能用 “learning by doing”之名粉饰自己低俗的教学目标,把大学教育戏为手艺活儿的传承,把学府里的教学等同为车间里的传帮带,有意不搞清楚作坊中的师徒关系与教室中的师生关系。
当学校的教学不是站在专业的高度去探讨形式规律的时候,自然会虚拟一些并无投资的甲方,蛊惑学生去怎样追风赶潮迎合市场。把铸就干将莫邪的反复锻造减缩为快捷的表面抛光;把成就韩信的所有漫长修炼扼要为只要学会从胯下钻过就行头具备。如此这般的大学生,真该退了学费直接到市面儿的公司去跟班学艺。在实践中学习,那样更可免去无聊课程的麻烦,还会躲避那些二把刀老师混淆视听的玄吹。
许多事儿就那么简单,现场的师傅在操作过程中可以对你行“无言之教”。无论是学习者还是传授者,都会更轻松更有效。有些事儿的确要高深一些,非名师、大师的指点就上不了那个坎儿。蔡元培早就认定“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教师怎么就可以照本宣科呢?课堂就怎么可以一家专断呢?教学的内容怎么可以概念化?符号化?仅仅为了落实为考卷的标准答案吗?看来这儿已经堕落成“养成资格之所”。
在这级台面儿上,对于老师,最起码的是真诚,其次才是广博后的融合、讨论中的思辨。诚然,这些都只能是智者和勇者之事,精英之事。识字的人未必读书,读书的人未必是学者。“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环视一下现在已经上了台面儿的,有几个能有如此之担当。
师傅与教师,一旦我们把他们捋顺到各居其位,学费该怎么个交法就自有道理了。现在的学费是为求实还是务虚?扎堆儿混混?父母出资请一大群人合力消解孩子们原有的鲜活个性?还是为那一纸文凭?相信社会的终审标准会不认标签而之验货品,让宝贵的青春清醒地去拜师学艺吧,找大师才能问径探道,让那些卖牌子的贩子们有摊位没顾客才是。
【编辑:赵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