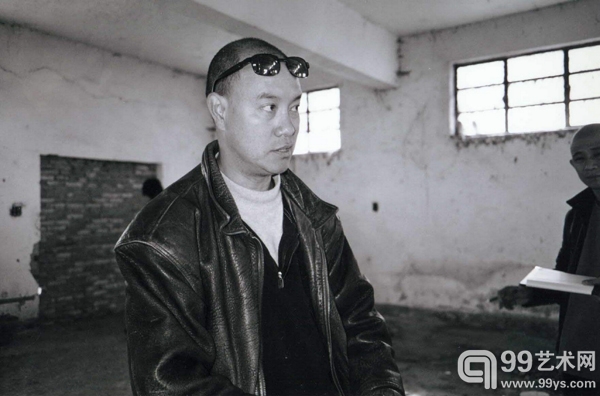
叶永青2000年创办上河创库
和丽斌(以下简称和):听说你最近正在策划一个叫 “出云南记”的展览,是缘于什么样的契机和什么样的考虑?
叶永青(以下简称叶):从90年代初一直到本世纪初,大家现在回头去看是一个小的繁荣期,一方面是在创作上出现了一大批人,另外一方面是在艺术生态上也出现了一些变化。这些在创作上出来的这批人,目前也都是很有影响力的一批人,而且通过这些艺术家也培养出了一批更年轻的艺术家,形成了昆明、大理、丽江这样一个基本的艺术生态圈。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云南开始变通为另外一种形态的当代艺术氛围,这种云南的当代艺术氛围和之前的云南艺术提供给中国当代艺术史的版本是不一样的。现在我觉得是回到以前了,因为云南这个地方是一个被外来者描述得过度的地方,像世外桃源啊、边疆啊之类的,所以云南艺术一直提供的是一种关于“边疆”的信息的东西,云南是中国政治版图上的边疆,经济上是一个国家郊区和二流城市,文化上是一个盗版城市或是说文化上提供一种异域风情,最早像徐霞客对云南的描述就是这些东西,最典型的就是艾芜写的《南行记》,当时想做这个展览也是有点想回忆他的云南情结,他是一个典型的外来主义者,他把云南、缅甸和整个东南亚一起作为边陲来描述,虽然落后,但是也焕发出一种野性,这是特殊的风光,这种风光延续出来一直到“毛”时代基本上都是这样,包括《五朵金花》、《阿诗玛》,再到之后的“云南画派”、重彩画、云南版画等都是这样的历史。但我觉得从80年代开始云南有一点(当代艺术)的线索,与有一些艺术家和他们的艺术生涯和时代有关系,但那只是一个萌芽,比如80年代包括一些对“85美术”的回应,“新具像”运动等,但并没有形成一种潮流。并且,80年代面对的整个问题不一样,80年代就是想用艺术来改变自身环境,或是想用艺术来反抗自身环境的一个背景,所以80年代只是刚刚开始,并没有形成一个大的走向。真正有了大的走向是在90年代开始的时候,主要的特征就是当时的艺术工作者真正摆脱了体制而变成了真正的艺术家,像吴文光,从他的第一个作品《流浪北京》开始,就是一个象征性的作品,还有艺术家朱发东,他把自己的身份变成一个此人出售的、很迷离的、在北京街头游走的形态,这些对整个中国来说都是具有象征性的东西,它已经超越了云南自身的东西。说是出云南,但是在那个时候也有无数的出四川、出湖北、走西口、闯关东等,这些都会成为一种地域性的东西向整个国际化的、城市化的流动。所以当时我们的展览取名为《出云南记》,但并不是有些人曲解的“走出云南”,展览名称的英文为“On Yunnan”,是指自由的云南,就是无数的出走与回归,使每个人在这样的过程中获得每个人的经历和独有的历程。就是变成一个自由的人,而不仅仅是一个“中国的艺术家”或“云南的艺术家”,而是在这种碰撞中找出属于“我的世界”的一个过程。云南产生了一大批迄今为止比较有影响力的艺术家,像何云昌、曾浩、刘建华,还有一些一直在云南的像曾晓峰、罗旭、李季、唐志冈等,这也是我比较感兴趣的方面,我喜欢通过一个展览来讨论这些问题,这里面有些意味。虽然我以前也在云南待过,也做过很多展览,但是我觉得有些关于云南的话还有两个情节没有说完,一个是关于创库,一个是关于讨论云南的所谓“地方性”。大家都在讨论云南,但是对于云南的讨论我觉得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比较尴尬的局面,所有关于云南的讨论实际上是每个人都在从自己的心灵深处放一个牢笼把自己关起来。其实整个90年代的当代艺术就是一个“不断出走的艺术”或是叫一种“离家的艺术”。这是个整体走向,并不是有些为了捍卫某种尊严也好,什么也好的批评家一直在强调的“独立性”。我觉得从古至今,云南没有独立性可言,云南整个少数民族的文化和在这个地域所生长出来的东西都一直受惠于汉文化,也一直从属于汉文化,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才慢慢的形成自己的品质和有意思的东西,而不是中心与边缘的冲突,这是一个假命题。所以我们是想通过一个这样的展览和实证来思考这些问题。
和:从1999年开始的上河会馆,再到创库,至今有十年了,到今天还一直被各种媒体、艺术家在反复地讨论,你作为创办人,想请你再具体地谈一谈今天的创库,包括未来昆明的艺术社区和城市之间的话题。
叶:昆明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故乡或是说是一个这一辈子都走不出去的城市,一直是来来往往的。其实当时做会馆,做创库也可以说是一种偶然的经历,就是为了改变当时不喜欢的生活方式。故乡是一个你可以一厢情愿描绘地无比的美好的地方,但当你回到故乡的现实里面就会发现这和你怀念的是不一样的,这个所谓的故乡太贫瘠,是让你无法落地的。当时我做会馆,包括之后的创库就是想对这样一种已经安排好的生活的反抗,不愿意就位,想创造一种自己喜欢的模式。现在回过头来看我当时回到昆明做会馆、做创库的这些经历,对我来说还是有收获的。我原来只是一个艺术家,因为这些经历,我做了很多超出艺术家之外的角色,像老板啊,策展人啊,甚至去帮艺术家推销,卖出他们的作品,总的来说,我当时变了一个身份,就是一个叫卖者,一个推销员,一个推广者,推广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不停地在叫卖一种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和艺术家的价值有关系。艺术家的角色是什么样的?是在工作室里画画,画两张他要卖的作品?不是这样的,艺术家是要有创造力、想象力的,他是能够看到社会的可能性的人,但是今天的艺术家已经被压缩、萎缩到很渺小,已经丧失了很多东西,变成了和工匠差不多的角色,已不太关心这个社会;相反,一些开发商和商人还有一些艺术家的品质,当然他们需要牟利,他们非常讲回报,但是很多艺术家反而更像商人,像那种小商人,反而商人却在做一些接近艺术家的思考:第一,他要了解人的欲望,所有人的欲望能够带给自己一些可能性,这原来是艺术家要想的问题;第二,商人每天都在想如何让自己看得更远一些,这也应该是艺术家想的。但是现在的艺术家不太想这些问题,或是说已经没有能力想这些问题了,他们想的东西都很可怜,这个社会把艺术家挤压到一个非常小的空间里面。这是我们通过几轮变化看出来的这个社会的格局和分工上的东西。虽然上河会馆、创库创造了中国的很多第一,比如说是中国第一家艺术家自营的空间;第一家主题性社区,创库是始作俑者,这些都是第一次,也确实在那个时候引人注目,这是事实。但今天也确实应该承认,这些东西都全部失落了,全部都是过去了,今天的创库已经变成了一个野生动物保护区。艺术家如果没有了想象力和创造力,不能够把自己的生活方式推广到自己的人群之外的话,他对于这个社会就和一般的装修工人是没什么区别的,他们就是自己做自己的事情、自己挣自己的钱,就是这样一个人群而已,对我来说没有意思。比如说创库这个概念,我们现在还守着它就是一个苦局,但创库对我来说就是一些想法,一些创意,它不是一个地方。张晓刚和我是合作者,我们一起创办了上河车间,当时我们谈得很清楚,我不想做一个卖作品的画廊,我想做的是一个非营利的空间,一个功能性很模糊的空间。后来因为家庭的很多变化我们要去北京生活,张晓刚说他不相信我舍得放弃创库这个地方,因为当时过得很有意思,但是对我来说没有什么舍不得放弃的东西,因为我很喜欢的一句话是老子的“为而不有”,我的理解就是说这些东西都不是物质的东西,是一个关于想法的东西,就是你有这个想法你就要去实现它,但并不是说你有了这些东西之后你就要去守着它,没有必要。所以对我来说创库是可以移动的,可以携带的,所有有价值的东西都是可以携带的,都可以在不同的地方落地和重生,无非就是要有一些有创意的人群,有另外一些身上带着这种气息的人群,让他们来创造,在不同的地方落脚做出一个新的东西。创库只是创造了一种模式,这种模式被复制,像北京的798,还有上海、成都、重庆等等遍地开花,这种做法在别的城市都得到了政府的支持,一些基本的模式我们都还是可以从创库身上找到影子:租赁式的、自我营造的艺术空间和招商引资的模式,还有艺术家的工作室等等。这些基本的模式每个社区都有,但这些模式从法律上来讲都是脆弱的,都是没有办法长远,它不具备一个品牌效应,不是持续性的,不是常规性的,也不是公开和透明性的,不是公共性的,中国未来的一些艺术社区一定要朝着我刚才说的这些方面发展。现在北京的艺术区,所有的房子都是和二房东租的,我们的创库虽然是和工厂的大房东租的,但仍然还是租的。虽然我现在离开昆明很多年了,但我仍然没有放弃关于艺术社区的一些思考和尝试,当然也一直在做一些工作,可以小小的透露一下,还是有一些进展。这种思考我觉得是基于我们原来做过创库的思考,我更多的是看到我们以前做艺术社区模式的缺失和不足,以及一些遗憾的地方。我一直在想,如果将来我们还有机会,一定要做一个新的艺术社区,肯定不能再走创库的模式,而且创库的这些东西恰恰是我们要抛弃掉的一些东西。现在不管是对昆明的政府还是对一些开发商,我一直在表达我对艺术社区的一种期望,就是如果历史再给我一次机会的话,我们一定会再创造一个第一。这会是一个全新的模式,不是草场地模式,不是宋庄模式,不是798模式,不是莫干山模式,因为这些模式在我看来都是一个模式,我们要谋一个另外的局。这几年我大概做的事情就是劝说包括政府,对文化产业感兴趣的发展商和一些团体,不管是云南的还是云南以外的,只要想在昆明做这种变局的,我都给他们指了路,让他们去蓝顶,去798等做调研,做调研的目的不是去模仿和拷贝这些艺术社区,而是回来思考在这些基础之上如何能够在昆明的现有环境下着手,在政策上、制度上、地域上、规模上和形态上如何来做出一个新的艺术社区,第一,这个艺术社区要聚集最好的当代艺术资源,当代艺术在云南发展了也表示疑问,就是凭什么要把这么好的地留给艺术家?我和他讲道理,昆明能够影响昆明之外的资源是稀缺的,几乎没有;在历史上,昆明影响中国的事很少,昆明是一个接受外来资源的地方,目前来说,在当中国代艺术领域里面有一些尖端的、有影响力的人或事能够聚集在这样一个小小的聚集点,云南的这种资源要抓住,而且这种资源是稀缺资源,是很容易被这个社会消灭掉的。简单地说,如果这个资源形成了几个人,聚集起来就是带动性的资源;但如果张晓刚买了世博园,我买了高天流云,大毛买了海埂的房子,唐志冈买了翠湖边的房子,那这种资源很快就会被房地产消灭了,就是说这些资源如果没有被聚集起来,每个人单独使用这个资源就是毫无意义的。这种资源是要聚集起来做公共的事情。艺术家的成功要被政府和社会承认,但这种成功是要用来回馈社会的,所以政府需要支持。第二,对于那些在创作中的艺术家要找一个模式与他们合作,还需要扶植一些更年轻、充满创意的人群。他们没有钱,需要多大程度的帮助,应该寻求一个模式来扶植。这才是一个复合式的东西。我们不会再去做像创库这样专门的艺术社区,这种实践是包括了全中国艺术社区的实践,纯粹的艺术社区都是危险的,它就像一个菜包子。我们要做的是一个符合社会的艺术社区,就是要和这个城市共同分享的艺术社区,艺术家只是这个社区里面的一颗辣椒或是一颗糖,他味道有些怪,但这个社区需要这个东西。这个社区是在整个生活里面形成的,也许现在这些会变成美术馆、工作室,但将来会形成我们想要的东西。现在包括昆明都在做各种社区的包装,包括房地产商也在利用艺术家来做社区的改造,我觉得这都是好事情,能够带着大家一起玩这个游戏,而且也能证明艺术的影响力。我们要谋一个有未来的东西,而不要再去纠缠像租金这样的小事情。有一段时间对创库的讨论,媒体他们来找我,我都没谈,因为那个时候谈是自取其辱。因为媒体是你好的时候来捧你,坏的时候来打击你的。创库现在给大家感受到的气氛是沮丧的,不是别人要羞辱你,而是自己本身就是这样一个状态,原来创库是引领这个社会并给这个社会带来兴奋的,但现在是很沮丧的,这是谁都改变不了的事实,你不能说你还在坚守就会发生什么,这被媒体描绘出来会是很可笑的。我觉得艺术家这个群体还是要问一下自己能够给社会带来什么,人生的意义不是去索取东西,你不能总去抱怨这个社会没给你什么。艺术家应该很感恩了,这些年社会的发展让艺术家成长得很快,但艺术家回馈给社会的还是不够,我觉得这个社会还是很公平的,当你给社会的东西不够,那只会是自取其辱,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道理。
艺术家如果有一些想法,但是自己想不清楚的话,别人就算是想来帮助你也是在羞辱你。什么是我们要的?不是说这个社会不需要艺术,这个社会需要艺术,艺术家应该向这个社会要什么?艺术家能给这个社会什么?这些都要谈得清楚,才够有意义,我觉得现在我们还没有这些东西,我为什么要办创库的展览,其实就是在回答这些问题。做一个艺术社区,或是做艺术这单事情,要明确三点:第一,谁出钱;第二,谁决定;第三,谁受益。我们要回答这三个问题,艺术才能够达到公共性,如果我们自己都回答不清楚的话,社会也是不会帮你回答这些问题的,艺术的公共性就是这三个问题组成的。那艺术区呢?你要明白什么叫艺术区,艺术区是什么?第一,艺术区是提供给这个城市原来没有过的生活空间,这种空间能够帮助这个城市实现城市化。今天的城市都在转型,像昆明这样的城市都在想慢慢地变为一个大型城市,这种大型城市是以什么作为标准的呢?是以制造业和工业的衰退,城市的功能变为一个娱乐机器,艺术是在这里面的一个最重要的引领性行业。第二,艺术区所能够提供的场所是这个城市原来没有的文化设施,比如像美术馆、博物馆以及各种各样的剧场等等,这些空间是这个城市原来不具有的空间。第三,延长这个城市的夜生活,延长这个城市的营业时间。第四,让这个城市拥有这种新的生活的功能和新的生活的人群,包括艺术家的就业等,提供了这个城市的安全性和扶贫。这些是艺术社区能够提供给这个社会的东西,要先去考虑这些,而不是100平米或200平米的问题,这种问题纠缠下去永远都不会清楚,在这样的情况下,别人想帮助你,提出来的所有方案都是在侮辱你,他不是在故意羞辱你,而是在不了解的情况下羞辱了你,他会觉得艺术家是很好打发的,他就是一个私人给你一个空间,让你像只老鼠一样的活着,在里面画画画,不是这样的。
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