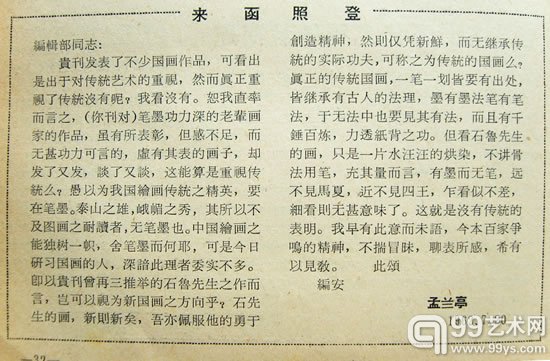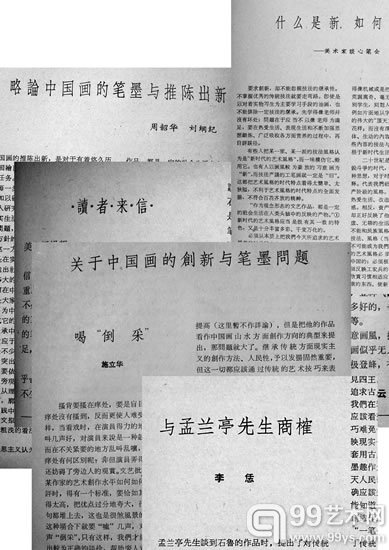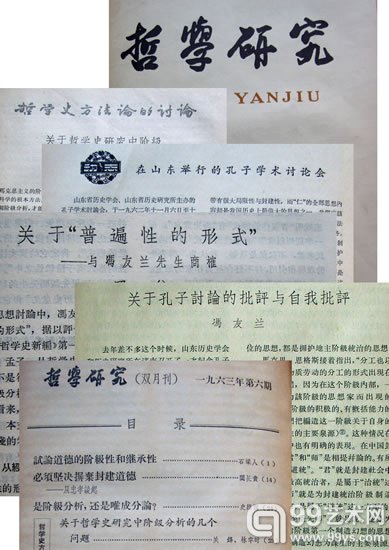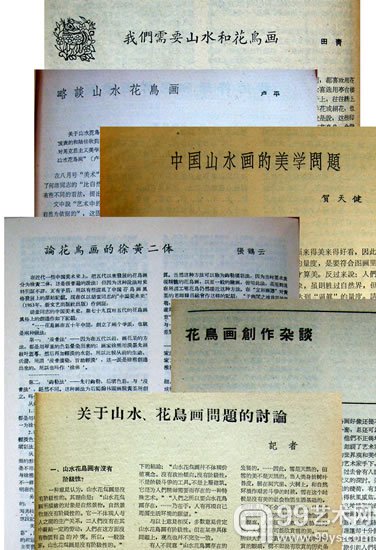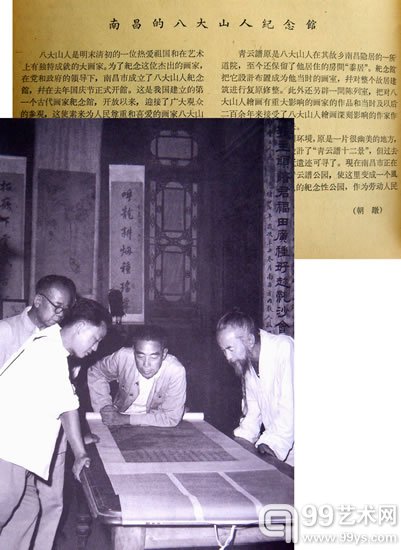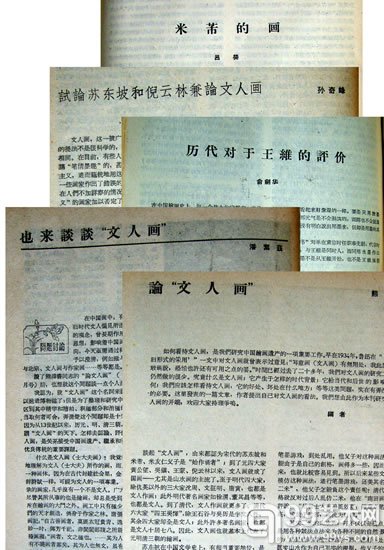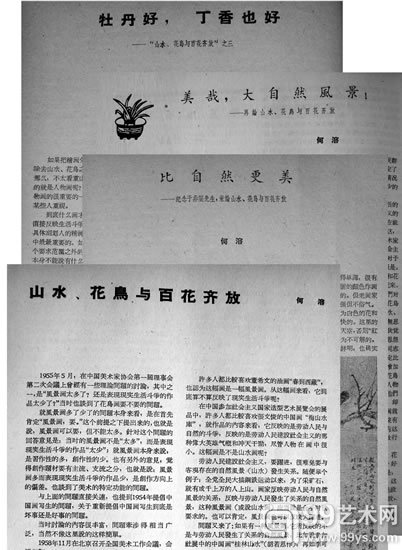内容提要:20世纪60年代初期,由对石鲁批判所引发的“中国画的创新与笔墨问题”论战主要涉及笔墨、六法与中国画评价标准等问题,与此同时,出现了对于山水、花鸟画的讨论热潮,为“封建的”、“形式主义的”文人画家举办的展览,尤其对于“文人画”鲜有的深入系统的讨论,以及美术院校中国画教学调整等一系列回归传统的现象,这与新中国伊始文艺界在“二为方针”指导下所进行的“中国画改造运动”原则大相径庭,中国画、文人画不仅可能免于被改造的命运,甚至有被提倡的倾向。这股思潮背后的历史根由是什么?讨论涉及哪些关键问题?其对中国画发展有何意义?基于上述思考,本文尝试性地在完全使用原始资料的基础上,展开对这一时期不同历史事件、不同学术观点的梳理与研究,旨在最大限度地还原特定历史语境,探究这一现象背后的历史动因及其深远影响。
关键词:20世纪60年代初 “文艺八条” 中国画论争 传统 笔墨 文人画
一、中国画的创新与笔墨问题之争
1962年《美术》杂志第4期刊登了一篇署名为孟兰亭(化名)的来信,这封信实际上是由美协机关刊物《美术》杂志社精心策划的,目的在通过对石鲁作品的批评,挑起论争,进而支持中国画的革新探索。孟文认为《美术》杂志社发表了不少国画作品,然而却没有真正重视中国画的传统。在孟看来,我国绘画传统的精英,要在笔墨。“泰山之雄,峨眉之秀,其所以不及图画之耐读者,无笔墨也。中国绘画之能独树一帜,舍笔墨而何焉……”“真正的传统国画,一笔一画皆要有出处,皆继承有古人的法理,墨有墨法笔有笔法……”基于此,他认为,石鲁的画“只是水汪汪的烘染,不讲古法用笔,充其量而言,有墨而无笔,远不见马夏,近不见四王,……这就是没有传统的表明。”〔1〕因此,不能算是中国画。来信一经发表就引起广泛关注,《美术》杂志社随即收到50余封相关文章。20世纪60年代初关于“中国画的创新与笔墨问题”的论争也就此拉开了序幕……
20世纪50年代末期,以石鲁、赵望云为代表的“长安画派”〔2〕开始引起美术界的注意。1961年,“长安画派”在北京举办了“西安美协中国画教研室习作展览会”,并在全国美协的安排下先后到上海、南京、杭州等地巡回展出,其显著的“地域性”风格特征,以及主张上的地区性画派概念〔3〕,令人耳目一新。西安画家也因“发现了新的表现角度”、“开拓了风景画的道路”,表现了新时期“人与自然的关系”等原因获得了广泛的好评。〔4〕而“长安画派”的出现与石鲁有很大的关系,美术史学者郎绍君认为,“没有石鲁就没有长安画派。他的思想主张、艺术见解,创造力和作品本身,都表明他在长安画派中的支柱和核心地位。”〔5〕正因为此,当石鲁的一系列作品〔6〕获得巨大成功之后,石鲁越来越受到关注〔7〕,进而因对他作品所展开的不同评价引发关于中国画论战也就顺理成章。对孟兰亭文章进行分析不难发现,首先,孟文强调重视传统艺术,尤其重视中国画的“笔墨”;同时,由对石鲁作品“不讲古法用笔”,“有墨而无笔”的评价进而引申出如何重视传统、表现笔墨的问题。实际上,在新中国伊始所展开的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中国画改造”的语境中,这样一种观点是被彻底否定的,这自然与当时所强调的以“二为”方针为准绳的艺术政策有关,而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所体现出来的“艺术工具论”观点一直占据绝对话语权地位。在这样的语境下,有没有传统,有没有笔墨似乎并不重要,正如王逊在1954年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古人的笔墨技法不仅离开了现实,而且阻碍我们接近真实的自然景物,那种“单纯以笔墨为评判艺术价值的至上标准的时代已经过去了”〔8〕。而诸如这种艺术工具论的观点,直至1956年“双百方针”出台后才稍有所松动〔9〕。1962年“文艺八条”的颁布,似乎又将这一讨论引向深入。
实际上,如果我们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关于中国画及笔墨问题的探讨做一个简单梳理的话,便不难发现,新中国初期王逊与邱石冥为双方代表的“关于国画创作与接收遗产”的讨论,主要是针对传统国画能不能表现今天的现实生活以及要不要接收遗产(包括笔墨)等问题所进行的探讨〔10〕;1956年,由对艾青《谈中国画》一文的批判以及随即发生的有关“何为中国画特征的讨论”〔11〕,则在某种意义上着眼于中国画自身,逐渐向着中国画本体问题靠拢;而这场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由“孟兰亭”引发的论争则是在上述基础上进一步深入探讨什么是“笔墨”,如何表现“笔墨”的问题了。正如美术评论家郁风在“长安画派”研讨会上相当震惊地发言:“可以说(石鲁等人的作品)是一个炸弹,炸开了山……大家还记得1956年第二届中国画展上,李斛、宗其香同志的作品曾引起过争论,那是还争论着算不算国画的问题。从这次展览就可看出国画的发展五年来已经有了多大的不同。”〔12〕换言之,对于“笔墨”的探讨,从王逊到孟兰亭,从上个世纪50年代之初到60年代伊始,似乎存在着一条由大致倾向于“否定”、“不要”到“肯定”、“要”,再到“如何要”的逐步深入的发展过程。尽管这只是一个大的轮廓线,而关于中国画本体、关于“笔墨”问题的不同观点之间的争论实际上也一直贯穿于整个新中国十七年,〔13〕但这仍在某种意义上反映出中国画在新中国十七年中的一个流变。
孟文一经发表,就引来了极大的关注,〔14〕《美术》杂志也专辟“关于中国画的创新与笔墨问题”栏目继续讨论。来文各抒己见,有赞同孟文的,也有支持石鲁的,进而引申出对传统绘画评判标准的理解等一系列问题……大致到1963年《美术》杂志第6期发表的王朝闻《探索再探索——石鲁画集序》后,才基本上结束了讨论(这时阶级斗争又重新被强调,预示着“文革”的来临)。在来信中,支持孟兰亭观点的有施立华和余云等,施立华认为我们今天评论中国画的作品时,谢赫提出的“六法”应该仍是不移的“金科玉律”,“中国画”应该用传统的技巧来表现,因此,石鲁的作品虽然是值得肯定的,但以中国画的眼光来看石鲁的作品还差了一段距离,甚至有部分作品还不能算属于中国画的范畴。〔15〕余云也认为,石鲁的画虽则新鲜,勇于创造,但继承传统的东西却不多,所画的画也不美观。〔16〕正如上文所言,新中国伊始,只要能表现“生活如何之深”、“思想内容如何之高”就可以说合乎当时的艺术标准了,而对于是否有笔墨的问题,则是无所谓的。然而此时,孟兰亭、施立华等正好把当时的论断来了个完全颠倒,尽管其中关于“一笔一画皆要有出处”、“‘六法’仍然是不移的金科玉律”等观点的提出本身有些偏激,但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无疑可以说是重新审视传统思潮在中国画领域中的一个反映,这一思潮不仅对当时同时也对新时期以来的中国画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而在支持石鲁的来信中,大致包含两种观点,其一,正好与上述论断相反,认为石鲁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很好的运用了中国画的传统技法和形式。他的作品在中国画传统的脉络上,远可以追溯到石涛、金冬心,近可承接黄宾虹、齐白石,是有着清晰的传统印迹的。并且“受到了宋元之后的文人画传统的启发,同时又在努力吸收八大、扬州八怪、吴昌硕、齐白石等大家的花鸟画的优点……”〔17〕“如《转战陕北》等作品,无论用笔用墨都可以看出作者重视骨法用笔……”(王其元)从精神上看,不但有“荆关的雄强”、“马夏的苍劲”、“二石的奇宕”还有“黄宾虹的葱郁”(罗尗子)……他的作品“并非只是用中国宣纸、毛笔、墨来作画,而是从立意、构思到表现技法,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中国画的传统。”(安华)〔18〕而石鲁的泼墨和积墨,也力求作到“墨中见笔”……其二,赞同石鲁在精神层面、创新方面以及反映时代感情等领域进行的探索〔19〕。他们大多认为笔墨确实是构成中国画特性的一个显著特点。但是“笔墨”更多的只是一种技巧、技法。〔20〕而对于中国画的笔墨以及中国画传统的认识来说,只有从艺术对现实的反映出发去认识才可能达到对中国画的笔墨及其传统精华的正确认识,从而也才可能在实践上真正作到推陈出新〔21〕。基于此,周韶华、刘纲纪认为,孟文中谈到的“出处”问题,也应该有两个方面,一、古人;二、现实。“否认古人是笔墨的‘出处’之一是错误的,否认这个‘出处’也就是否认了遗产的继承……”但“只看到这个‘出处’而看不到另一个‘出处’,即看不到现实这个‘出处’是更加错误的。”因为“古人这个‘出处’只是笔墨的流,只有现实这一‘出处’才是笔墨的源。”而“中国画在笔墨上……的全部意义、价值只在于它完美地反映了现实。离开了对现实的反映去谈论中国画的笔墨……除了把笔墨神秘化、抽象化……之外,不会有其它结果。”〔22〕历史上每一个时代的大画家无不是反映了自己时代的现实生活,体现了自己时代审美理想〔23〕。而石鲁的画由于是可以表现时代精神,反映现实生活以及表达思想感情的,所以其价值是值得肯定与赞扬的……在论战中,多数来稿倾向于“笔墨”在传统绘画中虽很重要,但他终究是艺术表现的一种手段,并非艺术批评的唯一标准。同样,“六法”虽然是宝贵的传统文化但不是万古不移的,而是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的。〔24〕
就上述双方的论点进行分析,不难发现,孟兰亭文章的支持者大都从中国画传统的立场出发,强调笔墨语言,强调“六法”,试图努力在当时忽视或割裂传统的语境中为中国画传统的延续与发展寻求出路;而对孟文持否定态度的文章则认为石鲁作品不仅与现实生活与群众的感情相联系,反应了革命现实,强调了“现实生活”同时也强调了“中国画传统”。实际上,这也正是新中国十七年中国画领域里所面临的两个最为基本的问题。一方面,在大的历史语境下,关于艺术为工农兵服务、反映现实生活的功能性、工具论在新中国十七年中始终处于主导性的地位;而另一方面,关于中国画本体问题的探讨从未中断过,而是随着政策、形势等变化在逐步的起伏调整中。此时,论战双方无论哪一方,其实都并不反对“笔墨”、“六法”在中国画中的重要性,只是程度不同而已,这与之前的讨论显然有着本质的区别。毋容置疑,这样的调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艺政策的宽松度,而1950年代末1960年代初由于国际国内等原因,在文艺界,政治压力相较而言似乎降到十七年来的最低点(下文详述),这就给传统尤其是中国画传统的自主性发展带来了较大的空间……且不论讨论的程度如何,单从讨论的对象看便足以证明,对于传统的认识在不断的深化,所谓“中国画创新与笔墨问题”之争,其实质则表现为我们如何运用传统,如何运用笔墨来“创新”国画艺术。此次讨论甚至对新时期中国画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5〕值得强调的是,与此相呼应,曾经被轻视甚至忽视的山水、花鸟画问题又重新进入了人们的视野,〔26〕而人们对一度被否定和批评的“文人画”〔27〕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
正如上文提到的那样,新中国十七年每一次文艺思潮的出现都在某种意义上取决于文艺政策的变化。1956年,“双百方针”的出台是新中国文艺政策的一次重大调整,在“去苏联化模式”、“走中国式道路”的大背景下,“民族化”思潮正式兴起,文艺界则在对前一阶段所存在的“民族虚无主义”批判的同时,转向了对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视。正是在这样一种语境下,中国画的命运获得了历史性的转机。然而,“双百方针”之后的“反右”、“大跃进”、“拔白旗”等极左运动,使得这一刚刚获得的宽松氛围再度收紧。而中苏关系的逐步恶化直至彻底破裂等一系列因素,在对1960年代初期国内政治、经济、文化造成极大冲击的同时,更进一步加剧了本已存在的“民族/国际”二元对立的紧张关系,使得对民族传统文化的诉求变得尤为突出……正是出于对这一系列现象的深入反思,中央在各个领域采取措施来挽救局面,在文艺界则出台了“文艺八条”,试图重新回到那种相对宽松的有利于文艺创作的“双百时期”。当然,对“民族性”的强调更多是在中外对比之下对“身份”问题的一种定位,所强调的更多是对本土文化、民间文化的重视,并不意味着对中国画传统尤其是文人画传统的倡导,但这样的一种语境至少给传统文化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了契机。这种现象的出现,不仅与“文艺八条”的出台密切关联,在政策上还与新中国十七年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的重新界定直接相关。
“文艺八条”〔28〕的出台可视为20世纪60年代文艺政策的一次重要调整,即“一、进一步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二、努力提高创作质量;三、批判地继承民族遗产和吸收外国文化;四、正确地开展文艺批评;五、保证创作时间,注意劳逸结合;六、培养优秀人材,奖励优秀人材;七、加强团结,继续改造;八、改进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文艺八条》在某种意义上是对“双百方针”的延续与深化,〔29〕其中心内容是调整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以及贯彻落实科学和文艺工作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30〕。我们对此间的科研、教育等政策进行考察不难发现,无论是聂荣臻的《请示报告》中所提出的“一定要鼓励各种不同学派、不同学术见解和对于具体学术工作的不同主张,自由探讨,自由竞赛”等问题,还是《高教六十条》中规定的“在自然科学中,必须提倡不同的学派和不同的学术见解,自由探讨,自由发展。在哲学、社会科学中……必须批判地继承历史文化遗产,吸取其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31〕都明显的带有“双百方针”的“色彩”。而根据《文艺八条》主张,一方面在创作实践中允许“少谈革命政治问题”题材的出现,另一方面则允许创作“偏重传统”的受欢迎的作品,并且同时在艺术风格技法上允许重新采用传统艺术形式……实质上,这样的一种对待传统的态度恰恰反应了2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期整个文学艺术界所兴起的一种“重新审视传统”的思潮。与此同时,思想界则出现了关于“儒家文化全面再评价”〔32〕的热潮,虽然关于儒家文化的问题在“双百方针”期间就有所提及,但其作为一种较为强劲的势头则是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33〕,而1962年关于中国历史的种种非马克思主义的讨论,则进一步推动了对儒家文化的积极的、肯定性的评价……〔34〕
正如上文已经论述过的那样,关于十七年“中国画改造”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属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在美术界的一种体现,而无论是在新中国伊始的“第一次文代会”期间,还是在“双百”抑或是20世纪60年代初期,十七年中每次文艺政策的调整实质上都与知识分子的“定性”、“定位”(界定他们的阶级属性,确认他们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地位)相伴随,而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问题的“不确定性”则无疑成为新中国十七年党对知识分子政策不断反复的根本原因。新中国伊始,基本上延续了《讲话》中对知识分子的定义,即知识分子与“城市小资产阶级”相一致。因此,知识分子虽然存在着经过改造后变为无产阶级的可能性,但却不属于无产阶级,因而对其进行思想改造是完全必要的。这种状况在1956年“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出现了一些变化,在会上周恩来宣布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35〕这一定性在1957年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得到了肯定。但是,随着“反右运动”以及“反右斗争的严重扩大化”,1958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又宣布我国有“两个剥削阶级和两个劳动阶级”,知识分子就被明确地归入“资产阶级、剥削阶级”,受到批判、斗争……随着“反右”扩大化以及“大跃进”运动不良后果的逐步暴露,对知识分子的“定性”在半年内再一次出现了“反复”〔36〕。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在1962年的“广州会议”上,周恩来关于《论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37〕,重新肯定了他在1956年提出的“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论断。〔38〕随即,陈毅在讲话中,宣布给广大知识分子“脱帽加冕”,即脱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帽,加上“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之冕,并郑重地向与会人员行了“脱帽礼”。“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结论,可以说是对知识分子的作用、贡献以及政治思想上的充分肯定。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社会地位、政治地位的确认,无疑是知识分子政策能否真正得到调整的基础,而对知识分子的肯定不仅对于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进而展开“百家争鸣”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也使得“百花齐放”成为可能……
编辑:黄亚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