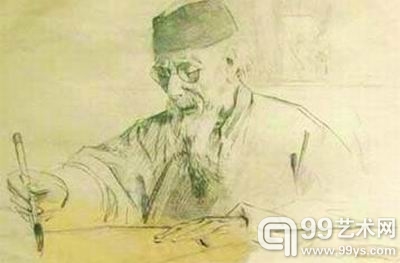
马克西莫夫速写作品《齐白石作画》
毕业“得天下英才而教之”
到了最后一年,每个人都要集中精力完成毕业创作。詹建俊说,“苏联的毕业创作在整个学习中的位置非常重,学习好还是学习坏、这个学生有没有才能几乎全靠毕业创作来判断,因此,一定需要这样一个有分量的题材。我们的毕业创作很少有一米以内的。有画长江大桥、垦荒、登山、朝鲜战争、地下斗争等等,都属于‘重大题材’”。
从五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主题性创作是主流“风景、静物、肖像不够重视,这也是社会的一种不成文的规定,谁画这个谁没出息。那时候艾中信先生就画风景,不善于画人物,因此领导对董希文就特别重视,一个《开国大典》,一举成名。”靳尚谊说。
谌北新回忆确定题材时马克西莫夫的“把关”。侯一民画地下工作者,马克西莫夫问他,“你当过地下工作者?”侯一民说“我就是地下工作者啊!”马克西莫夫说,行,因为他有生活;秦征画的《家》,是一个妇女回到战争后的家中,家徒四壁,一片狼藉。马克西莫夫说:“你成天在画布前能把形象弄出来?你得出去,到京郊,到农村去找形象,你光用嘴说不行。”
“马训班”翻译佟景韩印象很深刻的是,有一个学员画了一幅和创作有关的雪景习作,马克西莫夫就亲自去他写生的地方,让学员和司机做姿势,他看看雪景色彩、反光的关系等等。“有条件尽可能去,没有条件他就看学员的一大堆素材,斟酌构图,一丝不苟。我们的教授是否都能做到这一步?”
若干年后,在中央美院求学的陈丹青听老师冯法祀谈起《刘胡兰》的创作,冯法祀指着画面中铡刀下的血迹,“我专门杀了一只鸡,对着鸡血当场写生啊”。
1957年初夏,“马训班”毕业作品展在中央美院大礼堂举行,一下子出现了这么一批反映现实社会生活的绘画,盛况空前。马克西莫夫指导下的中国年轻油画家作品让人耳目一新。佟景韩记得,在礼堂门口举行的仪式上,吴作人讲话说:“得天下英才而教之乃人生一乐也。”他把这句话翻译给马克西莫夫,马克西莫夫听了很高兴。
这一幕留下的一个镜头是:在冯法祀的巨幅油画《刘胡兰》前面,正中间坐着朱德总司令和老师马克西莫夫,两边顺次坐着江丰、吴作人以及中央美院的老师们,后排站着“马训班”全体学生。这个瞬间保留在当年6月9日的《人民日报》上。
1957年初夏,马克西莫夫与靳尚谊、魏传义等十几个人到武汉、四川旅行写生,重庆是最后一站,马克西莫夫从这里飞往昆明然后经北京回国。“起飞前,老师深怀惜别之情和我们每个人合了影,一再握手告别。”靳尚谊回忆道“时间长了,感情在悄悄增长……在驱车回城的路上大家一言不发,谁也没能想到这竟是一场永远的诀别。”
临别前,魏传义记得马克西莫夫最后对他们说,“最重要的还是你们今后要互相帮助,互相要多提出一些意见,只有这样才能成长起来。”“他接着说,不管你以后的作品多么好,总应该感觉不是你所理想的那样,不要满足,要精益求精……画家是个个不同的,每个人都应该找到自己的道路。”
离开中国的马克西莫夫,没有看到他的学生们在接下来波诡云谲的政治风浪中的命运,他可能想不到,“马训班”结束后不久,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右”运动席卷了美术界,江丰被定性为“反党集团”,“马训班”的冯法祀、俞云阶、秦征等五个成员也被错划成了右派;他也不会想到,在日后的“文革”中,画了《冼星海在陕北》的于长拱自杀了,画了《刘少奇同志与安源矿工》的侯一民会因为这幅画而饱受折磨;他可能更想象不到,在“文革”中画多了“红光亮”画面的靳尚谊曾因此一度辨色能力受损。
之后,中苏关系恶化,曾经象征两国友谊的“马训班”也不再为人提起。靳尚谊的毕业创作《登上慕士塔格峰》一度由中央美院陈列馆保存。1969年,中苏爆发珍宝岛事件,陈列馆觉得再保留反映中苏联合登山的画不合适,就把它折叠着还给靳尚谊,结果经过一番折叠,颜色掉了,画也毁了。
翻译佟景韩了解到的是,训练班本来是要办下去的,据说要来的是涅普林采夫。1958年夏天,佟景韩和文化部、学校的有关人员都到机场去接机,可是人没有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