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3年《三峡大移民》(200×800cm);

2004年,《三峡新移民》(300×1000c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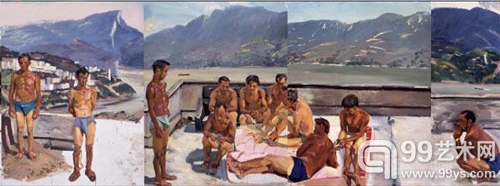
2005年《温床》(260×1000cm)
整整70年前,寓居美国的弗洛姆这样描绘了他身陷其中的现代化都市:
车水马龙的大都市(生活在这种城市里的人都有失落感)、高耸入云的高楼大厦、震耳欲聋的无线电广播、一日三变的新闻报道(人们搞不清究竟哪种报道是真实的)、眼花缭乱的各种演出(……)、跳跃有致的爵士音乐、政党间的明争暗斗、国家之间的战争和地区冲突、各种类型的恐怖活动……所有这一切,都是某种星座的表现,说明了人正在面临着一股自己根本无法控制的力量,与这股力量相比,人只是一粒尘埃罢了。[1]
这是一位现代城市的游离者对城市经验的诉说:声光电俱全,资讯铺天盖地,繁华与迷乱并存,亢奋与失落共在。读之,令人有可能想起一幅未来派油画,名叫《城市的崛起》。画家波丘尼结合立体主义的结构和新印象派的色彩,编织了与运动和速度同步的旋律,以此为不断扩张的现代城市演绎出一幅壮观:光的能量撞击着物体,奔马所向披靡,驭夫纷纷坠地……浪漫派厌倦工业的喧嚣和城市的繁乱,心向田园,梦萦古堡,未来派却一心赞美机器的轰鸣和城市现代化的“伟大活力”。波丘尼说:“古旧的墙壁和宫殿令我作呕。我希望新事物、富于含意的事物、强有力的事物。”[2]他的作品给予“劳动、光线和运动的伟大综合”[3]以直观的呈现,而这正是其将工业文明系于城市的梦想。可是,当观众们看到,画中那些紧攥缰绳、奋力撑持的人们,最后像多米诺骨牌似的一个接一个倒下去,又在扬尘和光雾中灰飞烟灭时,是否会突然醒悟,人,原来不过是城市崛起的代价。
在未来派的经验中,城市是一部宏大叙事的乐章。其中没有琐事,没有卑微的命运和庸常的悲欢,只有史诗般的整体的恢弘,磅礴、壮丽,如洪流涌来,如车轮碾过。但与此同时,城中的芸芸众生,不过是被种种有名的或匿名的权势所玩弄的数字,就像今日中国的煤老板们始终不肯一次性报告完毕的矿难人数一样。在这个充满欲望、雄心与繁殖力的人类空间中,人,反而是被抽调了生命的“能指”,永远不会与其“所指”相遇。其结果,城市本身也遭遇了被能指化的命运——有符号而无姓名,有阵列而无躯体,有气势而无质感——这样,未来主义怀揣朝向未来世界的激动,却不知不觉玩起了穿越,从现代都市蓦然回到法老的宫殿和墓地,变成了古埃及的概念写实主义,只不过是在为其理想中的城市概念提供热闹的图解。
其实,未来派不仅有向后穿越的法力,也有向前穿越的功夫。凡是对今日中国城市(此指中国大陆的城市,下同)——不论大中小——有一定观感的人,大约容易在他们的中国当代城市印象和波丘尼的画面之间找到共鸣点。只要涉足这些城市,人们心中既有的关于城市的静态概念就不免被一种日新月异的动势所改变。这时,如果他们想为自己的观感给出一个命名,除了用“城市的崛起”或“崛起的城市”,还真找不出更合适的词句。
编辑:李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