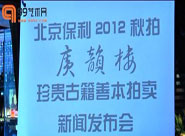格林伯格的“退却”:从社会主义到托洛茨基主义
如果说,构成主义在苏联的失败是现代主义与共产主义分离的开始,并且只影响到苏联艺术家的话,那么20世纪30年代前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则彻底打消了欧洲知识分子对于共产主义的幻想。1924年,列宁逝世后,斯大林掌握了苏联的最高权力。1927年,在欧洲知识界有着很高威望的,主张世界革命(而不是一国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托洛茨基被斯大林开除出党,并被驱逐而流亡。1928年,为了肃清托洛茨基的影响,斯大林加强了对于第三国际的控制,引起很多曾经支持十月革命的欧洲进步知识分子的警觉。同年,打着左翼社会主义旗号登上政治舞台的墨索里尼在意大利终止了议会,取消所有政治团体并镇压进步的知识分子和共产党—墨索里尼的崛起让进步知识分子看到了欧洲的法西斯主义危险,整个20年代末到30年代中期,知识分子还试图将消灭法西斯主义的希望寄托在斯大林身上,即使在1933年希特勒上台之后,他们也不曾放弃希望。在大部分人心目中,1936年的西班牙内战,是苏联领导的包括摄影师卡帕、作家海明威在内的左翼知识分子联盟与德国和意大利所代表的法西斯之间的斗争。但是到了1939年,苏联便不再支持西班牙的左翼,从而使西班牙被法西斯政权所掌握。西班牙的陷落,使得全世界都对法西斯的扩张感到焦虑,德国对波兰的企图更使知识分子感到忧心忡忡。紧接着的同年8月,斯大林和希特勒签署了互不侵犯条例,并且秘密瓜分了波兰。《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导致欧洲的进步知识分子对于苏维埃和斯大林主义的理想彻底幻灭,在他们看来这是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合流。在欧洲的前卫艺术家和理论家群体中,很多重要的知识分子都是犹太人,在德国和奥地利迫害犹太人的时候,苏联的国内战争也导致了很多犹太人逃亡,《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则进一步将犹太人聚集的波兰暴露在法西斯的统治之下,这无疑加深了进步知识分子对于斯大林主义的厌恶。当他们联想到苏联对于构成主义艺术家的放逐,更使得欧洲知识分子觉得斯大林主义几乎就是法西斯主义的同义词。这样,现代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蜜月期也就在20世纪30年代结束了。在30年代前后,像布列东这样的艺术家纷纷在加入共产党后又退出了共产党,而很多人也开始由支持共产主义转向反对集权主义,比如法国作家纪德[Charles Gide,1889-1880]、英国作家乔治·奥维尔[George Orwell,1903-1950],后者的《动物庄园》深刻地描述了30年代知识分子理想的幻灭,而《1984》则显示了对于集权主义的反思。
也正是在1939年,格林伯格25完成了他第一篇重要的文章《前卫艺术与庸俗文化》,他认定“前卫艺术”是诞生于19世纪五、六十年代知识分子的先进意识的一部分,是西方文化中心的艺术家的一种新的创造。前卫艺术是对产生它的资产阶级文化的背弃,前卫艺术之所以前卫,是因为在西方社会(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法西斯主义)中存在着庸俗文化。庸俗文化是古典文化和古典文化的大众翻版,并且为各种政治所利用。因此,前卫艺术不可避免地被群众所回避,只有少部分社会精英才能接受。而正是群众的反作用决定了前卫艺术是一项重要的实验,从而为文化增添新的形式。一年以后,他又发表了《走向更新的拉奥孔》,在这篇文章中,他通过对现代主义绘画实验的形式分析,归纳出前卫艺术反抗庸俗文化和资产阶级的方式就是取消题材,而进行形式自律。即使如此,他还是坚称:
“前卫文化的任务是在反对资产阶级社会的过程中履行某种职能,这种职能就是为了在同一社会的表现中寻找新的相应的文化形式,同时不屈从于其意识形态的划分,不屈从于它对艺术进行自我评价的否定。”26
这两篇文章树立了一个完美的逻辑:庸俗文化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文化,前卫文化是对庸俗文化的反叛,而抽象绘画因为其纯粹性和精神性,所以是前卫文化的代表,也因此抽象绘画是对资产阶级在艺术上的反叛,而抽象绘画反叛庸俗文化的方式则在于取消题材。
但是在1960年发表的《现代主义绘画》中,格林伯格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他认为现代主义是资本主义文化的独有现象,它与“始于哲学家康德的自我批判趋势的强化甚至激增同出一辙”。这种自我批判来源于启蒙运动的批判,但现代主义与启蒙运动的批判运作方式有着显着的不同,“启蒙运动的批判以更能让人接受的方式从外部展开;现代主义则通过被批判对象本身的过程从内部进行批判。”27。同理,现代主义绘画发展的动力就在于内部批判:
1938年,布列东、里维拉和托洛茨基在墨西哥。达利曾说:布列东是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
“因此,每门艺术都必须以独特的方式实现这一点。以下必须得到展示和阐明:不仅在广义的艺术中,而且在特定的艺术中,都存在着独特的和不可简化的东西。每门艺术都希望通过其固有的方式决定这门艺术自身固有的独特作用。这样无疑会使各门艺术的权限范围变得狭小,但也使各门艺术权限更加牢固地在范围内占据更可靠的地位。”28
沿着这个逻辑,“纯粹性”便成了艺术的首要原则:
“每门艺术都将变得“纯粹”,并在这种纯粹性中寻找确保自身物质标准和独立性的东西。纯粹意味着自我定义,艺术批判就是一种彻底的自我定义。”29
“而绘画自我定义的方式只能存在于‘平面性’。”
“在现代主义绘画的艺术批判和自我限定过程中,强调不可避免的平面性是其最根本的特征。封闭的形状支撑是一种隶属于戏剧艺术的条件和规范,而色彩则是一种隶属于戏剧和雕刻艺术的规范或手段。然而二维的平面是绘画艺术唯一不与其他艺术共享的条件。因此,平面是现代绘画的唯一方向,非它莫属。30”
以格林伯格的这三篇文章为轴心,结合他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的批评文章,我们可以感觉到一种明显的“退却”。这种退却首先体现在:“前卫艺术”这个词在60年代以后就不再出现了,而被取而代之为“现代主义绘画”;其次,《前卫艺术与庸俗文化》从社会学、政治学角度树立了抽象绘画的前卫性,而在《走向更新的拉奥孔》中,当格林伯格梳理作为前卫艺术的抽象绘画的历史的时候,抽象绘画演进的中心从“趣味反叛”转化为“形式简化”的原则。1960年的《现代主义绘画》则将“形式简化”中三位一体的媒介、纯粹性和平面性再度简化为“平面性”至上的原则。第三,相比以前的文章,《现代主义绘画》完全不强调抽象绘画的意识形态的反叛功能,格林伯格通过取消外部批判在现代主义中的重要性,将抽象绘画的价值与外部现实的批判完全切断。早年那种对于资产阶级和庸俗文化的深刻而豪迈的批判在60年代的格林伯格笔下已经荡然无存。我们甚至可以说,格林伯格的理论已经从典型的左翼转向完全右倾—特别是当抽象表现主义被称为冷战的文化宣传武器的时候。很多学者都意识到了格林伯格的这一变化,有人认为这是格林伯格形式主义理论的悖论,也有人认为这是格林伯格的思想从激进变成保守的转变,也有人将之概括为去马克思化。无论表述有何不同,一个显著的事实是:50年代末期开始的艺术发展很快就证明将前卫艺术的价值等同于平面性原则的误区。格林伯格也因此成为当代艺术必须清除的障碍,而且事实上他的影响在实际艺术创造中也彻底被清除掉了。
格林伯格1960年在《三十年代后期的纽约》的自注中轻描淡写的“转化”为什么会发生呢?它到底是格林伯格试图将形式主义理论哲学化的必然代价,还是经过麦卡锡主义(McCarthyism)31后的对共产主义的“背叛”?这是一个无心的偏颇,还是有着别的原因?沿着我们梳理的现代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前卫艺术与庸俗文化》的写作、发表和产生广泛影响的大背景是当时进步知识分子对于法西斯主义的恐惧和对于曾经寄予厚望的社会主义的失望。对于艺术界人士来说,从构成主义艺术家被驱逐出苏联的时候,他们就感到困惑:为什么抽象艺术不能为社会主义革命所接受?在此背景下,梅耶·夏皮罗[Meyer Schapiro,1904-1996]的《抽象艺术的本质》试图弥补抽象艺术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鸿沟,即他认定抽象艺术所提供的是一种否定古典文化的意识形态模式,是一种积极的力量,所以也同样能表达批判社会的意识。同时,抽象艺术可以不依赖外部事物独立表达情感,是新型的前卫艺术。夏皮罗试图通过“前卫性”找到抽象艺术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关系,而无论政治还是艺术,其前卫性的基础则是对于个体的尊重。可是,斯大林在20世纪20-30年代的政治清洗以及和纳粹德国和约的签订,使得左翼知识分子将对法西斯的恐惧投射到苏联的政治斗争中—他们最终发现,即使在最根本的人道主义问题上,他们也无法和现实中的社会主义政治实践分享价值。
这些知识分子开始进退维谷,当他们无法否定社会主义革命的合理性,也无法忽略苏联政权对于知识分子的暴行的时候,托洛茨基主义成了他们的选择。这一选择的象征性在于,左翼知识分子从托洛茨基这样在现实中被放逐的社会主义政治家身上,感受到了他们在思想上的被放逐之痛。托洛茨基对于20世纪30年代乃至今天欧美的左翼思想意义之深远给予多高的评价都不过分,而他之所以能被称为西方左翼思想的大旗,还因为他认为艺术应该在社会革命中有自己的特殊性,而这和当时左翼知识分子畏惧的斯大林主义是非常不同的。在1923年《文学与革命》32中托洛茨基主张艺术作品首先应该用自己的法则来批判;在1938年的《艺术与政治》33中,作为当时左翼知识分子对前卫文化与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矛盾的困惑的响应34,他提出所有伟大的思想都是旧思想的碎片—新教是天主教的碎片;马克思主义是黑格尔哲学的碎片;新的艺术也是一样。因此先驱们越是勇敢实验,就越感受到与保守群众和既定权威对抗的痛苦。他还抨击了斯大林政府对于艺术实践的束缚,并且暗示艺术是一种要求真诚的精神功能(而这在苏联虚假的宣传文化中是不可能存在的),因此最重要的是艺术应该保持自己的规则和原理,独立于各种权威之外。所有的这些思想最后体现在《创造自由的革命艺术宣言》35中,即艺术要扮演革命的角色,首先必须彻底反抗一切对艺术创作的束缚。托洛茨基思想对于当时的左翼知识分子最大的影响在于:他认定艺术虽然是革命的一部分,但是艺术在革命实践中有着自己的原则,并按照自己的规律发展。在格林伯格30年代的两篇文章中,我们几乎完全可以将他的理论和托洛茨基的对应起来36。比如,《前卫艺术与庸俗文化中》将前卫文化、庸俗文化、学院文化、大众文化理解为资产阶级文化的碎片,而庸俗文化是保守的资产阶级的权威的代表;在《走向更新的拉奥孔》中,首先借用以上夏皮罗对抽象的分析,然后结合托洛茨基对于革命的艺术必须摆脱权威的观点,认定了抽象绘画通过摆脱内容的控制而获得前卫性和革命性,但是艺术的实践必须有着自己的原则(媒介性、纯粹性和平面性)并按照形式简化的规律性来发展。
但是,格林伯格和左翼政治的关联似乎就到此为止了。虽然格林伯格对于抽象艺术的前卫性的批判来源于夏皮罗,但是托洛茨基的理论却使他很快走向了夏皮罗的反面,即现代主义绘画越来越成为一种“象牙塔”。这种转变则是从对巴黎画派的谋杀开始的。格林伯格在1947年7月的《国家》杂志中,将纽约模仿巴黎抽象绘画的艺术称为“新前卫艺术”,声称“这种新‘现代’艺术就会迷惑、阻碍和制止真正的创造者”。1948年,《立体主义的衰落》则标志着他认定了现代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巴黎的最终决裂,他说道:
“如果说像毕加索、布拉克和雷热一样伟大的艺术家令人悲哀地衰落了的话,那么可能只是因为过去保证他们发挥作用的一般社会前提在欧洲已经消失了。另一方面,如果你可以看到,随着戈尔基、波洛克、戴维·史密斯这样新充满活力和意蕴的天才的出现,近五年美国艺术水平提高了多少,那么结论颇令我们吃惊:西方艺术的主要前提连同工业生产和政治权力的引力中心最终已经移到了美国。”37
格林伯格对于巴黎画派的批判有着多方面的原因。30年代以来欧洲左翼(很多知识分子这时已经到了美国)对于法西斯主义恐惧和斯大林主义反感的延续,特别是受苏联影响很重的法国共产党和意大利共产党在1948年以后几乎在大选中掌权的趋势,更加深了这种恐惧。对于美国人来说,这无疑是欧洲在被法西斯攻陷后的又一次沦陷,冷战理论和马歇尔计划就是在这个背景下产生的。当格林伯格说,“一般社会前提在欧洲已经消失了”,其实暗指的是欧洲可能被苏联阵营占领,文化的自由将不再存在。“二战以来”,相比深受战争摧毁的欧洲,美国的经济获得长足的发展,其外交体系也从门罗主义(Monroe Doctrine)38转化为全球扩张。在此因素的影响下,在美国产生了一种非常强烈的自主意识—这种自主意识体现为政治上的新自由主义39。美国和欧洲的关系在40年代颇有些像巴黎和凡尔赛在19世纪中期的关系(如前文所述,巴黎掌控了政治和经济,而凡尔赛则在文化上控制着巴黎),现在则需要一场革命将西方文化从集权主义中拯救出来,而革命的武器则是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领导者只能是美国。欧洲经历过资产阶级革命后依然存在着社会和文化的等级壁垒,苏联的斯大林主义则以革命的名义消解了个人主义,而美国作为一个移民的新教国家在文化和社会价值上奠定的价值核心正是个人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