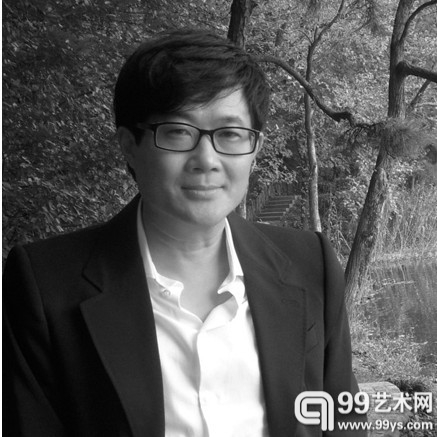
从“疯人岛”到阿玛尔菲
From San Servolo to Amalfi
——“给马可波罗的礼物”的散记
2月底,我因为筹备展览,从在威尼斯的书店里买到的THE TREASURES OF VENICE(WHITE STAR PUBLISHERS)中得知,在9世纪,San Servolo是本笃会教士居住的地方,从12世纪至1715年,主要由修女操持,她们在这里为士兵修建了一所医院。1734到1749年,这里修建了教堂。以后,部分建筑被转而作为精神病院,直到1978年才关闭。把这个孤独的小岛用作精神病院是可以想象的,她美丽、孤独,却与城市没有过分遥远的距离,方便,适合于家人的关怀与探望——我想是这样。我并不知道San Servolo详细的历史,我也没有非常的探究心去了解她的过去,从圣马可广场坐船去San Servolo,只需要十分钟左右的时间。灿烂的阳光下,我们能够非常清晰地看到她。不过,在绵绵的雨天,透过迷蒙的空气,只能依稀看到她的模样。在第一次登上San Servolo的时候,我拍了几张有水滴痕迹的照片,不能否认的是,我喜欢San Servolo,她的建筑,教堂与花园,不是别的原因,仅仅是因为她的相貌告诉我了时间及其含义。的确,与威尼斯其他地方相比,San Servolo没有特别的不同,甚至也没有特别的建筑,不过是曾经有修士、士兵和精神病人居住和使用过的地方,而今天,她是威尼斯国际大学(Venezia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的校园。如果不是要举办“给马可波罗的礼物”这个展览,也许再多的威尼斯之行,我也很可能不会登上这个空间非常有限的小岛,而事实上,我已经不少次数登上了她,游历了她,我透过她的视线,观看了岛外的风景,眺望了远处本岛上的建筑与人群,目送了不同形状与速度的船只,领略了大雨将致的乌云以及黄昏中的彩霞。我承认,对于那些长期居住在垃圾般的城市环境中的人来说,的确可以用“美丽”这类我们已经长期不使用的词汇去形容San Servolo,并且丝毫不会让人感觉到牵强、尴尬与做作。
5月24日,我是在没有任何激情的心理状态下启程再次来到威尼斯的,仅仅是要为展览作提前的准备。之前,吴山专和张培力的装置作品让我心里不安,他们的作品所需要的材料与工程技术要求,导致预算的增加和时间的急迫。想说的是,没有什么“美丽的”风景能够覆盖内心的焦虑与烦躁,尤其是,没有任何艺术在成为物理事实之前能够让人激动与欢欣,尽管冲动,尤其是艺术家的内心冲动被认为是艺术之所以成为艺术的前提。因此我要承认,展览本身丝毫也没有让我有任何激情,就像我们每天清晨从床上起来需要漱口和洗脸一样,只有程序与时间表在指挥行动,无论展览是否重要,是什么性质,都需要按时开幕,我要去完成这个似乎必须去完成的项目。
直到25号,生活本身并没有提示任何戏剧性。我与吴山专、英噶(Inga Svala Thorsdottir),设计师殷九龙和他的助手走下飞机旋梯,我们到达了马可波罗机场。water taxi将我们一行送到了San Servolo,没有任何值得提及的事情,除了听取先前到达开展工作的学生孔立雯的工作报告。夜晚在9点半之后降临了,14号楼的路灯指示着我们,让我们领略黑夜中的San Servolo,以及红砖墙外远处的灯光与无底的海水。我又一次观察了教堂前面的院子,我决定将这个有古代雕塑的院子作为openning night的场地,此外,我们要通过院子到教堂的后院去关心吴山专的工程师的工作。站在准备安装霓虹灯的脚手架上,我们眺望了海面和本岛上的灯光,波光粼粼,灯光投射出教堂的“后背”。这时,通常的感受会给出“美”的评价,不过,工作本身是枯燥的、紧张的、担心的甚至是恐惧的,情况往往就是这样,美如果离开了目的和效用,也变得不那么美了。她没有让人有任何遐想,仅仅是一处物理世界。记得20多年前,读到康德(Immanuel Kant)的书,很多人有了“无目的性”这个概念,我们被告知,功利与目的是有害的。人的高级精神具有抽象性,美,朝着无限的高处上升而展开。可是,在夜晚,如果我们走过灯光幽暗的教堂回廊,想到的仍然是白天现实生活中的很多麻烦事,心情仍然是下降的。没有什么精神是一直朝着抽象而去的,尽管人到终了会有抽象的意象。经常的感受就是这样,学术或者哲学的唠叨没有减弱现实的焦虑,在离开北京的前一天晚上,黄专在“梧桐”谈到了苏格拉底(Socrates)对“抽象”的坚持及其意义,他用“硬问题”来表述这样的坚持是何等的有价值。是的,我们向往那样的世界,好像艺术也具有实现这类向往的可能,可是,为什么人类数千年来没有达成哪怕是抽象的一致性呢?即便两个卿卿我我的情人,只要一丝原因,冲突和矛盾就油然而生;两个有智慧的知识分子讨论学术问题,也很容易被现实的一击而导致分离。我们是灵魂构成的——如果我们认可“灵魂”或者“spirit”这样的词汇仍然可以勉强使用的话,我们知道灵魂是不可捉摸的,活动的,不能控制的,不可躲避的,或者完全有自主权的,灵魂可以给出一切,包括黄专说的那些“硬问题”,可是,智慧是如此地相对无力与脆弱,只要面对物理世界给出的麻烦,一个女人离去的背影都会让你心烦意乱,世界在很多时间里处在黑暗中,尽管这里白天的阳光异常灿烂,何况我将在次日开始去解决那些有关展览的琐碎工作,这就是这个晚上我的心情。
经验告诉我们,对于那些没有将时间放在对微观世界的思考和体会上的人来说,没有什么情绪是值得或能够让记忆永久操劳的,每分每秒中的感知并不存在,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仅仅是把似乎重要的事情联系起来,而省略掉了中间的一切。我们能够记住什么?每个人都不一样。时间长了,我们会觉得我们的生活没有什么太多的内容。可是,在清晨,如果领略一下San Servolo的一切:走过那些小径,步上木板搭建的眺望台,抚摩被风雨抚摩过无数次的柱廊,观看建筑的那些被时间侵蚀而出现的斑驳,就可以知道,只有细节才是记忆的真正内容。细节属于物理世界,我们总是通过物理世界的细节来拼凑我们的价值,我们说建筑是如何的雄伟,充满风格与绝妙的趣味,可是,我们说的都是物理世界的事情;我们讨论威尼斯的美,那也是由那些不同宽窄的小巷、流水、船只以及花花绿绿的人群构成的,这些还是物理世界的事情;我们倾听圣马可广场回廊边的音乐,我们喝咖啡,甚至我们被音乐带到遥远的过去,那也是物理世界的记忆,我们想到历史中的人物,如果你去了古根海姆美术馆,或者在Academia博物馆里阅读到了提香(Titian),我们想象小巷里关闭着的有时间痕迹的小门里的故事,想象迎面而来的路人的经历,当我们站在Rialto桥上观看Gondola上的船夫,也许,很快就想到了那些在法国印象主义者的作品中看到的风景,所有的这一切,其实都是物理世界的东西。当你不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那些弯弯曲曲的水巷中就不会有别的情人?叔本华当然提醒过我们:世界就是我们感知的表象。感知的重要性被无数的文字描述过,可是,有经历的人可能会更同意:感知,似乎仍然属于物理的世界,尽管这个世界为感知所感知。
26日的清晨,推开窗户就可以看到水临窗边的大海。刚刚升起来的太阳将她的光线投射在远处一个小岛的白色的建筑上。这可是物理世界。如果一定要使用“感动”这样的词汇,清晨的风景比艺术更让我容易使用这样的词汇。这里很可能掉进了古人对艺术和自然的描述,让我们回想到无数艺术家和哲学家关于自然的判断。我知道,也就是在一百年左右的时间,自然才被一些艺术家所忽视和轻蔑。通过读书,我知道了自然的含义已经被改变,我们在重新认识和理解自然,我们将自己的心灵世界也理解为自然中的一部分,甚至心灵就是自然。于是,我们经常发现我们回到了哲学的语词陷阱中,成为历史与古人的俘虏。当我们到了安装TOBUY IS TOCREATE(英文的安排是吴的生造)的现场时,德国工程师已经在脚手架上工作了。通常,对于那些在烈日下工作或者劳动的人来说,阳光不是很美丽的,温度增加了汗水与内分泌紊乱的几率,导致情绪的不稳定,导致疲倦与困顿,导致对感情的不专一和不关心,导致对细节的放弃。不过,事实也不完全是这样,在炎热刺眼的阳光下,三个德国人——父亲Roger Juers与他的两个儿子——像机器一样一丝不苟地在这里工作。我们养成的生活态度,尤其是自由散漫的人会不接受“机器”这个词汇。它没有感性的力量,对于柔情似水的人来说,它几乎是暴力的同义词。在我到达San Servolo之前,我想象不出吴山专作品的脚手架和有机玻璃的字母会是怎样一种情形。然而,当我看到了那些用有机玻璃做成的字母,看到了那些精致的螺丝钉,看到了德国人在烈日下的状态,我不得不使用“很专业”这个词汇。于是,理智,或者说“机器”唤起了激情,精确与完美成为我们喜悦的依据。这是我的感受。我告诉那位父亲:“你很专业。”吴山专告诉我,没有什么比“你很专业”更能够让他们感到幸福与愉快的了,他们为“专业”而感到无比骄傲与自豪。一切都在进行中,即便是非常粗的活路,例如将废土拉进展览空间——那是王广义的作品空间,也有一个宽宽的白色织物被安排在走廊,目的就是让即便是橡胶做的轮子也不要损坏了室内的地面。更多的工人出现在展览空间,拆卸壁灯,安装镶板,将膏灰刮在镶板上。之前,那是我在4月25日到San Servolo与Francisca研究工作的时候,我感受到的是意大利方激情与紧张的严重欠缺,甚至只有没有太多关心的冷漠。现在,这里的一切都显示出开始与进步。下午4点半,当我再次走到吴山专作品的现场,安装工作已经结束,德国父子三人已经在草地上抽烟和喝着可乐,霓虹灯已经十分精确地被安装在了有机玻璃的字母板上,让我最担心的工程最早完成了,这时,张培力的安装现场才出现了白色的涂料。这是我在26日中最深的印象:“机器”与进步,专业与快乐。黄昏,我们在食堂的外边共进晚餐。我把一张父亲在黄昏中的照片挂在了网上,是想表达对德国精神的敬意,在国内艺术圈的工作范围里,我几乎没有看到过这样的工作态度和质量。
【相关链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