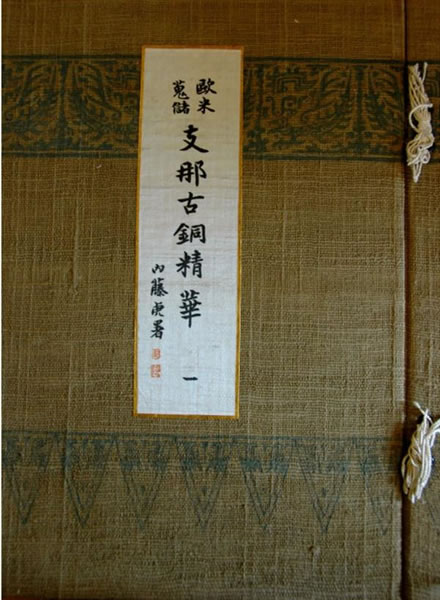
《欧美蒐藏支那古铜精华》封面
《欧美蒐藏支那古铜精华》印量非常有限,每套都有独立的编号,因此目前即使在收藏丰富、历史悠久的东亚艺术图书馆中也是非常罕见的。打开扉页,在陈述学术目的之余,有些细节可能能给我们更多信息。这套书并不是纯粹的学术著作,而是梅原末治应山中商会之邀编辑的,实际上也就是山中商会的销售图录。出版发行之后,山中商会会及时补寄照片和勘误表,也会寄出哪件器物已经售出的简要说明。山中商会的兴盛就是中国文物外流的一个缩影。
这个时期,日本及全球其他地方的中国艺术品收藏急速膨胀。主要在洋庄的帮助下,全球的中国古代艺术品收藏已经从满足西方猎奇心态转变到真正认识中国艺术之美。到1930年代,人们有一个强烈的愿望,需要描绘一张最新的中国古代艺术品的全球分布图。拥有中国古代艺术品收藏的藏家们也希望界定自身的地位。在一定程度上,这就促成了西方在1935-1936年的伦敦中国艺术博览会。这次艺展对中西学术、商业、收藏、观众等各个方面来说,都是一拍即合,由此造成一场轰动世界的文化盛会。这是中国国宝第一次走出国门,也是迄今为止在海外展出的最高规格的国宝展。对国民政府而言,大战在即,文物外交有助于获得更多的支持。对于故宫,这次大展的意义同样非常寻常,故宫从帝制遗产到博物馆的转变过程漫长而曲折,正是在伦敦中国艺展上,故宫最终成为艺术博物馆的龙头老大。
日本的中国古代艺术收藏在这个时期内也是突飞猛进。住友财团收藏的奠基人住友春翠的泉屋收藏了大量中国青铜器,泉屋的图录在很短的时间内不断重编再版,一方面说明其收藏增长迅速,另一方面也说明研究和认识迅速成熟。日本的中国艺术收藏迫切需要集成式编纂,这是梅原末治的系列图录的背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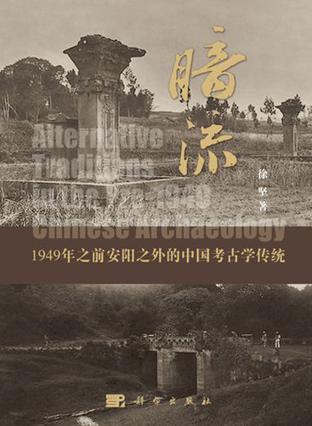
这样看来,金村从盗掘开始就融入到古物流通网络之中,怀履光只是其中的一个买家,并没有操纵的能力。而且,由于金村声誉鹊起,以至于从不同地点盗掘出土的不同器物都有可能贴上“金村”标签。因此,任何一笔“金村”收藏都有可能是时代和地域意义上的杂拼。而在最重要的编辑者中,虽然怀履光以真实记录为目标,但是对于梅原末治而言,全球或者日本各大收藏的辑录式整理才是他的主要兴趣。而梅原末治在甄别鉴定上过度相信口述资料,在风格厘定上显得粗糙,这导致本就不够清晰的金村进一步模糊了。
编辑:江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