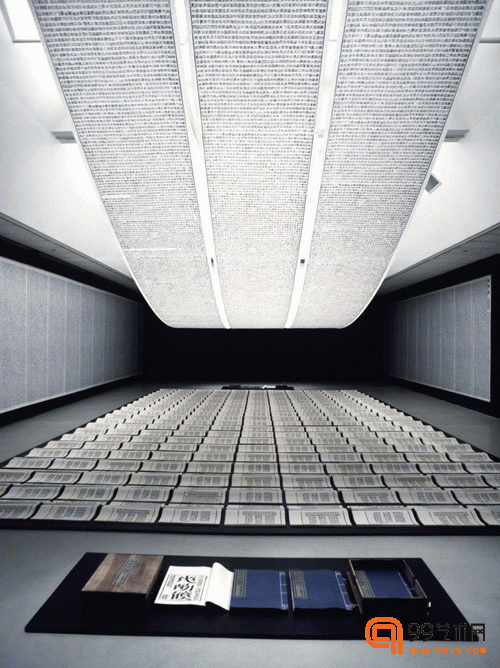
徐冰 《析世鉴》1988 年 木板水印 装置 110×1200cm
徐冰
在1988年的中国艺术界,徐冰的《析世鉴》引起了一场“徐冰现象”的讨论。
与大多数同代人一样,徐冰(1955— )中学毕业后到了农村,经历了两年“再教育”的过程。徐冰曾把版画的重复性和痕迹结合起来加以考虑,以图在重复的工作中展示不重复的艺术形象。他的《木刻第二系列》就是这种结合的有趣尝试。这组木刻体现了徐冰早在1985年就已意识到的一个道理:“把绘画的过程更多地看作是一种创造性思维的过程……”艺术家自信,在制作过程中,艺术家的灵魂能够获得一种类似于“修炼”过程那样的完善与满足。正是这样一种精神,指导着徐冰后来进行了《析世鉴》的制作。
1988年10月,徐冰的《析世鉴》与中央美术学院教师吕胜中(1952— )的《彳亍》在中国美术馆一展出,引来了批评家的注意。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忍耐,佛教文化中的“修炼”,浸透在《析世鉴》之中。徐冰之所以提出“复数性”,与这种精神在自己的思想中占支配地位有着极大的关系。徐冰曾对许多人谈起过释迦牟尼寻求真谛不畏艰辛的故事,并表示他自己很乐意接受这样的精神状态。就在充满火药味的中国现代艺术展期间,他还很有兴味地讲述一个朋友曾经给他讲过的故事。在讲述中,艺术家将试图避世修炼以求大彻大悟的心理表现得非常清楚。
《析世鉴》是’85思潮的一个转向——由批判和颠覆性的姿态转为对意义的退出。我们清楚,谷文达和吴山专在’85思潮期间曾经对汉字进行过富于达达意味的处理。基于一种敏感,谷文达和吴山专已经在自己的作品中打破了汉字固有的文化樊篱。他们行为的重要性不在于是否消除了汉字的字义,而在于使汉字从此丧失了它在艺术言语范畴的尊严,它的存在之于艺术家,不过是为了表达某一内在需要的材料。文字在作品中是否保留了原意的痕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艺术家对它的使用造成了对人们习以为常的规则的侵犯,因为对“规则”或“逻辑”的侵犯隐含着双重的可能性:它既可以在艺术语言上导致一种新形式的产生,又可以形成一种对文字所支撑的文化体制和习惯的颠覆。徐冰创造的文字是’85后期出现的消除意义的新倾向的一部分。事实上,在谷文达和吴山专之后,人们实际上已经有了思想准备:汉字本身没有神圣不可侵犯的尊严,艺术家可以随便对待它。
在“大灵魂”和“纯化”艺术语言的争论中,在“新学院派”提倡艺术形式的精致化以及部分批评家关于艺术应该保持对现实的批判的观点对立中,徐冰的作品似乎到达了一种“超凡脱俗”的境界,在这两种思潮的喧哗之中,艺术家跳出了本质主义的争论,站到了一个“大彻大悟”的立场上。
- 相关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