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完成作品 250x360cm
就在第六届全国美展半年之后,艺术界的人们又感受到了一股清新的空气。它直接来自1985年5月在北京举办的《前进中的中国青年美术作品展览》。从这些青年人的作品中,真正感到了中国艺术的发展正在从一个面孔走向多元,各种艺术风格的追求开始拉大距离,并形成自己独特的面貌,看到这些作品由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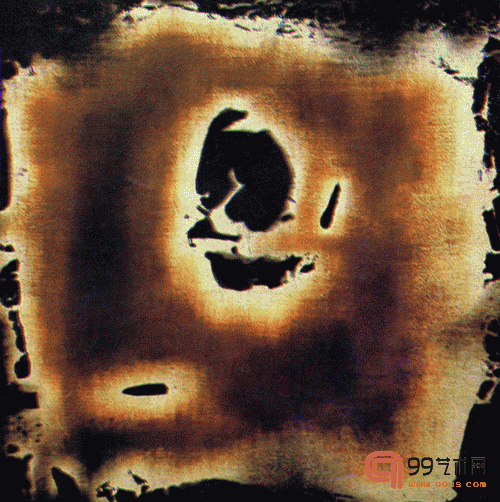
鹿林 《胎息图》 1986年 丙烯
毫无疑问,中国原有的关于职业的安居乐业的传统观念,中国艺术家以及一切在单位里工作的社会成员的固定精神状态,在80年代受到了最强有力的挑战。商品经济和个体经营的短时间内的成功使人们意识到,在脱离固定的单位体制状态下,个人的努力也许更能体现出自我的价值。对于作为个体的盲流艺术家来说,追求内心生活的无拘无束是自不待言的事。但是,这种追求的目的的达到,似乎又必须与他们的生活基本条件相联系。正是在这一点上,那些外国的购画者扮演了重要角色,当然,对于这一点,也有盲流艺术家表示了相当的反感。艺术家张念这样毫不留情地写道:
……为了生活,现代艺术家可怜巴巴的(原文如此——引者)盯着洋人的钱包,他们的爱好成了现代青年艺术家活下去的源泉,这比妓女卖淫还恶心。
不过,盲流艺术家温普林(1957— )在他那篇原拟发表于《画家》的阐释盲流艺术家的长文里这样写到:
我想盲流的这个传统是从历史上延续下来了,这就是“随便”。而这个随便的思想基础是“自我”的观念——自我感觉的舒服和自我的不压抑。其实,这也是人文主义者之流的老传统了。从西洋文艺复兴时杰出的盲流艺术家们,如达•芬奇、卡拉瓦乔之流再到西班牙味道的、潇洒的盲流戈雅之类,一直再扩展至现代风味的盲流高更、波洛克。哪一代盲流不随便,随便地把握着人生的历程……
毫无疑问,盲流艺术家“随便”的“艺术的”生活方式,为中国艺术家们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这些盲流艺术家们所采取的生活方式,使中国的艺术家看到了他们模糊的未来——不管他或她是否彻底放弃自己的固定工作和稳定的收入与福利,他们都将发现自己的艺术生涯又多了一条新的道路。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下一页
- 相关新闻
表态



0人
0人

